“风景先于我们的梦而存在,它早已在此,目睹我们的到来。”
—— 罗伯特·麦克法伦,《荒野之境》
I 一瓶香水
收到 melt season 的新香水时,我正在打理露台小花园。
那瓶香水的盒子嵌在一小片苔草里,很漂亮。 我把它摆在花园里拍了点照片,它很快就融入了环境。它们像是一个小声的期许,在召唤清爽的初夏。


香水的名字“敕勒”,于是很自然地想到了那首《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印象里,这好像是学生时代最早碰到的包含了两个易错读音字的诗。其实要不是去查了一下,我到现在还不确定“四野”的“野”是读“yě”还是“yǎ”……
对那个“见”字就没什么疑义,从一开始,眼前就有一幅画面——风儿吹过,隐没于牧草的牛羊显现了出来。
那个画面在很多年里都是一个中景,和我认知中的草坪、草场、草地重叠了起来,成了一个笼统的概念。直到许多年后,我对植物和自然景观有了兴趣,开始学着重新观看,这个镜头才被渐渐拉近和拉远。
“敕勒”香水就像那个中景画面。

觉得隐约认识。不管是香水本身的颜色,还是那些苔草,都让我以为它会是款清新的香水。想想那些晨光雨露下的青草,明亮温柔,沁人心脾。
这个预想对了一半。
“敕勒”的确沁人心脾,但跟温柔不太有关系。
它有一种更为广阔的意境,更贴切的感受也许是这样的——
从一开始,就像置身在暮色中的旷野。眼见着地平线渐渐消失,天空和大地融为一体。你被这一切包围和笼罩,有种隐藏其间的安全感。黑暗的到来并没有阻碍感官,而是激发了它们的潜力。起风了,送来阵阵混杂着烟草燃烧和草木的气息,惬意的舒畅感贯穿着你……
感受这个香水时,视觉是退居其次的——确切说是对青草的既定想象。
我拿起香水瓶,再看瓶身的文字,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那上面除了“敕勒”,分明就还刻着香水的英文名——“ROAMING WIND”。
“漫游之风”。
这个名字一下调动了我的印象和记忆。
一幅关于草的景象。
II 一段记忆
那是在一个山谷里看到的。
我们一行人本是要去山上的葡萄园,结果碰到了美丽的日落,于是纷纷下车,偷闲欣赏。
一下车,我就端着相机去拍了个日落。

但紧接着,就被脚下的草迷住了。

漫山遍野的草在落日中闪耀着金色,风吹之下,犹如海浪。

低下身子,凑近了看那些草,就像是潜入了水面。世界被一分为二。上面的,汹涌澎湃,下面的,巍然不动。
再近一些,又是另外一幅景象。

同样的草,之前看是一片整体,严密厚实,而现在,它们变得更为生动,像是挥舞着看不见的笔,在创作瞬息变幻的画作……
我后来知道了一个词,“透明性”。
它既是指一种物质条件——容许光或空气透过,同时也是一种人类的知性本能。画家莫霍里-纳吉在他的《运动中的视觉》里提到,某种形式的交叠“超越了时空限定。它们将不起眼的个别事物转化为充满意义的综合。”
这个说法完美解释了我迷上那些山谷之草的原因。它们在偶然之间,让我窥见时空的交叠和渗透。
这个回忆真是美好,所以我现在决定——
以后要是有人问我因为什么喜欢上草的,我就说这个。
III 一小桌旷野
等我真的开始种花种草,那是一年多之后的事情。
如同我对很多东西的喜好。书本,书里的故事,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它们当中有些是植物学或园艺类的,但更多的,我在心里把它们放在了一起,不作归类——
比如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科西莫有一天决定一辈子生活在树上,从此就没下过地;
比如德里克·贾曼的日记。他时常提及自己的小花园。贾曼在一个核电站附近买了一栋小屋,并且在那建造了一个花园,将一片荒芜变成了天堂一般的存在。他从海边捡回漂流木、燧石、贝壳搭建苗圃,又种下虞美人、金盏菊、薰衣草、紫罗兰…… 我在网上搜索这个花园的照片,发现它尽管有人照料,但处处透着野生气息;
再比如那本《杂草的故事》。
里面有句话,改变了我对草的认知。那是爱默生对杂草的定义——
杂草,是指“优点还未被发现的植物”。
大多数杂草,只是在人类看来,出现在了不正确的时间,不正确的场合。于是很多时候,它们被连根铲除……
写到这里,我去露台看了会儿我的小花园。
两周前,我收拾了一个工作台,在上面种了一些草。它们是的的确确的草,有些你可能在路边见过。鼠尾草、山麦冬、羽毛草、蓝盆花、蓝羊茅、柳叶星河、朝雾草、波士顿蕨……
如今,它是小花园里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我尤其喜欢在天快黑的时候去看看。那是我休息的时间,不会被日常琐事分心,但心神又处于游离之中。
在我眼里,那些花草是一小桌旷野。有时候让我很放松,是我的栖息场所。有时候,又像是被暮色染上了神秘,是我的想象之地。
我会凑近了想象自己是一只虫子,于是这些花草都成了参天巨树。从朝雾草的根部启程,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到达树(草)冠,远远眺望,蓝盆花喷吐着蓝色火焰,不啻《魔戒》中的索伦之眼震撼人心,要到达那里,我要跋山涉水,一不小心,就会葬身蓝羊茅的山尖,或者摔下山麦冬的悬崖……



这些想象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幼稚?
但我想当一个人身处于真实的旷野,那种观感也许和虫子很接近。
IV 一部剧集
我还没去过真实的旷野和草原——那个山谷不知道算不算旷野。
不过,这些年对植物和自然景观的认知,也许让我有意无意地作了一些准备,所以哪天真的到了草原,应该不至于停留在一个书呆子的眼界。
关于这点,今天无意间刷到一条有意思的评论。
有个人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我的阿勒泰》的观后感,大概意思是说这个剧太理想化了,美化牧民的生活和环境,应该更“现实”些……
结果下面有个人回复,“去你的,我们牧民哪有那么苦。” 留言地点显示,她来自牧区。
看到这条留言,我笑喷了一口水。
《我的阿勒泰》是“敕勒”香水的合作剧,这些天我也在看。
在城市中碰壁的姑娘,回到老家阿勒泰,渐渐发现了生活的美。此前的她,有点像是爱默生对杂草的定义。
《阿勒泰》让人如此有同感,它也许跟我那“一小桌旷野“有相似之处。它们是一种安慰,多少能抵消一些城市对我们的控制。
我很喜欢剧里一些镜头,那些开阔的画面。
它们有别于常见的剧集,不像是为了小荧屏而生,更像是为宽幅的大银幕而拍摄。这些画面也延续到了一些剧照。看得人神清气爽。



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张。

于天地之间的奔跑,何等的自由。
像飞翔。
V 一架钢琴
这张剧照,我在 melt season 的太原路店里也看到了,在滚动屏上。
上个月底,我错过了“敕勒”香水的新品会。
在后来 melt season 的朋友分享的照片里,有一张让我眼前一亮。
太原路店的小花园变了点模样。

装“敕勒”香水的礼盒,就像是把这个小花园搬了一小块出去。而我很好奇那些立在绿苔上的是什么草种,是不是我认识的墨西哥羽毛草。因为这个草,我最近也在种。它太好看了,透明、飘逸,但又有点茸茸的,让人忍不住想去摸。

于是在前天,我去了店里。
melt season 的太原路店我很喜欢。 这个选址不在热热闹闹的商场,也不是法租界那些人流更多的地方。它很幽静,也很低调。 于是每次去那儿都不像是探店,而是像 拜访某个人,有种自然而然的亲密感。
一到店里,就看到了这个。配合“敕勒”香水的发布所做的店面装饰。

我后来得知这是个“龙”的意象。它从一楼开始,蜿蜒到了二楼的展厅。

但这个毛绒绒的质感真是可爱。于是在某些角度,它又像是一只没藏好尾巴的狐狸。

二楼的专柜上放了一瓶“敕勒”香水。有了这个“狐狸”的心理暗示,我再闻“敕勒”,又有了一点别的感受。比起之前体会到的辽阔感,这回像是镜头拉近了,多了一些亲近。

店里逛完后,我走去了小花园,去验证那张照片里的是不是墨西哥羽毛草。

太原路店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花园。
看那些花草树木,比如水杉、羽毛槭、蓝冰柏,大吴风草,蕨类,像是在见老朋友,“哎呦,最近身体不错。”“可以啊,熬过冬天了啊。”
另一种小小的喜悦,是之前还叫不出名字的,现在又多认识了几个。
澳洲米花就是,上次来的时候我还认不出。这个季节,它开花的样子真是热情,就是气味让人不太想靠近。

走进小花园,我就看到了那架废弃的钢琴。
在之前的照片里,它被草和绿苔覆盖着,没有显示全貌。而现在,我在正面的角度。

跟之前的照片相比,它有另外一种美。

看到它第一眼,我就想到了“教授”坂本龙一弹的那架经历过海啸、被海水侵泡过数日的钢琴,也是一件废品,但在“教授”看是经历过大自然的洗礼,被大自然调试过的琴。
眼前这架钢琴,肯定是没法弹了,我试着按了下 琴键 ,纹丝不动。
但琴盖上那些我最后也没能确定是不是墨西哥羽毛草的草,它们随风摆动,真像是在应和什么我还听不到的乐曲。
真是想不到,来店里是看跟“敕勒”有关的草的,结果有了这么一个收获。
V 另一本书
《荒野之境》是我最近在看的一本喜欢的书。

今天文章开头引用的那段话,就出自这本书。作者罗伯特·麦克法伦在书里坦承,那是他不记得从哪儿抄来的。
我实在很喜欢这段话,于是放在了开头。
《荒野之境》里,麦克法伦从家附近的一棵山毛榉开始写起,写到他去探寻荒野,最后再回到那棵山毛榉……麦克法伦想要绘制一张关于荒野的文学地图,以此对抗常见的公路地图,但他也意识到,这张地图他永远无法完成,也无意完成。
回到那棵山毛榉,并不是放弃,因为他对荒野的探索从未停止过。他的举动是T.S.艾略特那段诗的概括——
我们不能停止探索,
而一切探索的终点
都将是回到启程之处
第一次将它看清。
荒野既是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也存在于麦克法伦的身边,那些之前没有察觉的场所。
我们普通人不是麦克法伦那么硬核的旅行者,但有些东西是相通的。
我们也都在有意无意地绘制自己的人生地图,或者一本词典。植物、香水、以及其他我们热爱的事物,是其中的类目,它们互相连接,互相交织,互相渗透。
我期待有一天去真的草原看看,不过,我想也许我也会像麦克法伦一样,会回到启程之处。
旷野和草原,既在敕勒,也在 melt season 的花园,和我的那个小桌。
今天的小互动:
说一样你喜欢的野花野草。我随缘选两位朋友出来,送这本我喜欢的《荒野之境》。
大家夏天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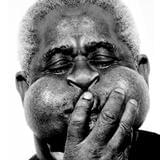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