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1年下半年,省黄梅戏剧院正式分为两个团,我在一团。1962年春,我和蓝天同志带一团到湖北省黄梅县演出,当时的主打剧目是1960年移植的广西壮族歌剧《刘三姐》。这出戏全剧的唱腔我没用黄梅戏的主调(腔),采用的是安徽民歌、黄梅戏的花腔杂调重新编创的,例如其中一首刘三姐和老渔翁的唱段“这边唱来那边和”,我将黄梅采茶戏的“女慢花腔”(又名花鼓腔)作为创作素材。我对黄梅县的采茶戏一直很好奇,现在能带着剧目到黄梅县演出、拜访,当然是愉悦之情油然而生,而且这个由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戏在当时普遍受到观众的欢迎与好评。该戏还被广交会邀请至广州,与上海的昆曲《琼花》作为为中外宾客演出的剧目。在剧团我经常听老艺人说起黄梅戏又名黄梅调,与湖北黄梅县采茶戏有一定亲缘关系。1960年湖北省艺术学院的王民基老师还把他记谱整理的一本《黄梅采茶戏唱腔集》送给我,我一直很珍视这本书,初步知道了黄梅采茶戏的历史渊源和剧种的声腔结构。1958年省黄梅戏剧院在武汉演出期间,一次于汉口江岸区文化馆举办的座谈会上,安徽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1892—1968)和黄梅采茶戏老艺人余海仙(1904—1967)相见,看他们忆往昔之艰辛,说今日的喜悦,我似乎也感同身受。
在黄梅县演出的一周,我们受到了非常热情地欢迎和接待。我因学习、调研心切,更感到兴奋。所以在黄梅县,我除了看黄梅采茶戏的传统小戏外,主要采访了几位著名的采茶戏老艺人,如王艺修、桂三元、项雅颂、周香林和该团的团长乐柯记同志。乐柯记团长是“盖三县”余海仙先生的学生,他向我口授了湖北渔鼓的唱腔。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他还向我口授了一首采茶戏的《打猪草》女腔,是六声宫调式,音阶排列为:sol、la、si、do、re、mi。但他的老师余海仙先生演唱、王民基先生记谱的《打猪草》女腔则是六声角调式,这与严凤英唱的五声徵调式的《打猪草》女腔大异其趣,难怪黄梅有谚语曰:“黄梅戏十腔九不同,各唱各的板,各唱各的音。”这也许就是迄今黄梅戏只有“这是谁的腔”“那是谁的腔”,而无流派的根之所在。虽然自由,但它的生命力极强,一直在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黄梅县有位民俗学者桂遇秋[1] ,对黄梅县的民歌、曲艺、戏曲、民俗等都有较踏实的研究,对黄梅戏尤甚情有独钟。他的长辈桂林栖同志是安徽省五十年代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黄梅戏非常关怀和支持。桂遇秋同志每次到安徽来都要与我在一起探讨些有关黄梅戏的问题,我们到黄梅县演出,他每天都要忙碌着为我们张罗事情。使我收获最大的是,他陪我到黄梅县电台,将黄梅县采茶戏剧中所有录制过的演出剧目和唱段资料,全部复制成几盘大开盘带送给我们剧团。我们团还排演了他们整理演出的优秀剧目《过界岭》。我将这批资料借回家,除学习外,还打算将全部曲谱记录整理出来。“文革”期间,剧团的“造反派”分为誓不两立的“好派”与“屁派”,每天在广播的高音喇叭中互相辩论、攻击,“好派”的录音磁带没有了,叫我把黄梅县送给剧团的那几盘采茶戏的录音磁带交给他们。我因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三反分子”,成为团里的主要批斗对象,那些录音磁带都被斥之为封资修的反动东西,就这样,这些宝贵的资料全部被毁掉了。
注 释
[1].桂遇秋先生除了认证黄梅采茶戏的源流来自民间茶歌、山歌、小调之外,还调查了乡间手捧坊间印制的木刻唱本《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人独唱的名为“黄梅歌”的曲调。桂先生曾为我唱了这三首曲调,这三首曲调我都收录在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黄梅戏音乐概论》中。

时白林(1927年3月15日-2022年12月31日),男,汉族,笔名白林,安徽蒙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著名戏曲音乐家,安徽省艺术研究院原一级作曲、国务院特殊津贴终身享受者、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名誉会长、安徽省戏曲音乐学会会长、安徽音乐协会名誉主席时白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31日12时56分在合肥逝世,享年95岁。

《我的音乐生涯》时白林著,李春荣主编,安徽省艺术研究院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出版发行。这是一本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回顾自己音乐生涯的自传作品。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上篇“音乐生涯”,分5章讲述了时白林怎样走向文艺道路、如何成为专业音乐工作者、电影《天仙配》的诞生、三年困难时期后的“村官”生涯、参加黄梅戏革命小组等人生与艺术经历,并配以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下篇“音乐文论”,精选了30篇时白林创作的文字作品,包括论文、发言、序言和纪念文章等。最后附有时白林音乐创作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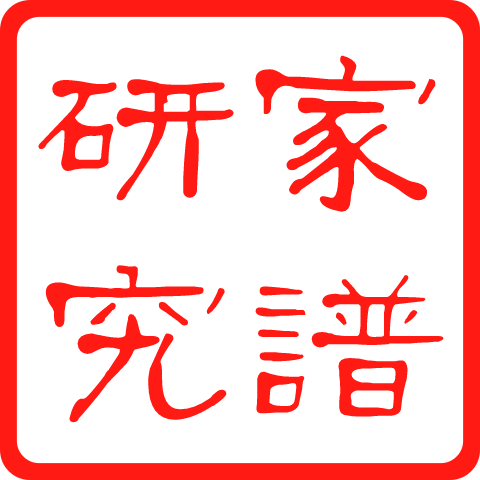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