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佐思佑想知识库本期邀请的“信息捕手”穆川,她的职业在我们眼里会有些神秘,她从事考古、文博行业已经十几年:
本科进入北大考古系,博士毕业后,进入某知名博物馆工作,参与过多个国家级考古项目。
佐思佑想与穆川对话近两个小时,以下是我们出品的对谈精校版,全文15000余字,同步收录在知识库中。
目录:
十八岁的决定:我不要大富大贵,就要学考古
想不到的考古知识:房地产会影响考古工作者的工作量
真实的考古发掘,第一感受是巨大的落差
考古学者眼中的新疆,穿越千年的遇见
欧洲考古经历: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对待考古的松弛感
考古的意义:昨天太模糊,今天就不真实
普通人如何了解考古?考古学者的博物馆攻略和私藏书籍推荐
十八岁的决定
我不要大富大贵,就要学考古
小初:我们先从你这个比较神秘的职业选择开始聊起吧。你本科就选择了北大考古,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吗?
穆川:对的,我的父母虽然没有那么支持我填考古,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尊重我的选择,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小初:为什么会选择考古呢?你是文科生,大家会说文科生有那么好的成绩,就应该去学金融,去学法律这样热门的、有用的专业。
穆川:还是因为我个人的偏向。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历史,但是光学历史的话,我会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史料的研究,每天都坐在书斋里面。
但是考古,我那时可能受一些纪录片或者相关书籍的启发,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觉得它是可以有很多新的材料,而且这个新的材料是需要自己去发掘的,通过这些新的材料就能发现很多新的问题,再去做研究,可能更有意思一些,但是也没有很明确的认知,十几岁那时候对考古还是有很多浪漫的想象吧。
小初:我挺好奇你做这个决定时,你的家人或者老师有意见吗?会不会劝你去读一些更好就业的热门专业?
穆川:是的,而且我高中毕业是十几年前,当时考古、文博没有现在这么火,公众对考古也没有现在这么感兴趣,我收到最强烈的一个反对的声音来自我的历史老师,他也是我的班主任。
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你真的确定你要报这个吗?”他说:“你要是学了这个,以后就不能大富大贵了。”
小初:哈哈哈,你应该反问他,那你为什么学历史?
穆川:可能他是从过来人的角度考虑得比较实际,我也确实比较理想化,觉得考古好自由,能够去野外发掘新的材料,全国各处跑,还挺酷的。所以我当时就回怼了老师,我说我不要大富大贵,我就是喜欢这个,我就要学。
小初:你还挺勇敢的,在十八岁做出这个决定,而且你当时的高考成绩是可以去北大更热门的专业的,所以先给你鼓个掌。
穆川:也没有了,没有那么伟大。当时纯粹就是热爱吧,后来长大一些,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他说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我对他的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更多的就是抱着我对历史的这样一种感受,来选择的这个专业,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不管我之后做什么样的选择,至少在那一刻是发自我的本心。
小初:你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对不对,但是你非常肯定这就是你内心想要的东西,后面的经历也证明了你选择这条路是没有错的。
穆川:我不知道有没有错,感觉这条路自己也还在走吧。我上了大学以后,才发现很多同学都是被调剂过来的。
小初:你是为数不多的,一开始就认定是要选这个专业的人。
穆川:对,主动的选择。那个时候学考古的同学一个年级就十几个人。
小初:你真正去了大学之后发现考古是你想象的那样吗?
穆川:其实差别还挺大的,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慢慢地感受到它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并不是大家所见到的那些很重大的考古发现,那只是考古的一个面相。
考古非常不同于大学的其他专业,因为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用我们老师的话说,它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完美结合,所以我们大三上学期的时候都会去考古工地实习。

在实习的过程中,才是第一次真真正正地去接触这个学科,大学的前两年,我们都在学习基础知识,在学习怎么为大三上的田野发掘做准备,再到三年级的时候下到田野里面,那才是真正的挑战和检验。
小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真正沾了考古的边, 是从你第一次有了实地的挖掘经历开始,才体会到考古它到底在研究什么,或者它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穆川:是的,像北大考古学的设置,大一大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上一些专业必修课或者限选课之类的,那个时候都是停留在课本上的,更多是给你一个整体的考古学背景和学科知识的积淀,包括我们会学习考古学导论、田野考古学概论,你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选修课程,但是更多的还是要落实到发掘,因为考古和传统狭义的历史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是运用文献史料来研究历史,考古是面向田野的,你要去发掘新的材料,然后通过这个材料来研究历史,来研究人类的过去,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放下的就是田野发掘。
想不到的考古知识
房地产会影响考古工作者的工作量
小初: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大家过一阵又会讨论,今天科技的手段已经那么发达了,为什么秦始皇的陵墓还是不能被挖?
穆川:这个涉及到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保护,因为我们现在文物工作的基本原则,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保护。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可这个观点,一个墓葬或者一处遗址,只要一发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它的破坏。只要一打开,就再也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保存条件。
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是有限的,但是技术是一直在进步的。将来有更好的条件、更好的技术,能够更好地去保存这个墓葬的信息,更好地去解读信息,那不是更好吗?
而且考古发掘不光说是秦始皇的陵不能挖,现在绝大多数的墓葬我们几乎都不会去主动进行发掘。唯一一座被主动发掘的帝陵就是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那是建国初期的时候,当时对很多东西的认知还不够完善。
当时也是历史学者郭沫若、吴晗这些人,他们想要发掘永乐皇帝朱棣的长陵,就说先选择一个小一点的帝陵试掘一下,就先发掘了定陵,但是一打开,就会有很多东西意想不到,包括墓中的很多有机物都没有办法及时保存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还达不到。所以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破坏,从那之后国家基本上就定下了一个调子,不主动去发掘帝陵。
我们大部分时候都不会主动去发掘。因为发掘的成本很高,人员也不够,更多的时候,很多地方上的考古所、考古队都是在应付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是被动的,比如当地有一个建筑工地,要开工了,开工之前按照《文物保护法》是要考古队先入驻的,先要去勘探,先看看底下有没有东西,比如像西安修地铁或者修机场之前都要考古队先去发掘。
小初:这个是全国所有城市的规定吗?如果说我要去开发一块地,那首先考古的团队要先勘探看看有没有文物,还是说就针对比如说像西安、洛阳这种古都?
穆川:这个是《文物保护法》里面明确规定的。做这种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所有的建设单位都要报你所在省市的文物行政部门,他来组织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建设范围之内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是可能埋藏,你明白吗?所以它中间是有一个可操作性的,当然可能执行程度更好的是在西安、洛阳这种埋藏文物比较丰富的地方,但从法律上原则上来说都是需要先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的,就是基础建设,考古先行。
小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安一直在修地铁的原因?因为总是会发现文物?
穆川:对,而且这个费用是要建设单位来出的,要列入工程预算。在做预算的时候,就要先考虑到可能会面临的这些考古费用。
真实的考古发掘
第一感受是巨大的落差
小初:回到你的 18 岁,你的历史老师应该是你很敬重的一位老师,当时明确告诉你不要选考古,你父母可能也比较想你选择其他的学科。
我听到你的故事,想到詹青云,她高考的时候特别想去北大考古系,她说这是她十几年的梦想,但是当时北大考古系不在他们那个省招生,所以她就选择了港中文,因为港中文给奖学金,就这么和十几年的梦想擦肩而过。
你不光是本科选择了考古,在你说的那种比较懵懂的年纪,对它有一种外界的想象,但是你后来进入了考古学系,你本科同学可能后来也有很多转行转专业的,因为你刚刚也说有很多同学是被调剂到这个专业的,那你为什么博士的时候还选择继续考古?和你大三时那段挖掘经历有关系吗?
穆川:肯定是有关系的。可以说考古实习是一个分水岭,你可以在田野里面感受到,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我到底喜不喜欢它的。

很多同学也是通过实习以后会发现我不喜欢下田野,也不喜欢整理那些发掘出来的东西,还要研究它,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别的专业,我们当时本科就有转专业的同学,研究生的时候也有同学跨专业去了别的院系,但总体上比例还是比较小。
我们本科考古发掘是在陕西,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落差,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小初: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浪漫,或者是没有想象中都是新闻里写的什么某某重大历史发现。
穆川:是的,因为我们发掘的遗址之前被评为过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小初:你是抱着巨大期待的心情去的。
穆川:我觉得所有的老师同学应该都是抱着这个期待去的,但是你真正去到那个考古现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和你之前想象的那些东西完全不一样。首先你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力,身体面临巨大的考验。
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休息日的,我们看天吃饭,跟农民和建筑工人是一样的,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我们那时候就每天坐十分钟的车,去到一片田野里。刚开始那上面还种着庄稼呢,我们得先跟农民谈好价格,把那片土地上面的庄稼先收了,然后才能去发掘。那些都是老师们做的事,后来会知道,考古更多的时候都是在跟这些打交道,就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然后要开始布方,考古一般是按照探方来发掘,一般是 5✖️5米,中间会留一段隔梁好观察剖面,每挖一点土都得观察。国内的考古一般是有民工的,我们每个探方都有配民工,你要管理好自己的这个方的民工。
小初:所以是每个同学都分配了几个民工是吗?像包工头一样。
穆川:对,但是大部分时候还是我们自己上手去刮,我们用的最多的工具是手铲,不是洛阳铲之类的,那个主要是做勘探用的。

每天就在那刮面,蹲着刮土,要分辨各种堆积的土质土色,看它是什么年代,里面有什么包含物,是垃圾坑、是房址、是墓葬,还是其他什么。很多信息都是根据这个堆积来看的。说白了就是每天在那认土,所以色盲是干不了考古这个活的。
小初:因为分辨不出来纹理或者是颜色,就不知道这个土到底是什么,是吗?
穆川:对。那时候就是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蹲在那儿刮地,要刮得很平整才好划线。划出线了之后才好判断性质,或者它和周边的关系,不同的遗迹之间有一个早晚关系,判断哪个早哪个晚。
因为我们从上往下挖,你最先碰到的肯定就是现代人生活的地层,再往下挖,可能就会是明清的地层,或者是唐宋的地层,再往下就可能挖到秦汉的地层。
小初:这得挖到多少米才能挖到秦汉的东西?
穆川:不一样的,每个地方的堆积不一样,有可能就没有秦汉的堆积层,直接再往下挖就是新石器的,这就是地层学, 地层学是考古的一个基本原理。
小初:你们一直挖的目的是什么呢?
穆川:这个涉及到地层学的知识,我们去发掘的地下遗存,是之前人类活动的堆积,比如原来有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你有活动,有生产垃圾,或者你有建造,改造了自然,我们把这些被改造过的堆积叫做熟土,它包含了以前人生活的文化遗物,我们叫文化层。所以我们就是在发掘不同的文化层。
等到发掘到最下面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文化层了,它是没有经过人类改造的,我们叫生土,到这儿就可以停了。我们就可以从下往上,按时间早晚再反推回去,人类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多久,他们在这里的生产生活,文化层里面有什么遗物,通过包含的遗物也好,丢弃的垃圾也好,来研究之前的历史,他们在这里生活的过去。
小初:回到你的第一段考古经历,你每天这么刮土,当时的内心感受是什么?
穆川:内心感受就是特别沮丧,什么时候能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但是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那个时候每天发掘最多的就是陶片,用那种类似化肥袋、饲料袋的袋子,我们每天拿这种空的袋子装陶片,每个人得拎十几斤的陶片回去。每一片陶片都要清洗、编号,到最后要拼接,有的是能拼上的,拼得上的就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但那都是之后整理的事。
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每天都在挖陶片,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而且对自己所在的、负责管理的那个探方,很多时候是完全不知道的,是陌生的,真的非常沮丧。因为判断不清楚这个关系,可能今天觉得是 A打破了B,明天刮一刮那个面,诶,又是B打破了A,怎么回事啊?
小初:但是真相只有一个。
穆川:对,我们每天都叫老师,我特别感谢我们的老师,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他们每天会串方,到各个探方里面去解决同学的问题,他们对我们发掘的整个遗址内容都非常了解。像刚开始我们甚至都会怀疑,这真的是一门科学吗?不同堆积的早晚关系真的是这样吗?我甚至会纳闷这个。但是后来老师就会告诉你,这真的是一门科学。
他说是A打破B,你刚开始不信,你就跟他犟,挖到最后发现他就是对的。一切都是源于他有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的经验,我们当地的考古队有技工,也会请他们来帮忙,他们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田野考古发掘经验,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大学学了什么呀?特别小白,我不会认土质土色,体力还不好。
小初:经过了漫长又枯燥的那次挖掘,中间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还是坚定地选择这个方向吗?
穆川:有的,我觉得也是循序渐进,像是某种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突然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好像你认清楚它的本质以后,你反而会更喜欢它。之前可能看纪录片,都是一些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但真正的考古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蹲在那里或者跪在那里,刮地,一刮一上午。
但是当你真的解决清楚田野发掘中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发掘了一个房址,从头到尾做下来了,就是从上挖到下,看到了里面古人修的灶,你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的灶台是什么样子,看到他们居住的活动面,有一些会涂白灰,就跟我们现在家里装修是一样的,把地面弄得特别平整,你把土一点一点剥落下来,然后露出了那个涂白灰的地面,有一种成就感。
小初:你刚刚描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就是很感动,你站在那个土方上,一点一点地挖掘,最终你还原出那幅画面是几千年前的人类,他就在这个上面生活着,而且他过的可能是和我们比较相似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里面也有那些东西,你是不是会感受到一种就是经过漫长的历史之后,我们还有那种遥远的呼应?
穆川:是的,我觉得这就是考古带给我最幸福的事情,不在乎有了多大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实在我们看来都很重要,但是在很多外人看来,都是什么呀?一个陶片,一处遗址,连个墓葬都不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你在那么一瞬间的时候,感受到了那个契合的点,这就很重要。
当时我们是每个人负责一个探方,我旁边的同学发掘了一个墓葬,我每天就在那儿围观,最后发掘出来一具人的骨头,还有一匹马。我们开玩笑说,这是个放马的小孩。
小初:这是一个小孩,是吗?
穆川:你就会有很多想象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历史的真实,但是你可以给它赋予一些想象,那些东西都不会写在探方日记里的。包括有时候我们去发掘垃圾坑,里面的埋藏会特别丰富。你看盗墓的完全不会去管垃圾坑,但是我们每天特别开心地发掘,因为它是古人留下来的遗存,就像你说的,两三天的垃圾你就可以了解那个人那几天的活动。我们就可以通过某一个聚落的垃圾坑,来还原他们那个聚落的生产生活是什么样子。
小初:这次的考古挖掘经历让你更加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选择,你更加认清了它的本质之后,反而更热爱了。
穆川:我觉得考古很适合我,因为它是一门很向内的学科,埋头做事,更多的时候是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成一些事情。虽然考古做到管理的,像老师们,还是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比如要和当地处理好一些关系,包括我们自己的探方也要管理得很好,你要和民工处理好关系,还是会有很多和人打交道的事情,但是更多的时候你是在和物打交道,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小初:那之后你选择了本科直博,做这个决定相比你 18 岁那年进入考古系的决定,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吗?
穆川:非常大的不同。如果说 18 岁那时候是一时冲动,等到 22 岁的时候再来做这个选择,我只是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因为越学考古,就会发现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自己身上的不足也太多,学四年是完全不够的,非常不够。
我们班上的同学可能有一大半都选择了继续读硕士或者读博士,老师们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因为考古就是用古代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包含的内容又如此丰富,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学了很多课程,现在想起来,自己那个时候知识储备还是很丰富的,现在可能很多忘记了,但当时是真的很认真地在学习,我们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的课,对发掘出来的动物和人骨之类,比如肢骨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还有年龄这些,都能基本判断出来。
但是学了这些以后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不足。因为考古学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交叉的学科,虽然它是划在人文下面的。最新出来的一些技术,一些测量的手段,我们都是要学习的,因为你下到田野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还有好多东西我不知道。比如说我不会判断陶片的年代,因为我对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不熟悉,你越学就会越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
小初:你要研究过去,要对人类的历史非常的了解,同时你又要往前看,要关注最新的技术,关注最新的科技手段,去帮助你更好地,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我还记得,还原整个人类社会的活动。
穆川:是的,因为你想人类社会多么的庞杂,我们要怎么样通过物来看到人呢?“由物见人”这四个字其实是考古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但是可能是永远都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在努力接近。
陈嘉映的四季游学|与你再次直面解释鸿沟
走进高加索(8.1-11)|免签!世遗与美酒,雪山与教堂,共赴清凉一夏
暑期旅行精选:美国、希腊、日本、埃及、非洲、新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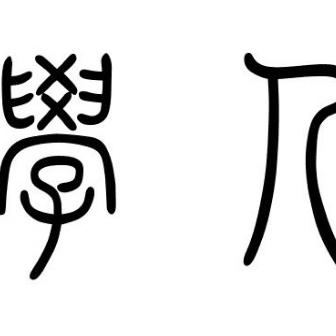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