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自古就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称号,园林的营建与发展有着完整的演进序列。随着秦、汉之一统帝国的形成,帝王苑囿的营建也逐渐朝着融合山水、花木与建筑等多元因素为一体的方向发展,而此时的秦代苑囿又是园林发展史中的里程碑,实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之作。
关中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与体系化的建筑经验,与技术因素为园林的营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其在秦代的建筑、艺术以及文化的发展史上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关中形胜的自然环境与苑囿营建之“基”
众所周知,苑囿就是对自然环境的人为选择与改进,因此其既离不开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又不完全依赖环境的本身,需要人们充分发挥其能动的适应性,对其进行积极的调整与改造,才能达到 “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自然环境的形胜之势仍然是古之园林营建的重中之重。关中地区一般是秦人苑囿的首选之地,其成熟的建制背后是有着诸多原因的。
其一,气候的适宜。远在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气候相较之今日,是温暖而湿润的。据《吕氏春秋》中所载,远在秦时春季来临要早于清初约三个星期左右的推断。秦汉当时的桃花盛开与燕子飞至的时间,确要比今日早出将近一月左右,足可见南方的一些植物与动物在当时的关中秦地完全有理由生长与生存。
其二,高山之势。山势之险胜可以衬托出苑囿的崇高之美,山之高峻,促人登顶,极目远望,远景尽收眼底,尤其是位于西南之地的终南山,其山势高大雄奇,林木繁茂,人若立于山下遥望便可见重峦叠嶂,苍翠无际。

如此这般在有限实景中的无限获取,才使得登山之“人”犹如置身幻境,心旷神怡的真实感受便会油然而生,既陶冶了心境又于无形之中,扩大了苑囿的物理空间,也正是基于此,秦人在进行苑囿设计时,往往以山作为其周边的界址,如秦上林苑就是以终南山为其南面边界的。
其三,水源的丰沛与流转。众所周知,庭园有水则秀,庭园理水一直是苑囿营建中重要的环节。关中地区自古水源充足,正是由于水源的存在,才能使在自然环境中营建的亭台楼阁、水榭小径有了灵动的气息,同时水又是万物生存之本,苑囿之中之所以有各种珍奇花鸟与林木走兽都与水的存在密不可分。
其四,可见沃野千里之“原”。在关中地区既高且平的“原”为数甚多,具体可见有铜人原、风凉原、凤栖原、乐游原、少陵原、高阳原、咸阳原、白鹿原、龙首原以及鸿固原等。由于天然的地形与地貌,使得不同的“原”之间渐自形成了条条水脉与旖旎风光尽的自然景观。

当时在长安城南的樊川就是秦汉时期著名的风景胜地,其全长三十余里,潏河纵灌其中,此情此景,情趣饶多。如此这般沃野川流,明丽风光的诗情画境足可作为《三辅黄图》中“络樊川以为池”的佐证。
《荀子·强国篇》记载:“其固险塞,形势变,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
秦人的苑囿营建离不开自然环境的依托,然此时的苑囿建筑有别于明清以来的中国传统园林的艺术风格,前者主要建立在自然的大环境中,对于“自然”的崇尚已到了无可附加的程度,而后者则主要基于在固定之所营建出自然环境的真实感受。秦时关中之地的山里河谷、物产之资的美丽与丰饶,由此而兴起的帝王苑囿之筑显然是大自然的衍生物。

二、多元的苑囿组成溯源历史
《说文》记载:“苑,所以养禽兽也;囿,苑有垣也。”
西周时期,园林多称为“囿”,此时“囿”的主要功能在于圈养野兽以供贵族与王侯射猎之用。其实“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殷商时期,殷商时期的苑囿营建多借助于自然环境的天然所成,将环境中的草木野兽以及猎取而来的珍奇异兽,狗马蛮鸟等物放养在自然环境当中让其孕育滋生,繁衍生息。另外还令工匠挖池筑台,使之成为狩猎之余休闲娱乐之所处。
殷商之后,对于苑囿的营建逐渐趋于多元,除了狩猎为主导的苑囿活动之外,还在苑囿中筑宫设馆与营建帝王的临时寝居之所。至秦时,“囿”才逐渐改为“苑”或“苑囿”之称,其意思本身包含着动物、植物、山水、观赏、狩猎、寝居等多元的文化构成。秦代苑囿相较之西周时期,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规模也甚为庞大。

在秦代上林苑中所囊括的宫室殿台甚多,朝宫就是规模巨大的建筑群落在苑囿中而营造的,此时的皇室苑囿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涉猎、园游赏景之所,而是融入了礼仪、权威与政治的多元因素,皇帝不仅可以在此打猎游玩,而且还可接见各国使臣与臣子,处理国家军机大事等等。
秦代在上林苑的营建中除了巧妙利用了长安八水的自然条件之外,还有许多人工湖泊与之相伴。自然之川流与人工之灵沼分流而并列,泉源的充沛殷丰与如织之渠涧可使土壤肥沃、林牧葱郁、鱼跃而鹤翔。尽管阿房宫以及其附属建筑随着秦末的战乱,与硝烟而毁于一旦,但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天然风景,确是不能被战火所泯灭的。
苑囿在秦时只是皇帝王公的专享,百姓只有修建的权利,而并无任何出入苑囿的权利。如在秦时,县应竭力征发刑徒为苑囿建造堑壕、墙垣以及籓篱,若遇经久失修之处就应尽快修缮,修毕后上交苑吏审核。若不满一年再有损毁处,就应由该县重征刑徒修之。

与此同时,其还应承担苑中牛马的牧养,就此秦代中央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厩苑律》,建立了牛马户口的登记与注销制度,在对于牲畜饲料的征收与支付,以及其养训使役与饲养优劣的评比等方面,都有着一系列明确的规定。
对于珍禽异兽的钟爱是秦代帝王营建苑囿的主旨之一,秦代苑囿中禽兽众多,有诸如鹿、牦牛、熊猫、水牛、象、野马、骆驼等,如此品类众多的禽兽都是为了帝王的射猎而预备的。秦人最早从西陲之地一路披荆斩棘,其林牧的经济形式占据了封国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射猎成为维持秦人生活的主要途径。
随着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的确立,射猎反倒成了皇室贵族们豪华的一种享受方式,而此时对于天然林区,抑或是皇室的苑囿,平民皆不准任意捕猎,即使捕杀也仅是在政府所划定的区域内,同时它们也都被列入“山泽税”的范围。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当秦代帝王统治时期,苑囿成了其彰显权威与荣耀,丰富生活意趣的主要场所,那么理所当然在其死后仍然需要相应的苑囿,作为自己身后的皈依。始皇陵中的山、水、环境以及宏伟的陵区建筑,都彰显了皇帝视死如生的价值意识。
三、秦人苑囿中所蕴含的设计法则
在中国园林的发展历史中,秦代苑囿艺术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承接,其使苑囿艺术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由单一向多元发展的价值构成之路,其间融合了统治阶级比附性的价值思想,同时也与工艺匠人们高超的筑造技艺须臾不分。
秦代苑囿在建造过程中有着典型的秦人标签,既融合了三代以来的传统“囿”之营建法则,又比附了秦人法天,尊天人秩序的崇高极权价值。借山之势,行水之灵就成了这一时期苑囿营建的必要法则。关中形胜,往往是帝王苑囿之地的最佳选择。

《战国策》记载:“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
“囿”的营建往往立足于自然环境的美轮美奂,而并非有过多人为价值意识的融入,其实际用途也不过是君王圈养珍禽异兽的自然山林,而秦代的造园者秉承了帝王法天而又比附于天的价值意识,在对造物尺度的把握中考量着自然中的山水与林木。
秦人在苑囿的建造中对于尺度的权衡已近极致,工艺匠人们将宫室楼台与水榭池亭等实用型建筑,巧妙地浓缩进大自然无限的风景之中,使君王在宫室与亭台之中就能欣赏到自然界中的奇峰、异石、流水与湖面,同时还能观赏到各类名花异草,珍禽异兽。这种将实用的尺度融入自然的环境中,所营造出的苑囿空间是后世仿效的典范。

规模宏大,雄伟壮观的苑囿内之宫室建筑,若同巍峨的崇山峻岭以及无际之葱郁林木,相较定然会影响其尺度感,然设计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规律,从而增强了尺度对比中的视觉冲击。
以山岭为背景依托,将宫室的营建作为苑囿的主体建筑,弱化周边的亭台水榭等辅助性建筑集群,再配之以纤弱的名花异草与珍禽异兽。在如此的苑囿构成中通过不同形式之间尺度的对比,使得主体建筑在周围不同尺度的景物的衬托下,凸显出其高大雄伟,壮观迤逦的艺术形象。
结语
秦代苑囿还可以被视为朝野政权的象征,是封建中央集权制下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主要场所。三代以来游艺性的单一功能,在秦时已然被统治者赋予了多元的价值含义。这种宫苑结合的苑囿规划至汉唐时已经日臻完备,逐渐形成了“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的新型苑囿格局。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
[2]司马迁,《史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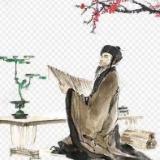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