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瓶词话》第七十二回,王三官拜西门庆为义父。在林氏老太太的主持下,敬酒礼毕,安席坐下,小优弹唱《折桂令》,其中一句唱道:“娇滴滴争妍竞宠,幸孜孜倚翠偎红。”幸孜孜,形容男人“倚翠偎红”时得意高兴的样子。我是在中学当老师的,用民间乃至某些名人作品中的叫法,是个“教书匠”而已,地位平平,囊中羞涩,因而没有资格,没有条件,其实也没有心思“倚翠偎红”。但是,“幸孜孜”得意高兴的样子,倒是时有出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的工资还很少。1960年走上工作岗位时月薪只有43.5元,第二年转正,工资为44元。直到1978年第一次涨工资,才涨了6元。上有老下有小的,只够养家糊口。家庭虽然不富裕,但就我个人而言,在某些方面,竟然有过与众不同的特殊享受,因而时常“幸孜孜”。有诗为证:
常坐轿车好心情,
偶住别墅入梦境;
父子摆阔上“国际”,
哥们霸气进“和平”。
(一)常坐轿车好心情
我有工作,是当老师的,但只能算个穷教师,借人一句话说,“饿不着,也富不了”。但是,我比一般老师幸运。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很多人还没有自行车骑的时候,我已经有轿车或面包车坐了。
最早,是我在上海老家担任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大哥有一辆座驾。这辆车是香港的一位华侨大老板回家乡探亲时赠送的,时间大概在1975年前后吧。这在当年,上海郊区各县人民公社一级的党委书记,不可能有座驾,至少在我老家宝山,是独一无二的。它形似面包车,车头的标记像一只大头钉,在香港属于“私家车”或“工具车”,三排座,便于一家人出行或购物。我每次回老家上海,大哥就派驾驶员去车站接我。乘坐方向盘在右边的香港车,感觉那么宽敞,那么稳当,那么快捷,那么舒服,听不到一点干扰音,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特殊享受。文前图片,拍摄于1980年8月,是大哥(左)小哥(中)和我,兄弟三人在上海外滩公园,以上海大厦为背景拍的照片,身后就是我大哥的座驾。
之后,我小哥的女婿王德兴创业有成,先买了一辆面包车,后换成一辆轿车。我回上海老家时,或者在老家想去哪里时,他都会开车接送。后来他女婿徐巍峰也有了轿车,就接老丈人的班,负责接送我。
同时,宜兴小连襟马盘余开了建筑公司,有两辆轿车,一辆是他的座驾,另一辆公用。我是宜兴女婿,每次与爱人去宜兴,他会派驾驶员到车站接;回上海时,也会派车送。有几次,竟然派车到邳县来接我们去宜兴呢!
而后,在邳县当官的许多学生都有轿车了。我想去哪里,一个电话,学生就派车过来接我了。
最后,我儿子孙子也有轿车了。我只要出门,随叫随到。他们带我回过上海,去过江苏苏州、徐州、宜兴、泗阳、淮安、盱眙,连云港,去过山东郯城,去过河北保定……
有一次回家乡母校顾村中学,探望在那里当校长的老同学苏永发。那已经是九十年代的事了,听说他去宝山教育局开会,还是骑自行车来回。我就笑话他:“你当个校长有什么用?还不如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呢!我要出门,打个招呼,小轿车就开过来接我了!”
常坐轿车,心情当然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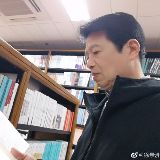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