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氛又到这里了
4月中旬,云南八谦律所把中国PPP领域的权威专家王守清请了过来,核心主题是讲最新的特许经营政策和实操要点。
律所的朋友最初还担心报名人数不多,答应给财哥留两张票。结果第二天就很抱歉地告诉我,只能给我匀一张,会场需要不停地:
加座加座加座。
不少政府部门领导和国企老总都来了。他们希望知道在下一个机会中,自己能捕捉到些什么。
积极的背后,是在新的一揽子化债政策下,城投公司不得不被卷入的转型浪潮。
发改委更是显得时不我待,几个月内一箭接一箭。到5月22号的协议范本出炉,PPP新机制的主要规则全部落地,前面还包括115号文、17号令、特许经营方案编写大纲、PPP项目信息系统。
常练大宝剑的朋友跟我说:
这是真正的全套。
城投公司成为政府的钱袋子,是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的。而狂飙始自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尤其是后者的四万亿放水,各地政府开启影响至今的财政扩张政策。这个过程中,政府曾一度可以直接向银行借钱,但后来被掐断,城投公司就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唯一平台。
在这段时期,城投公司还多了两大角色:
城市建设主体、城市重大资产经营主体。
同时在膨胀的还有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债,更多的是城投背负的隐债。
2010~2012年,国家看不下去了,国务院到四大部委连发几道金牌踩刹车。的确冷下来了,同时被紧缩的还有各大银行的贷款规模,各大投融资平台也没有逃脱“一抓就死”的局面。
分水岭出现在2014年。
当年直指地方债的43号文要求,融资平台公司必须剥离政府融资职能,还不能新增政府债务。这意味着,公益性资产普遍占到九成的城投公司,如果找不到出路,就面临生存问题。为此,文件还提出了后来都熟知的PPP模式。城投公司就此拉开转型发展的序幕。
十年之后,城投公司大致转成了三类: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城市综合运营商,产业类国企。云南这边省级和市级平台公司,上述类型全部囊括。
不过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有一样东西没有变过——为地方政府融资。另外,完全市场化并未实现。
2024年,又是相似的口吻和局面。海明威对青春曾有过一句扎心的描述:
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藏在时光中的伤痕,终于慢慢浮现。
1
老余还记得2012、2013年自己做过的一单生意,为云南某州市融资。
他记得,当时市长是真急了,贷款利率加顾问费,15%的资金成本连价都不还。县级政府更加困难,都借“高利贷”。那时候,民企老板都不敢说自己账上有钱,都得哭穷。政府这边,只要能搞到钱:
什么条件都答应。
2014年43号文出台后,财政部来主导PPP模式的推动,并意图为城投公司找到新的转型路径。
转型第一步就是干工程,但城投公司没有团队,怎么办呢?抽点。一是跟政府拿管理费,一是跟项目施工方抽点。
后来做着做着,发现还是自己干更挣钱,于是就陆续收编了一些本地的施工队伍,包括做砂石料、混凝土搅拌站等产业链上游的公司。
不过彼时的城投老总们的工作很简单,其实这么多年也没太多变化。他们的核心工作就一样,融资。配套的工作也就两样:
吃吃喝喝,拉拉关系。
第二步是实现人才的专职化和专业化。行政管理色彩浓重的城投公司,一把手之前普遍由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兼任,后来就要求人事关系上与政府脱钩,这是一部分。另一拨老总的来源主要是金融系统。
老余告诉我,2012~2016那几年,民间金融从火爆到崩盘,民企尤其是昆明本土地产企业后面又大量暴雷,而央企是自带资金玩,本地银行的日子并不好过。行长天天当乙方,拉存款、放贷款都得求政府:
但政府日子也难过。
来到城投公司后,至少可以当甲方。
在PPP撒开腿跑了十年后,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多,城投公司的负债也并未改善。
PPP的主导权换到了最擅长管项目、制定游戏规则的发改委手里。玩法也不一样了,通常的路径是,立项后,银行这边首先由国开和农发两个政策性银行带头试水,跑通之后,四大国有银行跟进,然后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这类中小银行就吃点边角料。
与十年前相比,本次城投转型的核心思路就四个字:
提质增效。
老余分析,从宏观层面来讲,基础设施的建设已到头甚至过剩,低效和无效资产实在太多,那么就要严控。以前是搞到钱,就搞工程;现在是先想清楚怎么还钱,才能借到钱。
再说具体点,原来做PPP可以用财政的资金去做无收益项目,现在不允许了,财政资金全部严格管控。还可以靠国债,比如超长期国债,尽管无需财政偿还,但这个钱的使用领域及申报要求也受到国家发改委的严格管控。
以今年的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例,就围绕“两重”建设花钱,具体针对8个方面、17个具体投向,核心要义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鼓励“耐心资本”。用流行的话说就是:
提倡长期主义。
而且资金支持的项目并没有所有制的区分,比如科技研发、设备更新等方面项目,会有民企项目。
最大的难点还是在市、县区两级,省属国企好一些。
前者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作为政府融资的一个壳存在,要转型只能走实体化,但人才和业务体系很大程度上都得推倒重来,道阻且长。国企改革,三年又三年,县城更是壁垒森严;后者更多是考虑产业化,怎么做大做强,怎么提高效率和利润率:
历史根源是不一样的。
市级尤其是县区的财政收入,之前主要靠地产,但现在土地财政走不下去了。老余说,加上上级转移支付,云南的县级政府每年能操作的资金盘子大概30亿左右,平均下来,一个月大概两三个亿的资金开支,其中:
至少百分之七八十要用于“三保”。
此外,找上面要钱上项目,自己还得有配套资金。所以,县委书记、县长也是不容易。
另一位朋友苦笑着告诉财哥,他现在都不敢轻易去见某县的书记,因为该县是朋友所在机构定点帮扶点,书记一见面就开口要钱。
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基础设施在闲置浪费,比如当地建个图书馆花了1000万,又不会商业化运营,配套的铺面都难以租出去。
所以,这轮转型其实就是上面要求地方要更精准、更有效率地花钱了。老余说。
2
债得还,钱也要继续借。症结不在于债务规模,而在于债务风险,也就是流动性风险。
长远的方向大家都清楚,但短期的资金缺口才决定生死。长短如何平衡,是第一道难题。
德勤曾作过一个调研,全国大部分城投每年的业务现金流净额,往往只能覆盖个位数百分比的当年还本付息金额:
保工资都费劲,遑论还债。
不过中国人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钻空子、绕道走。
天眼查显示,2024年以来,各地新成立的400多家国企中,名字或业务涉及产业投资、产业发展的企业数量就达到75家。此外,还有部分城投直接换个名字,就转型成了产业类国企。主要目的就一个,避开城投身份:
方便在公开市场融资。
有句话怎么说的,再丑都要谈恋爱,谈到世界充满爱。万水千山多障碍,唯有融资是真爱。
变身的直接原因是一揽子化债政策下上交所发布的“335指标”,它是指城投非经营性资产(城建类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不超过30%,非经营性收入(城建类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不超过30%,财政补贴占净利润比重不得超过50%。
而且,交易所还对城投转型提出了“城投归城投类,产业归产投类”的指导意见,即城投类平台仍保留原有功能的,现阶段仅能借新还旧;经营性资产原则上允许全部划出成立产投平台,强调从资产、业务等方面向产业类彻底转型:
反正不能是只以融资为目的“半吊子”转型。
“335指标”中,城建类资产包括市政道路、公园这类几乎没有现金流的公益性资产,和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土地使用权、无证土地等政府性应收类资产。
这些对城投公司是包袱,必须降低占比,实现的途径包含并表上市公司资产,或成立新公司,注入非城建类资产。还有些方式就不一一介绍了,反正骚操作挺多。
不少城投也在着力加大经营性资产的占比,盯上了现金流更好的行业,比如:
墓地生意。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地方政府都在鼓励火葬,取消土葬,这就需要建设公益性墓地。这个项目最大的优点是,投资规模小,现金流充足还稳定,几乎可以做到稳赚不赔。财哥就想问:
是不是离开土地就走不动道了?
好像也不完全是,比如城投公司现在就不太敢继续拿地搞地产了。
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全国还在拿地的企业,十有七八都是城投公司,拼命为土地财政托底。但最近明显少了。
之前拿地倒是轰轰烈烈,但真正开发的却寥寥无几。这里面也有秘密——拿完地转手就抵押给银行,套钱用于城市配套服务,然后就是:
给公务员发工资。
世界真是一个草台班子。
转型的第二个难点是,懂产业的城投老总不多,这不是吃吃饭打打掼蛋就能办的事。老张说。他深度参与过不少云南城投公司的转型。
按他的说法,不实战个十年八年,不敢说自己懂产业。这句话朋友也很认同,说就算财哥这么英俊,要写深度财经内容也得有长时间的积累。
多年前,老张曾听一位后来进去的领导大谈过三七产业。领导说,投资三七永远是对的,三七又能治病又能当菜吃,为什么不能做个三七火锅?老张一脸懵逼,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东西永远是赚的。一年之后,领导不说话了,三七价格跌得一塌糊涂:
产业是有周期的。
他觉得,不少城投老总对产业仍然不够重视,对其的研究甚至不如一些政府领导多。最重要的还是心态转变,以前出入的都是豪华场所,谈的都是以小目标为单位的生意,现在得脚踏实地赚慢钱。还有就是,不能用金融思维搞实业。
另一方面,要从上面争取资金,是不是得拿出货真价实的故事来讲,不是随便拿个项目规划报告就可以忽悠:
发改委是懂行的。
德勤的调查报告也表明,城投公司普遍存在可经营性资产占比低于10%的情况,并且,实体产业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产业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在布局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投入,也明显不足。
尽管已在推进市场化,但其业务模式仍受历史顽疾影响很深。
第三个难题是复杂的内部人事关系。
老张说,城投公司老总也难,没有选择上级领导的权利,甚至也没有选择内部部分员工的权利,裙带关系一层叠一层,真正能干活的其实不多。既然人力资源无法有效释放出来,就难谈转型。
以云南的优势产业为例,最大的劣势在于没有规模性,这就意味着高成本。反过来看,没有规模就适合走高端路线,但高端市场:
对人的要求又特别高。
他认为,云南不是没有优秀的本土人才,得把他们用好。云南是一个多元化的省份,这个县适用的产业和发展模式,在另一个县很可能完全行不通,得沉下心来多调查研究,刻舟求剑式地学全国先进地区并不对。
比如一味地追求互联网热点概念、复制热门产业,甚至还有常住人口仅有十多万的县城想搞汽车城,在老张看来,这些都是脱离实际的:
能不能先把茶叶卖好?
3
特许经营会不会是一剂解药?
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明华认为,通过特许经营去盘活存量项目,是目前最可行的选择:
这是政府最关心的事。
而不是什么赚钱就去搞什么,比如新盖一个菜市场,或收购一个停车场。
但从他所接触的城投公司里,大家普遍倾向认为,特许经营只是在超长期国债、专项债之外的另一种融资工具,而且做新项目更容易出政绩。
姚明华说,城投转型最难的一个点还是企业领导的固有思维,老是在原来最熟悉那个圈子里边绕来绕去:
有什么用呢?
特许经营本质上是给城投公司寻找出路并以此逐步化债,同时也鼓励民间投资。但在老PPP时代,会时常出现没有民企愿意参与导致项目流标,最后还是交给国企运作的情况,同时也伴随着国企转型可能会挤压民企空间的问题。
这次会不会重蹈覆辙?
姚明华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理解,的确存在一些案例,但中国整体越来越市场化,民企、国企都是企业,都是市场竞争行为。除了企业卷,政府之间也是相当卷。
他所接触的央企也都是高度市场化的,项目经理拿基本工资,出差费都自己掏,拿不了项目就没奖金。相对之下,本土国企尤其是区县一级:
市场化程度不够高。
民企是不是一定弱势,也并非如此。他觉得,还是取决于自身的竞争力。要与央国企竞争,民企必须是最优秀、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那一部分。
就云南而言,不少民企都是从矿业、工程、农业、地产等拼出来的,但在后面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没有跟上脚步。如果因为这个而拿不到好项目:
怪不得别人。
在他看来,经济转型期或疲软期往往是做企业的黄金时段,因为假话少了、实事多了,竞争也相对更公平。
财哥最近也看了很多关于城投化债和转型的资料,感觉大家都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思路。
从化债角度看,目前主要方式就这几样:控增化存、降息展期、压降支出、盘活“三资”、财政金融协同化债。说到底,都要:
以时间换空间。
关于转型,大方向都明了,但操作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财哥捋了几个代表性意见出来,感觉每一条都打在七寸上。
一是特殊再融资置换后,隐债变成地方政府的明债,那这笔钱算城投公司欠政府的,还是政府以资本金的形式注入或者补贴给企业?城投公司以后还要不要偿还给地方政府?
二是县级政府,根本无力支付给城投公司各项欠款,后者就只能再去融资还债续命,这也导致非标融资继续增加,融资成本还高。一屁股账,怎么转型?建议用银行资金置换非标高息债务,但银行会同意?
如果脱离特许经营权,县区级公司大的项目玩不动,因为资金需求大;小的项目又不能玩,会与民争利。还有就是人才储备和自主权,都不够。新增转移支付能不能向市县倾斜:
你说呢?
三是停息挂账,先缓解付息压力,再由政策性银行接手,逐年解决。没有收益的业务不要强加给城投。上级领导可以到地方挂职半年左右,摸清基本情况。
四是股权融资,但对企业的经营能力要求较高,毕竟投资人要赚钱。而股权信托类的手段,又有融资与回购周期短的限制。这些模式,并非城投短期内就能大举使用的。
总的来说,由于城投“功能强、产业弱”的独特性,转型难度确实非同一般。
但姚明华认为,至少先不要有躲的想法,总得想办法去琢磨,冒一定的风险去干。
还是财哥的朋友说得好,这一点该学学某歌手的精神:
三婚天注定,七婚靠打拼。
(老余、老张为化名)
部分资料参考来源:南方周末、经济观察网、新基建投融圈
云财财出品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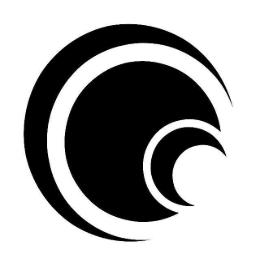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