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段时间,Pussy的爷爷生病住院,全家人轮番上阵陪床看护。但爷爷几乎对所有人的照顾都不满意,只有婶婶和姑姑来了才能安生。
“果然还是女人更擅长照顾人。”爸爸在电话里说。
一句顺口说出的无心之语,却令Pussy有些不是滋味。Pussy的爸爸在家是家务主力,在Pussy小时候也是带娃技能满分的家长,完全能够胜任看护老人的工作。但在全家分工陪护的时候,家里人仍然会觉得“男人粗枝大叶顾不上老人”,更乐意让女性成员去陪床看护。
照顾病榻上的老人绝对是辛苦活,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上述“权衡”之下,家里的女性成员总是会比男性成员更频繁地请假、长时间轮番陪床。
和姑姑还不一样,像婶婶和我妈这样的“儿媳”,并不是作为负有直接义务的亲属在照料爷爷,而只是代替她们“无能为力”的丈夫履行义务。而这样的事情并不只发生在我们家,大部分家庭在遇到有亲属生病需要陪护时,都会这样分工,甚至有儿童医院规定住院治疗期间只能由女性家长陪护,男性家长不能陪床。

但Pussy想问,男性真的照顾不好别人吗?成为“照顾者”的责任,会因为“不擅长”就默许男性的缺席吗?
女性的“照顾者”形象,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人们也习惯称赞一些“女性美德”:温柔体贴、细心耐心、包容接纳,行动上擅长照顾关怀,精神上提供高质量的情绪价值……
对这些美好的品质,Pussy其实非常认同——在女性社群中,姐妹们用关怀和友善构筑起相互支持的关系,是实打实的温暖。但当下的事实却是,“既然你会做、你做得好,就应该你来做”,社会为女性戴上的“美德高帽”,从来不只是单纯的称赞,而是隐形的期待和要求。
婚恋市场中,“温柔体贴”“擅长家务”“工作清闲能顾家”等要素是衡量女性价值的重要指标,男方及其家庭看中的不是女性本身的性格或能力,而是她能为家庭带来的好处。
到了职场上,女性也脱不掉自己的“顾家形象”——入职被盘问婚育意向,升迁和生育只能顾此失彼,女性在职场中总比男性多一道“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送命题,出题人以提防的姿态考察着女性,默认她们总会在某个时候“回”到家庭。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照顾者”角色性别化的一面是被苛求的女性,另一面是被放养的男性。

对一部分男性而言,“男性不擅长照顾人”是一块免死金牌,能让他们在家庭中顺利隐身,轻轻松松开脱自己,将照顾的职责压给女性。问就是不会,做就给你搞砸,反正老娘老婆最后会来给自己擦屁股。
而对于另一部分男性而言,“男性不应该照顾人”则化作嘲讽,使他们在履行照顾责任和违背“男子气概”的夹缝中两难。
尽管“吃软饭”等指控已经过时,但男性照顾者在大众眼里仍然是特殊的、作为下策的、难以持续的。例如,以“内娱全职奶爸”闻名的李承铉是大众眼里一个较为出色的照料者,但让Pussy不习惯的是,媒体往往将他的经历以“奇观”的形式呈现,作为一个“男代女苦”的例外范本被观察和点评。
人们喜闻乐见带娃综艺中手忙脚乱闹出笑话的爸爸,却不能想象一个男人能真正全职照料孩子。或许他们更习惯的是像傅首尔前夫那样“赘婿为尊严出走”的叙事——看到“女强男弱婚姻不靠谱”的模板,就轻飘飘点评一句“果然男的不适合照顾家庭”,继续巩固性别化的照顾模式。
就这样,照顾者角色成了女性的“天命所归”、男性的“逆天而为”。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根据pussy的观察,所有支持女性“照顾者”形象的证据,无非是在说女性更富有利他的品质——照顾就是一项纯粹的利他行为,为不具备独立能力的依靠者提供关怀和帮助,使依靠者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质量。
人们总强调女性的品质多么利他,却忽视了他们所要求的那种“燃烧自己点亮他人”的照料并不是一个独立个体能做的、应该做的。照顾劳动与女性的“绑定”也根本不是什么深奥的生理必然,而是父权社会文化为女性设定好的陷阱。
“女性是一种处境”,看看男人就知道了:如果他们也要将自己的生存命运寄托在照顾他人生活、满足他人情绪之上,他们的“利他品质”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比如在单位里或酒桌上对领导嘘寒问暖时,很多男的瞬间就会长出十八道弯弯肠子,并总结出“深刻的经验”供后人学习体会。

父权制下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想方设法服务父、夫、子,比起是天性流露的关怀,更像是换取生存资源的无奈之举。仰人鼻息的生活绝不会有公平的交易,无限利他的照顾必然伴随着对个体自我的剥削。
Pussy并不是想说,女性拥有和发扬利他品质是不对的。只是,我们需要正视照顾的“真相”:很多照顾劳动不能算是“自愿”的,而是维持生活必须接下的“包袱”——做家务、赡养老人、养育孩子……这些义务固然有其价值,但同时是重复的、琐碎的。
宣扬女性的价值是照顾他人,默认照顾义务全由女性承担,无限压榨女性的时间和精力使其包揽照顾义务,这些是不可取的。男性也应当公平地参与到照顾的情境中,不是甩手出门不沾家的“消失男人”,也不是在家如同不在的“隐形男人”,而是和女性一道,成为合格的照顾者。
但要达成这个目标,并不是仅靠个别男的有觉悟就能实现的。哲学家Eva Kittay在著作《爱的劳动》中提到,照顾的社会正义需要重视依靠者、照顾者、社会的“三角关系”。社会不仅要为依靠者提供帮助,也要采取措施保护和支持为依靠者提供照顾的照顾者,帮助其顺利完成照料责任,同时不至于牺牲自己应有的权利和生活品质。
所以,一方面,人们的观念需要改变。照顾劳动的价值应当被重视,照顾者的意涵则应与性别角色脱离。“爸爸”代替“男妈妈”,“育婴室”代替“母婴室”,男性顾家不是因为“耙耳朵”“妻管严”才做出的“帮女性分担”的行动,而是源于本身就应当肩负的责任。
另一方面,实践中的支持也必不可少,社会需要提供实际的鼓励政策或建设公共设施。比如制定性别平等政策、提供性别平等教育;培养男孩关心他人、关怀照顾的能力;实施男女同工同酬、育儿假期父母同长制度;重视育婴室、敬老院等基础设施,通过细致周到的设计为人们的家庭照料工作提供便利等。

日本许多育婴室内部分区,除哺乳区男士止步外,其余区域男士可入,并提供护理床、热水机、育儿用品贩卖机等设备,满足育儿需求。
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互相依靠和支持本就是生命的常态,发展利他品质、锻炼照顾能力是人人须有、人人互惠的。这不只是“女性”的责任,而是家庭中、社群中“人”的责任,其中必然也包括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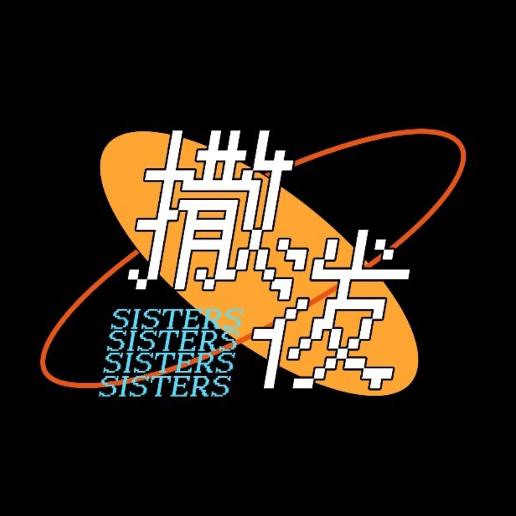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