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四年(1097年)七月二日,苏东坡抵达了生命中最远的一个贬所——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儋州在宋时为昌化军,属广南西路,距宋时的东京七千二百八十五里,万里飘蓬,至徼边荒凉之地。“人间寂绝鬼门关,更指儋州杳莽间”,且此时东坡已是六十二岁垂垂老者!这真是最恶毒的一次贬谪。要问为什么是儋州?是因为当权者的测字游戏,苏东坡字子瞻,据“瞻”得“儋”;苏辙字子由,“雷”下有“由”,所以,苏辙的流放地是雷州。
抵达孤悬海外的儋州后一个多月,便是中秋。九百多年前的海南岛,可不是今天的风景如画,而是蛮荒瘴毒的鬼门关。在宋代,放逐海南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而宋代是不杀士大夫的,所以对于苏轼来说,已是罪无可罪!
从熙宁至绍圣,从密州至儋州,这二十年里,苏轼历经沉浮,经朋党之争、变法之累、文字之陷,为帝师、极人臣、遭构陷、历贬谪……自从小皇帝哲宗摆脱高太后垂帘而亲政之后,“元佑”改元“绍圣”(意在推翻“元佑更化”之政,继承神宗之法),在又一轮新党的支持下,哲宗变身叛逆少年,全面颠覆高太后,实行“报复性”执政。在偏执而日渐扭曲的心理之下,苏轼等一众元佑大臣开始了群体贬谪之路,苏轼于绍圣元年四月以讽斥先朝罪名被贬知英州,未及到达英州已接旨意再贬惠州,惠州初定,再被贬海面,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即儋州)安置,没有最远只有更远,最终到达不能再远的儋州。
环视月色下的天水之际,苏轼忽然了悟,儋州之地,的确是浮于海内的孤岛,而整个山河大地,又何尝不是浮游于大千宇宙中的孤岛?芸芸众生的几十年,无非也是世世轮回中的一个孤岛而已。所谓人生如寄,人人皆蜉蝣一般,又有谁不是孤岛?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苏轼心神洞明,《西江月·中秋和子由》一挥而就,成就又一首千古不朽的中秋佳词。东坡居士”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遥对前代李白”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两代谪仙,当浮一大白!
苏轼另一首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于宋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彼时他在密州任上,刚刚战胜了严重的蝗灾。文名与政声皆隆的苏轼,中秋与同僚朋友喝酒赏月,谈天论地,通宵达旦。
对于天才来说,从不不会满足于世事的热烈。当客人散去后,苏轼酒醒兴尽,遥思七年未能相见的弟弟子由,天地旷然知音稀的孤独漫卷而来。他怀念那个笃实温暖的子由弟弟,当周遭充斥着虚假、谄媚和无处不在的别有用心时,子由那清澈的手足温情便更让人想念,他是洗涤苏轼烦扰的山泉,也是给予苏轼内心力量的泉源。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儋州的明月与京师同此清辉,然而今日的京师,已没有与苏轼共此明月的人了。就在苏轼人生最后一轮贬谪尚未来临的元佑八年(1093),五十八岁的端明殿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苏轼,失去了陪伴自己二十五年的妻子王闰之。绍圣三年(1096),一直追随在东坡身边不离不弃的侍妾朝云,也于七月病故于贬所惠州。绍圣四年(1097),安葬了朝云的苏轼,再被贬到儋州。此时他已经失去了生命中三个最爱他的女人,以垂老之身被迫孤萍漂泊,汲汲天涯。
在我们的印象中,无论显达困窘,苏东坡总是以豁达通透,超然达观与天地化一的形象出现。仿佛他从来道骨天成,不管身处何种境地,总能瞬间超拔出尘臻于化境。这样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再达观的人,遭逢变故都有一个思索、消化的过程。从绍圣元年(1094)至今这四年中,朝廷将苏轼一贬再贬,一远再远,以至天涯……儋州与世隔绝孤悬海外,从宋域的地理位置上说已是贬无可贬。如果不出意外,苏轼终将老死天涯。
垂老投荒的苏东坡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清苦生活。“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落枕前”,这是苏轼《和陶怨诗示庞邓》的诗,与《西江月》中“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正成呼应。在《与王敏仲书》中他写道:“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书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初到儋州他就做好了必无生还的准备。
“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对于一个如此爱苏东坡的我,写到此处,不忍下笔。痛苦、郁闷、绝望的东坡,令人心痛。时值中秋,佳节思亲,他遥想起同样遭贬谪在雷州的弟弟苏辙,“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一辈子都心心念念要“夜雨对床”的两兄弟,愿望也终将如梦了。
《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世间一切都是虚妄不真的,心生法生、心灭法灭,如梦,如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只此两句,便道尽世间况味,说尽万语千言。爱过的人,走过的路,写过的诗,飞扬过的雄心……一切是否也如梦?
在惠州时,朝云临终口诵《金刚经》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东坡将她葬于栖禅寺旁,并建六如亭纪念,做铭文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维摩天女般的朝云,终究别了她的子瞻,了尘缘飞升而去。人天相隔一年之后,东坡已远在儋州,竟连朝云的墓也望不见了。何止朝云,王弗的墓地,只在梦里的明月夜、短松冈,闰之夫人的灵枢,一直还停放在京西寺院,虽然立下了与她“唯有同穴,尚蹈此言”的承诺,然而不知道此生还能否践诺。啊,浮生真如大梦啊!与佛道缘极深的东坡,内心老早就有浮生如梦的了悟。
关于人生如梦如寄,在儋州时苏东坡还有一个“春梦婆”的典故流传。赵令畴在《侯鲭录》记述:“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
负大瓢行歌于田间,东坡这个形象已几类于庄子了。至于在现实中是否真的有这个“春梦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历经宦海浮沉的苏轼,内心精神世界已然静敛与彻悟,借着与春梦婆的对话,说出自己“人生如寄”“世事如梦”的了悟。在儋州时的东坡,是生命历经磨难后的复归自然,俗世、人生、世界、天地(宇宙)都可以化入茫茫的空漠中。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当月色照入宗朝绍圣四年,我们会看见茫漠天地间,一轮儋州月,与一个六十二岁的苏东坡,在历史中皎然孤悬,皎然孤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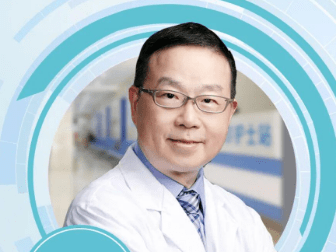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