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迷惑,从盛唐到五代,一个开放自信,军功强大的超级大国怎么就转变为武人当国、以下克上、分裂割据的破碎板块。
其内在的原因,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简单来说就是隋唐下层的土地分配制度均田制遭破坏,导致府兵制没办法维持,最终募兵脱离了制度的控制。从而最终造成了军阀割据。
一、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
均田制是从北朝开始实行的制度,指的是国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在得到土地使用权后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比如上税(租庸调制)、比如跟随国家打仗。土地属于国家,理论上来说分给你的土地在你死了之后要收回,在重新分配给其他人。

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就说的是府兵出征要自备相应装备
看似很美好的制度,而且北周隋唐武功强盛都跟均田制和府兵制有很大关系。但是大家发现,均田制只能在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情况能实行。事实上到了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期均田制已经开始实行不下去了。人口增长,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
对应的,府兵对于一次性的战斗有优势,但府兵说到底还是临时军队,面临作战时间不能长和作战半径短的问题,府兵是自己劳动、自己准备作战物资,时间长了,家里的地谁来种,不种地没收入,不要说买装备了,饿都饿死了。而且对于需要建立人身依附关系相互信任的军队,比如皇帝的亲卫部队,杨广时期就开始国家出钱建立骁果卫(就是最后弑杀杨广的那支部队)了。
这些在唐朝统一战争时期还可以克服,但后来唐朝疆域扩大到极限,边疆要留兵驻守,需要职业军人吧。唐朝与西边的吐蕃,南边的南诏、北边的突厥回鹘等随时发生战争,而且李隆基又是一个“开边意未已”的雄主。需要一支稳定的、职业的军队来驻守边疆。长期与异族战斗的西北(与吐蕃)、东北(契丹、奚)、西南(南诏、吐蕃)需要厉害的将领长期带领才能保证战争胜利。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要让将领集中所有资源用于战争才能打赢吧,不然发现敌人大将先去找军需官写申请,一套冗长的官僚程序走完,敌人也走了不是。

久而久之,处在边疆的节度使就成了集一方军权、财权、人事权等一切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
然后那些游牧民族还是流动的吧,在幽州打败了他们,万一他们跑到河东来怎么办,出于事权统一的需要,一个方向的节度使是不是由一个可以信任的大将总揽全局会更好呢?所以就出现了王忠嗣这样兼任西北四镇节度使和安禄山这样兼任东北三镇节度使的超级军头。
二、安史之乱后藩镇和朝廷的实力平衡
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王忠嗣到死都忠于大唐,所以很多人没听说过他,而安禄山一脚踢翻了大唐盛世。在对付安史叛军的过程中,朝廷要让政府军有战斗力,同样给了很多政府军头领节度使的头衔,方便他们便宜行事,战后这些藩镇得已保留,导致原本只是为了边疆战事的节度使制度在内地遍地开花。

然后一连串中央和藩镇的角力之后,大唐取得了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的平衡,在这个平衡中又度过了150左右。这个过程中如果皇帝强势一点、有能力一点就拿几个不听话的藩镇杀鸡儆猴,想方设法扩大一下中央权威,皇帝弱势一点,没有能力一点就被宦官、大臣、藩镇等欺负一下。
但其实真正欺负皇帝的主要是宦官,因为首先唐朝中央掌握一支精锐的神策军(在宦官手里)。单独对付任何一个藩镇造反没有问题,其次中央有大义名分,单独一个藩镇造反只要中央一纸诏书,周边想着吃掉你扩大地盘的藩镇马上像苍蝇闻到雪一样群起撕碎你。
三、微妙的平衡被黄巢打破
这样的平衡如果没有外力破坏,可能还会维持一定的时间,可惜遇到了黄巢,所谓的流寇可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某个藩镇的范围内活动。他是全国流窜作案,而且破坏力惊人,过程中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单个藩镇显然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中央开始授权一些节度使节制一大片地区,方便统一剿灭农民军。

这个过程在黄巢起义被剿灭之后,众多的小藩镇也就变成了几个地盘广大、实力雄厚的超级强藩:李克用、朱温、王建、杨行密。这一串名字吹响了后续五代十国的号角。
而地盘扩大了的各藩镇看着连唯一的神策军都被灭的一干二净的大唐皇帝,就好像当年的曹操、袁绍等人看着汉献帝。大唐这座大厦就这样倒了。
而五代十国武人当国的时代就这样来了,毕竟五代十国每个朝廷的前身都是大唐的武人节度使。“兵强马壮者为天子”。这批武人不最后打出一个胜利者并想出解决武人跋扈的制度方案这事不算完。

总结:从大唐盛世到武人当国的五代十国,其实有一连串演变的逻辑链条,最开始的原因,其实还是均田制的破坏和府兵制的解体,大唐尚武的传统埋下了最终被反噬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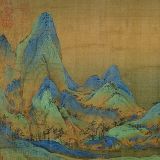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