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受美国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力捧的伊朗裔美籍导演拉敏·巴哈尼(Ramin Bahrani) 在他的新片《白虎》(The White Tiger)中,让镜头暂时离开美国的底层人民,对准印度,讲述了一个被很多人称为”印度版寄生虫“的故事。
在这个阶级分化严重,古老宗教传统根深蒂固,却又极其渴望现代化的国家,巴哈尼的影像里不再有那么多对角色的同情,更多的是用冷峻的视角对阶级关系的深刻临摹和剖析。
文:跑跑
编辑:抛开书本编辑部

影片开头,身为仆人兼司机的巴拉姆身着印度王子服饰坐在后座,而主人阿肖克和他的粉红夫人(pinky)正在驾车,三人转换身份后似乎相处融洽,但怪异感在霓虹灯的衬托下始终存在。
就在路边穷人的镜头一略而过之后,车内的平衡很快被打破,粉红夫人驾车撞上了路过的女孩。这是故事的开始,也是又一个轮回的开始。
在印度的佛教里,人死后,灵魂会离开人体进入新的生命体,直到达到涅槃,方可摆脱轮回。也就是说,轮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过是“上下浮沉的生死流转”,同样的残酷与绝望一次次上演,毫无例外。

这场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印度的轮回的主角有三个:成长在印度贫民窟的仆人巴拉姆,赴美留学的主人阿肖克与他在美国长大的粉红夫人。
阿肖克是家族产业的继承人, 他既渴望继承家族财富又渴望得到女友的认可。粉红夫人是美国梦的代表,第二代移民通过努力学习终于考入名校,实现阶级跳跃。巴尔朗从小就被贫困折磨,立志要赚取财富,打破轮回的神话, 成为人上人。
作为仆人,巴拉姆总是笑脸迎人,对主人们百依百顺,这帮助他突破了阶级的壁垒,参与到主人的关系之中。尽管三人表面上相处融洽,但每次当他们回到家里,他们都会意识到他们只是外来者,无力去改变任何事情。

在美国长大的粉红夫人从未想过长居印度,而在丈夫的家里她也从未受重视,因为她是唯一的女性,且她并不懂得在印度办事的条条框框。在巴拉姆衣锦还乡后,他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尊重,反而要背负上更重的责任,整条村的人都在渴望着吸他的血,他不得不又迅速逃离。
在印度这个最大的国家里,影片似乎也在暗示着,作为财阀的阿肖克家族只能扮演一个外来者的角色,他们不能了解或者改变社会运作的结构,任由摇着“脱贫”口号的政客骗取人民的选票。

从上到下,影片中的人物都处在一种被压迫的,不得其所的状态中,阶级跳跃的梦想被黑洞缓缓吞噬。
尽管巴拉姆处于受压迫的底层,无论被如何侮辱与虐待,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标准笑容,我们无法透过表情读出他的内心,只能通过他的独白(同时也是在对资本献媚)来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的内心也只有一种声音,那便是“赚钱第一”的丛林法则。
即使是在他努力向我们袒露心扉的时候,他也没法听见自己真正的声音,能听见的只是一个叫巴拉姆的人在读着自他童年起便写好的稿子。如他独白所说,与他同样长相的人在印度有千千万万,巴拉姆成了一个符号,他可以是那片土地上的任何人。

长时间地受屈辱也无法改变巴拉姆脸上的笑容,甚至分不清他是过于习惯于奴性,抑或是真的如此执着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作为底层仆人的命运终究会向他砸来。
当主人撞死女孩,巴拉姆被迫为主人顶罪。当他签下承认自己犯罪的名字时,他的微笑终于被茫然取代,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满。只有之后他得知自己无罪的时候,他的眼里才终于泛出泪光,我们才第一次通过他的脸来获知他的感情,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用言语(巴拉姆的独白)讲述的故事暂告一段落,影像终于成了表达情感的首要工具。

主仆之间的信任消失,从内部消解阶级的梦想化为泡影,巴拉姆终于不得不做回原来的自己。最后二十分钟,影片一改之前的叙事角度,将巴拉姆的感知影像化,一时跟着他的思绪漫游,到他的意识深处,在日常街头与死去的父亲对话,一时感知他所感知,摇晃的镜头跟着他在嘈杂的路上踉踉跄跄地走。
巴拉姆重新成为森林里的一头野兽,知觉灵敏,随时准备猎食,能感觉到一团火在他心里燃烧。

重新成为野兽标志着一个轮回的结束,也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巴拉姆实现阶级跳跃后,雇用了更多的工人,更多的巴拉姆正在涌现,财富取代了他们的信仰,而阶级的升降代替了生死轮回,人们对于涅槃的想象仅限于财富增长,也就再无摆脱轮回的可能,这是导演提供的直白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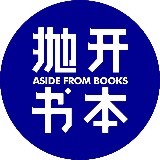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