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而言,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在中国公众中的知名度,与霍金当然未能同日而语。在中国的科学界和科普圈子里,道金斯可能差不多和卡尔·萨根有着类似的知名度。不过道金斯的星路历程与霍金和萨根都大不相同。
《自私的基因》一举成名
道金斯出生于非洲肯尼亚,8岁随父母迁回英国,在牛津大学拿了动物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科学博士等一堆学位。
1977年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一举成名,时年36岁。道金斯认为自然选择并不是为了保证物种或个体生存下来,而是为了保证基因生存下来,他的观点可以归属于“新达尔文主义”。

但是出版商和媒体之所以看好《自私的基因》,另有重要背景:两年前,威尔逊(E. O. Wilson)刚刚出版了引发巨大争议的《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1975),鼓吹道德、侵略性、宗教信仰、性别角色等等都与进化有关。而从二战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利用生物学来解释人类行为已近于禁忌,因为这和纳粹的“优生学”无法划清界线。所以威尔逊的观点遭到西方一些左派学者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牛津大学出版社感到《自私的基因》即使不能给这场争论火上浇油,至少也能借这场争论的东风。
《自私的基因》出版后大受好评,英国广播公司的科学栏目《地平线》(Horizon)当月就为《自私的基因》做了一档节目,道金斯在节目中接受了采访。《自私的基因》被《纽约时报》誉为第一本阐释新达尔文主义的通俗著作,还为后来的阐释竖立了标杆。《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这是“有关人类的最冷漠、最不人道且最让人迷失方向的观点之一……它的见解如此深刻。”
当然批评也是不可避免的,左翼批评者甚至认为《自私的基因》是在为撒切尔夫人的政策提供生物学理由,“撒切尔在社会层面上的政治个人主义反映了基因层次上的自私。”
丹尼尔·希利斯对《自私的基因》有一句酷评:“我对道金斯唯一的不满,就是他将自己的思想解释得太清楚了,读他的书常常会附带着产生一种幻觉,认为事情比它们实际上要简单得多。”这句酷评明显揭示了《自私的基因》的写作风格。
无神论者和《上帝的迷思》
《自私的基因》让道金斯获得了学术声望和社会名声,这种名声也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了学术地位,例如他1995年获任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教授”教职就可以视为这种转化的表现。此时他距离一个科学明星已经不太遥远了。
随后道金斯出版了《延伸的表现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1982),拓展了《自私的基因》中的观点。几年后他又出版了《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1986),开始挑战神创论。

这里需要提到另一个重要背景:进化论和神创论的斗争。神创论在20世纪70~80年代“上升为一种文化力量”,形成了某种“运动”,为了强调自己的“科学”色彩,神创论者会自称“创世论科学家”。有一个“神创论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在此期间在美国搞了300多场公众讨论会,神创论得到许多人的支持。1982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当时美国人中有44%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进入90年代之后,神创论逐渐演化为“智能设计论”,认为生命形式如此复杂,只能由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设计出来。
道金斯的《盲眼钟表匠》加入了对神创论的批判,两年后它的平装本登上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榜亚军,《悉尼先驱晨报》说它是“有关进化论与神创论辩论的当代状况的开创性著作”,《地平线》又为这本书做了节目,仍请道金斯自己来讲。
此时道金斯和另一个维护进化论的学者古尔德(S. J. Gould)都成了“神创论最明显的敌人”。道金斯和古尔德之间也有分歧(道金斯认为自然选择只在基因层面发挥作用,古尔德认为自然选择也在有机体、群体和物种层次发挥作用),两人各有一帮追随者,相互之间也进行辩论。有人讽刺辩论的两造都是“深谙世故的自信满满的自吹自擂者”。道金斯被称为“达尔文的灰狗”,《旁观者》杂志说“道金斯看起来是科学雇用的打手”,《每日邮报》说他是“花言巧语且自信满满的表演者,不仅利用他的立场来削弱对上帝的信仰,而且还竭力主张许多人觉得可怕的科学冒险主义。”
2006年,道金斯出版了《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这本书被认为是“对宗教和信徒的全面抨击”,在全球销售了至少150万册,成为“缺乏公众发言人的全球无神论者的一个标志性文本”。读者甚至能够感觉到道金斯在书中对宗教的某种仇恨:“历史上的宗教狂热者诉诸折磨和死刑的手段,诉诸十字军东征式的宗教战争和圣战、清洗和大屠杀,诉诸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这一点也不奇怪。”
随后,道金斯成立了“理查德·道金斯理性和科学基金会”,建立了理查德·道金斯网站(Richarddawkins.net)。他渐渐习惯了享受崇拜者的吹捧,被尊为“无神论之神”,甚至连“道金斯万岁”也出来了。至此道金斯跻身于某种领袖人物之列,但这种领袖身份已经和科学本身渐行渐远,道金斯也不再是写《自私的基因》的那个道金斯了。
文化基因·觅母·迷因
《自私的基因》出版4年后就有了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81),它和《物理世界奇遇记》(Mr. Tompkins in Paperback,科学出版社,1978)以及《从一到无穷大》(One , Two, Three,……Infinity,科学出版社,1978)成为我念大学期间最喜欢的科普读物。
平心而论,《自私的基因》并没有提出什么新发现,只是对人们已经了解的事实给出了新的解释。但道金斯自己另有高见:“一个科学家能做的最大贡献,往往不是提出新的理论或者揭露一个新的事实,而是发现一个看待旧理论或者事实的新方式。”这个说法用到《自私的基因》一书上,当然能够产生非常有利于道金斯的推论。我甚至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加有利于道金斯的例证——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就完全符合“看待旧理论或者事实的新方式”这一性质。
当然,至少在目前,《自私的基因》还无法与《天体运行论》相提并论,今后获得这样地位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倒是《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无法称为新事实)有相当的生命力,至今仍会被学者们讨论。道金斯为这个新概念造了一个新词:meme。
在《自私的基因》1981年中译本中,meme被译为“觅母”(找妈妈),意为“文化基因”。这是一个音译和意译兼顾的译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包括笔者在内)。这个概念是道金斯从生物学中“基因”概念类比而来的,他相信在人类文化的传承中,也有着和生物学中基因类似的东西,并且有着类似的功能。而在近年的中文文献中,meme似乎越来越多被译成“迷因”,这听起来是以音译为主,从意译的角度看,读者其实很难从“迷因”立刻联想到“基因”。
【本文原载于《新发现》杂志2021年第2期,科学外史(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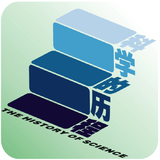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