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巴嫩地处亚洲西部地中海沿岸,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派的中东国家。虽然黎巴嫩本身面积小,人口也不多,但在中东地区的近现代史中却是一个重要的聚焦点,长期为海内外的媒体所关注。
在黎巴嫩众多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中,颇为外人津津乐道的便是黎巴嫩海量的移民。根据其中一组数据统计,黎巴嫩的海外移民多达1500万(其中拉丁美洲的黎巴嫩裔就有700—800万),超过黎巴嫩本国总人口的三倍,因此黎巴嫩与阿尔巴尼亚合称为海外侨民最多的两个国家——后者的海外侨民也是本国人口的三倍之多(阿尔巴尼亚侨民主要在土耳其,保守估计有600万,其中150万是以阿尔巴尼亚语为第一母语;其次是在科索沃,有180万阿尔巴尼亚人)。

● 黎巴嫩海外侨民大致分布情况(来源:Arab News)
在19世纪40年代“黎巴嫩山”政治体被打破以来,各大国一直在这片曾经是“新月沃土”的交通要道争夺各自的话语权,这给本来就宗派众多的黎巴嫩山蒙上一层战乱的阴影;20世纪中叶,随着原属于叙利亚的的黎波里和贝鲁特被殖民体系的干预政治强行并入黎巴嫩和强权政治下的巴勒斯坦领土被占,黎巴嫩更是与周边国家摩擦、纠纷不断。
在这种环境中,黎巴嫩移民在海外散布各行各业,是早期“东方形象”的一个重要传播者——虽然这种历史作用在今天遭到不少人的质疑与批判(例如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就对黎巴嫩基督徒移民塑造的“东方学”存在一定程度的质疑,因为这些早期东方基督徒存在对穆斯林的负面立场)。

● 德鲁兹派穆斯林埃米尔法赫鲁丁一世(绰号长者,图片左边)在1517年受封,成为黎巴嫩山埃米尔国第一任埃米尔,被认为是黎巴嫩雏形产生的标志性事件
黎巴嫩的历史阶段主要是四部分:奥斯曼治下的“黎巴嫩山”埃米尔政府(1517—1843),奥斯曼、法国共治的“黎巴嫩山”总督府(1860—1920),法国托管下的“大黎巴嫩”(1922—1943,是今天黎巴嫩共和国版图的奠基时代),以及1943年独立成国的黎巴嫩共和国。其中,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交界处,因为谢哈布家族的垮台,“黎巴嫩山”发生长达17年的宗派仇杀事件——在黎巴嫩长期具有统治地位的德鲁兹派穆斯林,和得到奥斯曼帝国支持的马龙派天主教徒,就谢哈布倒台后谁执掌黎巴嫩山统治权发生血腥冲突。
虽然天主教徒人数众多,且有宗主国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奥斯曼帝国虽然是以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但对于作为什叶派异端的德鲁兹派容忍度更低,且德鲁兹派埃米尔发动过独立起义),但相比起作战能力更强、“殉教”意识更浓郁的德鲁兹派穆斯林,天主教徒在冲突中始终处于守势。雪上加霜的是,黎巴嫩山南部沿海就聚居着大批什叶派穆斯林(他们绝大多数祖先是被萨拉丁驱逐出埃及的“法蒂玛王朝遗民”,少数是上述伊朗地区的学术移民),他们虽然不主动参与对天主教徒的攻击,也不可能指望他们能收留被德鲁兹派攻击的天主教徒。
因此,赛达和提尔——黎巴嫩山埃米尔总督统辖区为数不多的港口,就开始挤满驶向北非沿岸的船只——因为不仅仅北非的逊尼派穆斯林领主们愿意收留他们,更重要的是,法国在北非有占领土地。这些条件都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相比起死亡和压制,他们更愿意活着,传承薪火。
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批黎巴嫩裔海外移民就此产生。他们乘坐船只离开故土,在开罗、亚历山大港、君士坦丁港等大城市建立自己的教堂、市集与聚居区。
虽然历史上因为奥斯曼与法国的特殊关系,黎巴嫩天主教徒有过不少旅居教廷的神职人员(例如天主教理论家西蒙·塞姆阿尼),但这种形成一定规模社群的格局,也是19世纪以来的产物。

●冲突扩大化后,作为奥斯曼盟友的法国甚至请来原本与自己为死对头的阿尔及利亚起义军领袖——北非知名穆斯林长老阿卜杜卡迪尔,让他和他的“马格里布军团”来黎巴嫩山搭救被德鲁兹派军队围攻的天主教徒和马龙派宗主教。图为马龙派宗主教亲吻阿卜杜卡迪尔的手,感谢他搭救天主教难民。
虽然后来法国、北非穆斯林势力与奥斯曼联合压制德鲁兹派穆斯林的起兵,使得天主教徒暂时避免对方的攻击,但德鲁兹派势力一度的战争狂热让不少当地天主教徒对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存在非常大的心理阴影。加上后来法国、奥斯曼时不时征用当地人去战场当炮灰、镇压本地人的反抗、为数不少的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迁居,以及通往新大陆——南北美洲的航线在贝鲁特港口形成,自19世纪末开始,成千上万的黎巴嫩天主教徒开始“流散”各地的历史。
与绝大多数媒体宣传的“基督教文明生育率低”的刻板印象不同,黎巴嫩天主教徒实际上的生育率是非常高的。在短短的百年间,数万移民能发展成后裔群体上千万、且具有黎巴嫩血统的美洲人数不胜数,核心原因就是安居以后的黎巴嫩天主教移民生育率得以稳定提升。且得益于美洲相对发达的医疗业,移民的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加之与拉美主流天主教的宗教信仰接近,黎巴嫩移民的通婚情况非常普遍。就此,逐步形成大规模的黎巴嫩移民群体——即便是混血,他们通过姓氏和个别名字表达自己的传承与祖源。
典型案例一:前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赫卢

根据卡洛斯·斯利姆·赫卢的自述,他父母(均是黎巴嫩基督徒移民)于1911年在墨西哥结婚,婚后生有11个子女,其中出生于1940年的卡洛斯排行第10。
典型案例二:著名歌星夏奇拉
哥伦比亚著名歌星夏奇拉的全名中有两个阿拉伯语名字:夏奇拉(Shakira)与穆巴拉克(Mubarak),这些来自于她的黎巴嫩先祖祖源。实际上,即便是夏奇拉这种在哥伦比亚已经传承数代、在血缘上已经被拉美本地西班牙人同化较多的黎巴嫩后裔,依然有在少年时代参加海外黎巴嫩移民组织的聚会纪录。

●1988年夏奇拉参与哥伦比亚黎巴嫩裔聚会,她穿着“东方舞”的衣裳翻唱黎巴嫩国宝级歌手Fairuz根据旅美黎巴嫩诗圣纪伯伦写的al-Mawakib所唱的阿拉伯语名曲《我吹笛子你歌唱》
但也并非所有黎巴嫩裔移民能完整传承祖源的印记。因为历史上的纠葛,为数不少的黎巴嫩移民离开故乡后,直接采用西方的名字,以此抹去身上“阿拉伯”印记。例如同样是黎巴嫩移民后裔出身的已故美国航天员麦考利夫,与她有关的黎巴嫩印记只有:她有一个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舅公菲利普·希提。

●克里斯提·麦考利夫(左)父母皆是旅美黎巴嫩后裔,她的祖母便是旅美黎巴嫩历史学家希提教授(右)的妹妹。但在她自身的文化认同和家庭传承中,“黎巴嫩”的因素几乎无从着陆。至她及往下的晚辈,她家族在美国的年轻族人皆无黎巴嫩传承,成为典型的美国“盎-撒”文化组的成员。
这些天主教徒移民在异国他乡,对故土的原生文化具有非常复杂的情感。无论是语言还是姓氏,他们绝大多数都避免不了被外界视为“阿拉伯人”、“东方人”的困局,尤其是同胞内部对于“宗派”概念的争论,和对原生文化态度的不同。
活跃于文化线的黎巴嫩移民,出于对自身文化的珍视与对美洲舆论中对“东方”鄙夷的不满,他们不遗余力在外推广阿拉伯文化。例如黎巴嫩旅美派文学大家哈利勒·纪伯伦、艾敏·雷哈尼、米哈伊尔·努埃曼,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等,他们虽然出身基督教家庭,但他们更倾向于对外宣称自己是“无宗派的阿拉伯人”——至少努埃曼自己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且一直对外宣称纪伯伦“已经远离了基督教”——尽管纪伯伦的遗体最后还是按照天主教的仪式安葬在家乡。
但大多数笃信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与新教体系)的黎巴嫩裔普通人,他们选择远离故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和穆斯林与其他宗派基督徒(主要是东正教徒)之间的冲突,相比起不遗余力推广阿拉伯文化的叙利亚东正教移民,大多数黎巴嫩裔普通人更倾向于与当地文化(北美盎-撒文化与拉美文化)融合。

●旅美叙利亚人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但宗派以东正教为主,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坚持奥斯曼时代的“东方”打扮——例如菲斯帽和头巾,这种情况甚至在凯末尔禁止“菲斯帽”的土耳其全盘西化时代以后多年,旅美的叙利亚基督徒移民依旧保持奥斯曼时代的诸多特征
这种冲突、坚持与交融相并存的局面,对黎巴嫩本国来讲也是多棱存在的历史格局——一方面,黎巴嫩这个外部看来的“弹丸小国”,因为这种多样的历史面貌,其文化发展达到一种中东地区独树一帜的情况——后来随着贝鲁特与的黎波里的并入,黎巴嫩穆斯林比例上升,但后期移民的黎巴嫩穆斯林也在文化上呈现出与天主教徒移民类似的“百花齐放”。
但另一方面,频繁的移民潮、比本国人口更庞大的侨民群体,以及对穆斯林、犹太人和东正教徒既不信任但又有牵绊的历史迷局,使得海外天主教黎巴嫩裔对于“故土”的感情与回馈是非常微妙的。黎巴嫩内战之所以耗时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海外移民对交战各方都有源源不断的支持——这种支持不在于国家利益,而是各自的政治立场与宗派情结。这种与“民族第一、宗派第二”的海外阿尔巴尼亚人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黎巴嫩移民史,在世界史的书写来看,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化史,但对于黎巴嫩自身而言,则是“流散”、“分裂”与矛盾交织的记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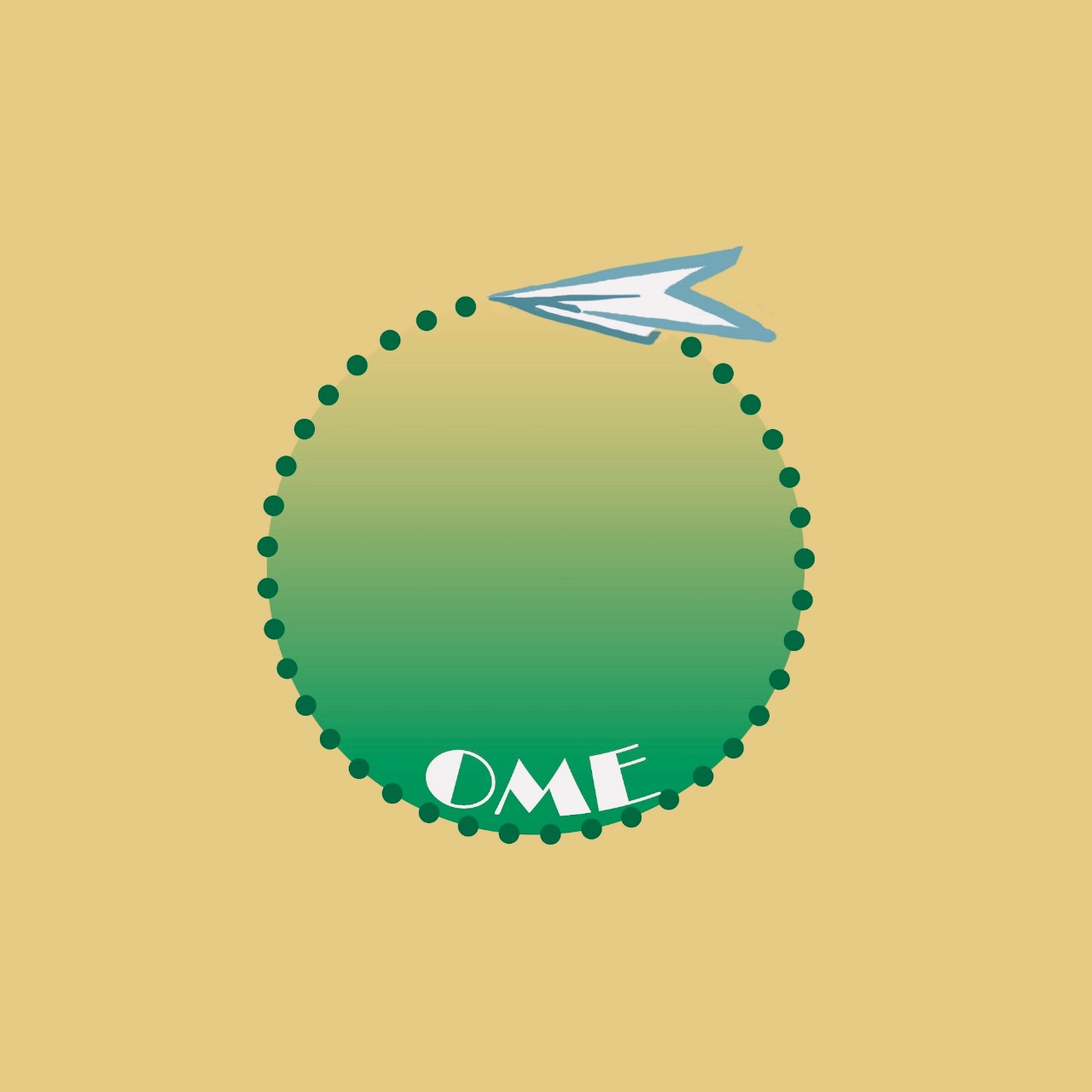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