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第五场,来自青岛的橙乐队主唱魏语诺鲜活得像一条鱼,以俏皮的台风把一曲《花房姑娘》唱成杂夹着蓝调元素的“花姑娘”的时候,崔健正坐在他位于北京的家里,手里端着一杯冰啤酒,面带微笑。
笑中带点醉,醉里带点苦。原来,中国还有人记着崔健。
被人遗忘是说到底也是件痛快淋漓的好事情,快刀子麻利地斩落,还没有疼,已经结束;疼的是钝刀割肉的折磨。
娱乐圈无非就是用几首歌娱乐别人,偶尔被别人娱乐一下。这永远是高富帅的天下,而崔健看上去永远像个朴实的农民,他的歌也似乎土得掉渣。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圈内的游戏规则,像一次轮奸,你不行了,后面立即有人补上来。崔健并不是不懂得珍惜,而是有些事,命中注定只能花开一季。久违的《花房姑娘》让这个不修边幅的中年男人一瞬间遁入回忆。
1986年5月9日晚,北京首都体育馆,“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孙国庆、毛阿敏、杭天琪、韦唯,当时名噪一时的内地歌坛领军人物尽数出场,在唱完了《让世界充满爱》三部曲之前,按演出计划有二十名层层筛选的无名歌手做为绿叶陪衬这些乐坛大腕上场献唱。这其中就有北京交响乐团的小号演奏员崔健。
当时崔健只是混迹于各大交响乐的演出现场做为乐器组的一员,从来没有单独登台的经验,他能争到这个演出的名次也完全是因为他的小号实在很棒,而且,他平时也会给一些音乐人创作歌曲,这次机会,他只不过借着天时地利想“玩一玩”而已,毕竟,年轻人喜欢尝鲜。
旁边已经有人把麦克风递到他手上了,不住地有人提醒,“最后三分……最后两分……”,崔健晃晃脖子,感觉身上的西服非常不舒服,勒得他呼吸不畅,同在一个乐队的贝斯手王迪指着自己裹在身上的棉袄开玩笑“要不你穿这个。”崔健在“最后一分钟”的提示中匆匆换上棉袄就冲到台上,“至少它不会勒住我的嗓子。”
台下观众的口哨声立即震天响起,历来所有的演唱会,有谁敢穿着一件破棉袄就冲出来?何况这个人的两条裤腿儿还一高一低……
“我曾经问个不休……”崔健略显沙哑的高音飙上去,台底下立即安静下来,很多人张大了嘴,完全傻了,整个中国,有谁这样唱过?
观众席上,那些刚刚从文革的严肃和打开国门刚刚接受了“喇叭裤蛤蟆镜”中国百姓在这耳目一新又切中思维要害的歌声中如醉如痴,口哨和欢呼直到下一位演员登台才渐渐平息。“再来一个”的呼喊也从没停过。
只是,不可能让这个另类小子再来一个,演出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和进程安排,而且,像纯文学一样正统的严肃音乐中突然冲出一个傻里傻气的年轻人,这让音乐的组织方极其不爽,现场观看演出的某官方代表推开阻止他的随从愤然离场,在门口,这位领导人找到了演唱会的总导演王昆厉声责问:你怎么搞的?节目审查了没有?这种牛鬼蛇神怎么都混上台了?”
晚会的高潮部分,近十七分钟的超长单曲《让世界充满爱》首唱开始,百名歌手齐齐站在台上,崔健做为伴唱站在合唱部的靠后位置。观众席上的欢呼又一次响起。“看,那个穿棉袄的换了西装--”而崔健听不到台下的喧闹,一本正经地隐藏在人群里,压低了嗓子跟着大部队唱:想起来是那么遥/仿佛都已是从前/那不曾扑灭的梦幻/依然隐藏在心间……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一夜之间知道了这个敢穿着棉袄上台唱歌的崔健。
虽然严肃音乐和政府部门对崔健当晚的表现极其不满,甚至要北京交响乐团开除他。但组委会显然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的洗礼下已经对“市场效益”这个词门径初通,演唱会结束后不到一周,主办方便推出了孙国庆、田震等10位歌手当晚的歌曲制作了《百名歌星荟萃精选》的盒带中,第一首便是“棉袄唱将”崔健的《一无所有》,中间插了一首胡月演唱的《祖先》,第三首还是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而盒带的封面上,去掉了众多的大腕级明星露脸的机会,印着身穿西装的崔健。
《一无所有》一战成名,中国的每家音像店和咖啡馆里都飘着这种听起来很压很憋甚至是很难听却又很刺激很亢奋很能戳到“痒点”的声音,你无法一直坐着听完,你就是想站起来,和着音乐一起摇一起摆一起嗨一起跺脚大喊过瘾。你说不出为什么,但它就是能拉扯住你的脚步。
那是种力量。
而崔健还是离开了北京交响乐园,当记者问及此事的时候,崔健微笑,“劝退。已经很给我面子了。”
人生里充满了各种离开,车站,码头,机场,甚至每一个遭遇红灯的街角,可以激情吻别,也可以抓过背包就转身离开,连一声再见都懒得说。崔健躲在北京东郊幸福村的家里,一边带着失业的焦虑琢磨着明早去哪个亲戚家混顿饭,一边连夜写出了《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
被抛弃,还要微笑,文革已经结束好久了,再没有文字狱,没有打杀和批斗,可这世界还爱我吗?
幸好观众们还爱。告别了国家工资之后,他加入了ADO乐队,在乐队的匈牙利籍贝司手巴拉什和马达加斯加籍吉他手艾迪的影响下,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崔健把西方摇滚元素和布鲁斯以及爵士乐的成份引入中国市场,配以他特有的磁铁般沧桑嗓音,在北京的各大音像店里偷偷灌制黑带,因为观众太热烈了。第二年,崔健发行了他的第一张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理所当然地收录了成名曲《一无所有》。
卖到黑碟泛滥啊。那是中国摇滚的第一次振兴,听惯了孙国庆的红歌,郑绪岚的“国粹”,甚至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也软得让人瞌睡,一本正经的中国音乐里突然兴起了崔健和他的中国式的音乐疯狂。
1989年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开始了国内巡演,卖到票断,却被中途取消,理由是与中国国情不符,引导青少年的靡靡之音。
从1986年的台湾第八届贡寮国际海洋音乐节上,摇滚教父 崔健戴着有着红星的白色棒球帽,背着吉他走上舞台,观众点名要他唱《混子》,当唱到那句“过得怎么样?”歌迷立即大声回答:“凑合”。
是啊,谁,不在凑合着?
崔健在舞台上狂歌劲舞,甚至间奏的空闲里还点了支烟,下雨,浇不灭的热情里,他把烟藏在衣袖里抽,顺着衣领往外冒烟,景象很诡异。
观众依然喜欢这不羁的风格和骨子里最透彻的力量,纯正的北京音里透着西北风的彪悍和最纯正的呐喊,不做作,不雕饰,甚至直白到让人跺脚。1991年崔健发行了第二本盒带《解决》,单曲《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被国内封杀,却拿到了世界级的音乐奖,并在世界华语乐坛风声突起,在日本拿下了六周的销售冠军。原来,领导着亚洲音乐走向的日本,也喜欢这样的摇滚。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行
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
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
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哇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撒野的感觉真好。观众的喜欢的音乐就是最好的音乐。不必给音乐背负太多沉重的东西,郭德纲说得对,“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杂技团,三十个人骑一辆自行车,它有什么教育意义?它违反交通规则了你知道吗?”音乐也一样,它只需要能勾起你把情绪从胸腔里扯出来一起跃动就够了。1994年崔健发行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并于早些时候拍摄了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光看名字就已经读懂了崔健音乐中的叛逆:
跟着音乐的感觉走吧,去他妈的一本正经。
本文选自《听首老歌,怀念我们一去不回的青春》,转载约稿请联系本人。
崔健:1961年生于北京,朝鲜族。1981年任小号演奏员,以一首《一无所有》开创了中国式摇滚先河,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代表作《最后一枪》、《新长征路上摇滚》、《给你一点颜色》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逐渐淡出歌坛。
2005低调复出,专辑依旧卖势火爆,实力证明,崔健仍是中国摇滚的最纯粹代表,至于复出的原因,崔健回应说“做为一个骨子里始终无法远离音乐的人来说,最完美的死亡方式是死在舞台上,而不是家里的床或沙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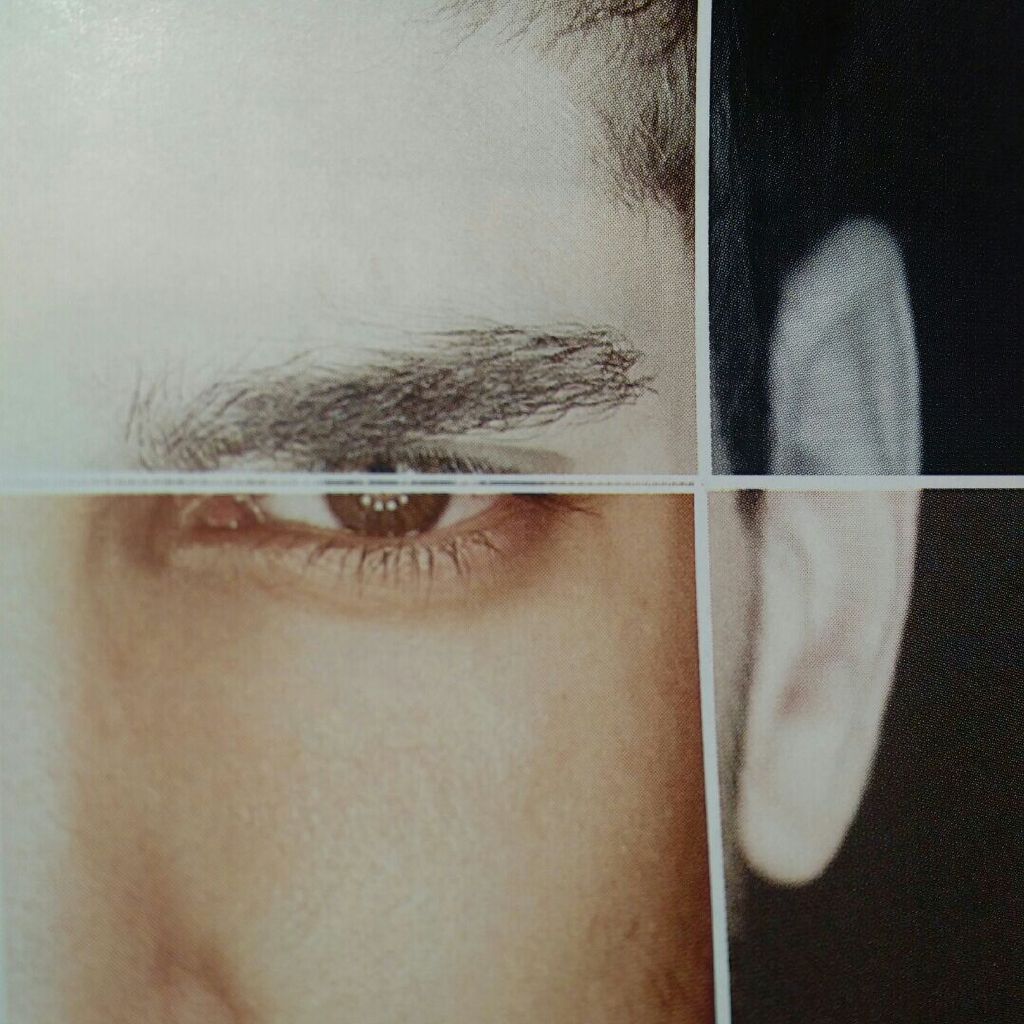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