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清初时期,随着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的相继设立,广袤的东北地区的行政管理逐步走向正轨。为保障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联系,清政府在重要城市之间修建了驿路,设置了驿站。除盛京——吉林——宁古塔驿路外,在增设黑龙江将军后,为防御北方沙俄的觊觎,以吉林城为枢纽,还增修了通往瑷珲城的驿路。这条驿路在蒙古卡伦站又分出通往三姓(依兰)的岔路。在驿路所构成交通网上,传递公文、押解人犯、运送贡物、补充给养,让这些官修的道路在随后的日子里,逐渐成为东北地区商旅经济活动的大动脉。

解放前的马匹运输队,取自《吉林旧影》
在清代,作为驿路上的重要节点,每隔50-70里,个别的38-125里(《吉林市发展史略》),设有驿站,以拨什库(领催)管理驿站的站丁、牛、马。驿站数量、规模因时代而各有不同,到了光绪年间,大致每站28人,每个站丁各管有1马1牛。和关内驿站称“驿”不同,东北的驿站全部按“传递军报”的规矩,从设立之初就称“站”,归东北三将军分别属领。其中吉林将军在光绪年间共辖有52个大小驿站(不包括边远地区承担驿站功能的“卡伦”,卡伦为满语,意为哨所)。

吉林城西路驿站
吉林将军下辖的驿站分东、西、北三路,北路又分瑷珲、三姓两个方向。这其中通向盛京的西路始终保持8个站设置,因这些驿站设置较早,故而驿站名称也多为满语。只不过西路所经地域属于吉林将军下辖开发较早的发达地区,为关内移民的重要落脚点,因而个别驿站后来也有了汉语别称。在道光九年版《吉林外纪》中,有这八个驿站的简要介绍:
西路自省城起,七十里曰蒐登站。蒐登站名称源自驿站靠近蒐登河,或因“蒐”字内含鬼字不吉,“蒐”现已改写作“搜”。《吉林市地名辞典》解释“搜登”为满语音转,意为岗梁。清代蒐登站所在地今为搜登站镇,为吉林市船营区下属乡镇。

伊勒门站近影,刘学风拍摄
七十里曰伊勒门站。伊勒门站名称源自临近的伊勒门河。伊勒门也写作”伊尔门“,满语意为“阎王”。这条河河道狭窄,旧时雨季经常泛滥。肆虐的洪水汹涌咆哮,将流域内化作一片泽国地域,故有”阎王河“之号。不过“阎王”的威风竟大致与清政府同寿,伊勒门河在解放前就被改写为饮马河,理由是好事者附会乾隆皇帝东巡时,曾在此河饮马。另外,1958年,饮马河上修建了石头口门水库,河流的凶嚣之气被大坝钳制,伊勒门更加有名无实,反倒不如”饮马“之名恬静。好在驿站所在地还保留伊勒门之名,现为永吉县金家乡下属村屯。
五十五里曰苏瓦延站。苏瓦延也写作苏斡延、苏瓦盐、苏完、刷烟,名称源于与之相邻的苏瓦延河。苏瓦延为满语“浊黄”之意,流域内是满族重要的发祥地。清末,汉语在东北普及程度超过满语,苏瓦延也就其汉语的译音改写为双阳、双杨、双羊,故而《清一统志·吉林二》 有“站即双杨站”的记载,《宁古塔纪略》有“双羊河站”的记载。
六十里曰伊巴丹站,即驿马站。伊巴丹为满语“欧梨木”之意。欧梨木是一种野果子树,果实紫红色,民间俗称臭李子。伊巴丹站因驿站周围生长了许多这种野果树而得名。伊巴丹站后来发展为城镇,为今天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
六十里曰阿勒滩额墨勒站,即大孤山站。阿勒滩额墨勒也被其他史料记作阿尔滩讷门、阿尔滩额林、阿勒坦额墨勒、阿勒坦额默勒。驿站名称源于附近的一座山岗——阿勒滩额墨勒山。据《盛京通志》记载:阿勒滩额墨勒为蒙古语,阿勒滩意为金,额墨勒意为鞍,即金马鞍之意。这个驿站后来发展为城镇,为今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孤山镇。另外,结合《吉林外纪》的插图,在伊巴丹站和阿勒滩额墨勒站之间的驿路上,还有一座城市,即伊通城。

解放前的畜力商队,取自《吉林旧影》
六十里曰黑尔苏站。黑尔苏又写作赫尔苏、克尔素,名称源于驿站濒临赫尔苏河(今东辽河)。“赫尔苏”为满语“盐碱地上的草”之意。史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筑柳条边,设“赫尔苏边门”,同年在盛京至吉林乌拉的驿路上设黑尔苏站。1943年,日伪当局修建二龙山水库,驿站沉入水底。 这个二龙山水库现在也叫二龙湖水库,近年爆火的“二龙湖浩哥”,就是以这个水库冠名。
八十里曰叶赫站。叶赫站也有“乜合”的写法,名称源于驿站设在明代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首叶赫部的都城附近。关于“叶赫”的含义,说法很多。有人说是满语“野鸭子”之意,有人说是满语“河边的太阳”之意,我更倾向于前一个解释。叶赫站位于今四平市梨树县叶赫满族镇附近。
四十里曰蒙古霍洛站。蒙古霍洛中的蒙古为民族名,霍洛是满语“沟”的意思。这个驿站是吉林将军辖区西路8个驿站的最西侧一个,虽然驿路大致保持东北西南走向,但从叶赫至蒙古霍洛,驿路明显有些偏向南侧,离开蒙古霍洛后,驿路才回到原来走向上。这个驿站位于今天西丰县明德满族乡附近的蒙古货郎村,把霍洛改为货郎,虽有些戏谑,但细想起来,在清末驿站废除后,驿路上的往来人,则以客商为主,不得不说这名称改得倒也符合时代脉络。
蒙古霍洛站再向西南,就是柳条边上的威远堡边门。威远堡边门是“盛京边墙”(即老边)十六边门之一。清代,北京—盛京—吉林驿路被俗称大御路,而威远堡边门是十六边门中扼守大御路的咽喉,是盛京将军和吉林将军分治界限。在清代,威远堡边门吉林一侧驿路途径之地古树参天、浓荫蔽日,为蛮荒之所。清初时,《柳边记略》作者杨宾赶赴宁古塔,过威远堡边门后,睹荒凉,触伤怀,曾作《出威远堡门》一诗,字里行间可见吉林将军管辖的西路驿路荒凉之一斑:
黄沙漠漠暗乾坤,威远城头欲断魂。
芦管一声催过客,柳条三尺认边门。
乱石雪积人烟绝,老树风口虎豹蹲。
从此征鞍随猎马,东行夜夜宿雪根。
然而自晚清开始,随着清政府封禁政策破产,大批关内移民涌入东北.关内文化与东北文化碰撞交流,产生出改天换地的新活力。期间,汉语逐步取代满语成为东北地区的通用语言,大量满语地名或 改头换面,或干脆退出历史,只有极少数顽强地留存于世,成为过往时光的特殊留念。一如搜登站、伊勒门等地名,承载的就是一条古驿路的历史兴衰。
特别鸣谢刘学风先生对我撰写此文给予的支持和鼓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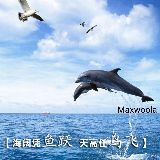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