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游客在土耳其旅游时,都会选择观看土耳其旋转舞(Samā‘)表演。洁白的长袍、令人晕眩的旋转、神秘的音乐和祷词,让各国观众都如痴如醉。现今,伴随着后工业时代文化的发展,土耳其旋转舞也逐步走向世界,为更多国家的更多人所知晓。
在土耳其的科尼亚(Konya),长眠着一位在伊斯兰世界无人不晓、东西方皆有名望的著名诗人—贾拉鲁丁·鲁米(Jalal ad-Din Rumi,1207-1273),常常被冠以“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称。鲁米是伊斯兰教苏菲主义(Sufism,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思想的统称,其追随者相较于其他穆斯林更加重视个人的精神功修)的大师,“土耳其旋转舞”本身是鲁米所开创的苏菲教团“莫拉维教团”(Mawlawiyya / Mevlevi Order)的精神修持仪式,于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除了旋转舞广为世人所知以外,鲁米的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脍炙人口:一本收录了他代表作的英译诗集在美国销量达到50万册。他的诗歌被重新谱曲并演唱,进入音乐排行榜。有人把他的诗作在美国的复活与纪伯伦的重新被发现相提并论。2007年适逢鲁米诞辰八百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2007年为鲁米年。同时代的诗人千千万,缘何只有鲁米的遗产能像这样被世人所知、所爱?有一个重要的答案是:鲁米是一个具有“包容性、普世性”的苏菲主义诗人。

● 土耳其旋转舞表演者们(来源:维基百科)

鲁米生平介绍

鲁米于1207年出生在花剌子模王朝的巴尔赫的一个波斯人家庭(今阿富汗的巴尔赫省,一说鲁米生于今塔吉克斯坦的瓦赫什)。“鲁米”一名不是他生来就有的,而是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位于安纳托利亚的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主要位于现今土耳其境内。阿拉伯语中称呼安纳托利亚等旧时拜占庭帝国的土地为“罗马”,音译为“罗姆”或“鲁姆”)。而由于鲁米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地位,又被冠以“莫拉维、莫拉那”(Mawlawi, Mawlana,阿拉伯语,意为“我的导师”和“我们的导师”)的称号。
鲁米一家于1217-1219年间为躲避蒙古人入侵而迁往罗姆苏丹国。鲁米的父亲巴哈乌丁·瓦拉德(Baha ud-Din Walad)是一名苏菲教士,鲁米24岁时,巴哈乌丁去世,鲁米继承父业,也成为了苏菲教士。据说,鲁米曾经拜会过著名苏菲主义诗人阿塔尔(Farid ud-Din Attar)和著名苏菲主义理论家、神学家伊本·阿拉比(Ibn Arabi)等苏菲主义先哲和大师,也曾是苏菲哲人布尔汉努丁·莫哈齐克(Burhan ud-Din Mohaqqiq)的弟子。
鲁米将近40岁时,与苏菲苦行僧大不里士的舍姆斯(Shams-e Tabrizi)相遇,这成为了鲁米人生的转折点。鲁米和舍姆斯成为了挚友,并在这个时期,鲁米从一个普通的苏菲教士变成了一名具有灵性和诗性的苏菲主义伟人。舍姆斯于1248年突然消失,此后鲁米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伟大著作《舍姆斯集》(Divan-e Shams-e Tabrizi),正式成为了一名诗人。
舍姆斯失踪后,鲁米又遇到了人生中另外两个挚友:金匠萨拉丁·扎库布(Salah ud-Din Zarkub)和苏菲霍萨姆丁·恰拉比(Hussam ud-Din Chalabi),并在这一时期写下了被称为“波斯语的《古兰经》”的煌煌巨著《玛斯纳维》(Masnavi或Mathnavi)。
鲁米于1273年在科尼亚(今土耳其科尼亚)去世。送葬那天,科尼亚全城居民都对其表示哀悼,很多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也参加了他的葬礼,共同见证了一位伟人的逝去。
鲁米一生用波斯语写作,与菲尔多西(Ferdowsi)、哈菲兹(Hafiz)和萨迪(Sa’di)并称为“波斯诗坛四柱”。他一生走遍了很多土地,被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国同时认为是本国的“文化名人”。2007年,为了纪念鲁米诞辰8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发行鲁米纪念章。

● 位于土耳其科尼亚的鲁米陵(图源网络)

鲁米思想的包容、普世思想
“不分血统、典籍或传统,
我们同畅饮着生命之水。“
鲁米的身份虽然是一名苏菲主义诗人,但他从不将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和信仰随意划界。相反,在他充满灵性的诗篇中,处处可见他心怀整个人类的悲悯。在他的诗歌中,不仅有伊斯兰教的传统意象,也充满了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喜欢的意象和阿拉伯、波斯、希腊、印度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鲁米思想的包容和普世性从苏菲传统中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很多苏菲主义者认为,世间的宗派只是人类的表象,而表象之后的真相则是“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都是真主的造物”。人类皆同源,人类本一家,而“爱”——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友爱,还是宗教范畴中对“造物主”的爱——而非“恨”,才是解决人类问题、通向智慧和真理的途径。正如鲁米在《玛斯纳维》中写道:
坠入爱河无论何缘由,
终将把我们引向完善。
16世纪的苏菲哲人巴哈乌丁·阿米里(Baha al-Din al Amili)的诗句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天方和佛塔都分别只是途径而已。
“爱”是鲁米的精神之阶梯,是数不清的问题的答案。鲁米认为,“爱之星盘显真主秘密”,是宇宙中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原动力。
作为莫哈齐克的弟子和舍姆斯的挚友,鲁米懂得了书本上的知识不能开启“内里的眼睛”,即内生的智慧。因此,音乐和舞蹈成为了鲁米及其教团不可分割的艺术元素。伊斯兰教本身对音乐舞蹈等艺术表达有一定限制,但鲁米又一次透过表面认知,发现了音乐舞蹈对于人类的心灵有着共通的作用。如果说人类会因为民族、种族的不同对一种语言、文字不一定能产生共情,那音乐和舞蹈则是人类生而能产生情感共鸣、最大限度跨越地域和民族的艺术。还有什么快乐比随着音乐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更淋漓的快乐呢?鲁米在诗中用音乐、舞蹈作为意象的频率也是前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诗中,这样的句子时常出现:
芦笛中燃烧着爱的火焰,
酒中盛满了爱的激情。
爱,需要得到印证:
如果镜子不反射,那它是什么?
一些所谓的宗教学者以严格、刻板著称,但鲁米从不是这一类人。穆斯林每日需要面对麦加的天房(Ka‘aba)祷告五次。但鲁米在《玛斯纳维》中说过,每个人的“天房“并不一样:
哲布勒伊来和众灵魂的克尔白是酸枣树
饱食终日者的朝拜方向是桌布
精神之人的朝拜方向是忍耐和冥想
外表崇拜者的朝拜方向是石上之像
(编译者注:哲布勒伊来(Jibril),又译吉卜利勒,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大天使,即《圣经》中的加百利(Gabriel)。酸枣树,指“天堂之树”)
在这里,鲁米虽然将不同的人做了一番比较,但至少他承认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和信仰,这一点,便胜出那些耽于说教、死板保守的“饱学之士”们无数倍。
鲁米相信,在任何的宗教、任何的信仰中都包含了一种普世的信仰在其中。鲁米的思想是开放的,他的文字里很容易看到其他文化的影子。在鲁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哲学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希腊式的观念对他的影响。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的形象——在晌午举烛寻找“真正的人类”的那个人——出现在了《舍姆斯集》和《玛斯纳维》当中。鲁米将所有存在物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矿物、植物、动物、人类、天使以及更高级的存在——正是新柏拉图主义中“所有灵魂终将回归它的神圣本源”的体现。

● 描绘鲁米的波斯细密画(来源:维基百科)
在鲁米的语境下,“信仰”并不是指的信某一个特定的宗教或者主张。任何宗教的祈祷和其他仪式只是信仰的外在表现。真正的“信仰”则是指的一种内心状态,而这对于任何宗教或主张都是相通的。《玛斯纳维》中有这样一句诗:
每个先知圣徒各有方式
然而全通向真主皆是一
另有一句:
因为被赞颂者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不同的宗教也是统一的
一个真正包容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是虚怀若谷的。美国著名鲁米研究者、诗人科尔曼·拜科斯(Coleman Barks)在他汇编的鲁米诗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鲁米对十三世纪时候伊斯兰教小村镇里那些备受冷落的成员表现出深深的关怀。他常常会在路上停下脚步,向老妇人和小孩子鞠躬,祝福他们和接受他们祝福。有一天,一个亚美尼亚屠夫——一个基督徒——打鲁米面前经过,鲁米立刻站住,向对方连鞠了七个躬。又有一天,鲁米走到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中间,告诉他们,他们将来都会像他一样,长大成人;这时候,一个小孩从田的另一边向他飞奔过来,一面跑一面喊:“等等我,等等我!”鲁米静静等着,等小孩走近以后,他向小孩鞠躬为礼,小孩也向他鞠躬为礼。

小结:用第三只眼看世界
中国台湾翻译家、将鲁米译介给中文读者的重要人物梁永安把鲁米称为“用第三只眼看世界”的人。这“第三只眼”正是心灵的眼睛、灵魂的眼睛,鲁米以心观人、以心观世界,得以脱离倨傲的冷漠,“目击而道存”——真正与全人类的悲欢相通,为波斯诗歌注入了一股股人文主义的气息。鲁米的故乡、现今的阿富汗,写毕此文时这个命运多舛的山国在干戈寥落、各派相争四十多年后正在经历又一次剧变,这位从阿富汗一路向西游历的大诗人看到这一切,必定会痛彻心扉:许多因为所谓“不同”而引起的争端、冲突甚至暴行皆是无比幼稚的行为而已,如同一群儿童因为几颗糖果而互相大打出手一般。
来源:Rumi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his Message,MUHAMMAD ESTE’LAMI,载于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杂志;The Essential Rumi, COLEMAN BARKS
文中鲁米诗歌中文翻译均来源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玛斯纳维全集》,穆红燕等人译,及甘肃人民出版社《在春天走进果园》,(美国)科尔曼·拜科斯编著,梁永安译
编译:唐飞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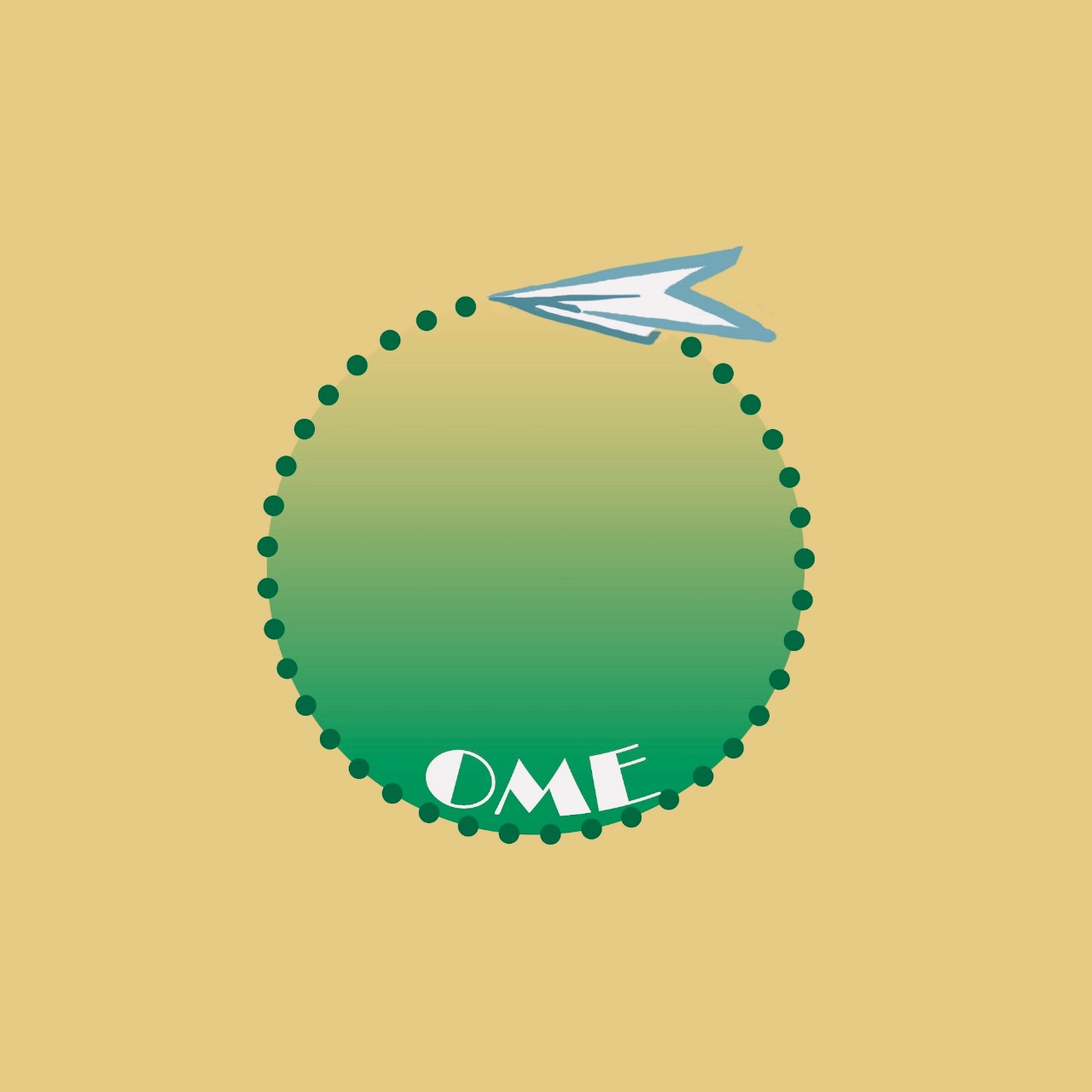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