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很多事情是不请自来的,你没法提前想好怎么对付,只有当它发生了,你才明白,在未来的日子里,你的人生将不再按照你的预期前行。
比如,我就完全没想到,我聪明要强的老妈,居然会得认知症*,我退休后不得不将很多时间精力放到她身上,甚至要变成她的“妈妈”。
就像老妈不愿意接受自己病了一样,我也不愿意接受老妈患了认知症这个事实,不愿意接受我不得不放弃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承担起为妈妈当妈妈这个新的人生角色。


很困,一夜未眠,惦记着在旧金山拖着行李转机的女儿,担心她略微超重的行李是否会被“严格”的美国人卡住,担心两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她是否来得及把行李从国际航班取出再办理好国内航班的托运……睁眼到快凌晨三点,距离下一个航班起飞大约只剩下20多分钟时,终于收到了她的短信:“已到登机口,安心。”
是的,我该安心了,可以安心地去睡了,但偏偏睡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从床上起来,把女儿的被套扔到洗衣机里,重新上床,辗转反侧了好久总算迷糊着了。
六点半醒来,起身。七点过,收到女儿短信,已经到纽约纽瓦克机场,和她的表哥胜利会师了。
早饭后,我和先生这对刚刚空巢的父母,立刻像调频收音机一样,从为人父母转换到身为人子的频道,奔赴自己父母家中。
我们先去了女儿爷爷家。为了让我们多一点儿和女儿相处的时间,先生的妹妹在此“值班”已经半月有余,先生要去替换她了。
之后留下先生照顾他的父亲,我一个人顶着太阳往妈妈家赶。阿姨的女儿今天走,我希望多给她们母女一点儿相处的时间。我刚刚送走自己的女儿,虽说不是撕心裂肺,也是难舍难分,咱们将心比心吧。
到家,拉着妈妈的手坐在沙发上,“聊天”,也就是听她用AD语唠叨。听,就全心全意地听,偶尔我会插进一些提问,让她感觉到我关注着她,对她说的有兴趣。就这么聊了40多分钟,相当于一节课的时间。如果有别人在场,一定觉得我们母女两个聊得很起劲,殊不知,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啊!
午饭后,阿姨和女儿出去买东西了,我陪着老妈。老妈通常是不睡午觉的,但是今天我觉得我需要睡午觉,且一部分的心还在女儿的身上,要继续听老妈讲AD语,有点心理疲劳,听不进去了。
但是,如果我自顾自睡去,没人去关注老妈,她肯定就会不高兴,就会发脾气,我也睡不成。怎么办?
既然她最需要的就是感到有人关注她,那我就想个办法,能让她在关注中安静下来吧!
于是哄她上床,在床头垫好靠垫,让她半坐半躺,发给她半份《新京报》,然后我在另一头放好枕头躺下,拿起另外半份报纸,我告诉她:“现在是看报时间(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看报是她多年的习惯),咱们看看今天都有什么新闻发生。”
当然这是哄不住她的,因为她已经退化到虽然还能“认得几个字”(借台湾作家张大春的书名),但无法理解这些字词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理解句子的含义,因此也不可能读懂报上的文章了。
在这张她平时睡的单人床上,我选择和她对头躺着,不光是因为床的尺寸小,我还“别有用心”:这样我可以触摸到她的腿,可以轻轻地抚摸和拍打她,好让她感到安心,不会“闹”。
我就这么轻轻地摸着妈妈消瘦的脚踝,每当她发出一些声音表示烦躁时,我就会改为有节奏地拍打,就像女儿小时候哄她入睡时一样,只不过那时候是把女儿抱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妈妈真的就安静下来,不再出声。我悄悄抬头去看,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我也放下报纸,希望能睡十分钟八分钟,但是,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这些天来睡眠一直不好,也许这是与女儿分离的身心反应吧!
几天前,特地带即将出国留学的女儿回爷爷家和外婆家告别。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一别也许还能相见,也许就见不到了!女儿和外婆告别时,突然伸出右手,轻轻地抚摸外婆的脸颊,瞬间眼泪哗哗流下。外婆似乎有些明白又有些不明白,她喃喃地说:“都是这样,我也是一个人在外面……”
看到女儿抚摸外婆的这个温柔的动作,我也流下泪来。但除了离情与伤别,我心里还有更复杂的感受。
我不曾记得妈妈对我有过这样亲密的爱抚。拥抱?亲吻?摸摸我的脑袋?搂搂我的肩膀?拍拍我的背?好像都不曾有过,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没有。
当然,她肯定是抱过我的,有小时候的照片为证。那是在重庆,我不到一岁的时候,而且照片上的妈妈是笑的。
一岁零九个月的时候,爸爸妈妈调北京进外交学院学习,准备将来出国工作。我被送到了外婆家。快五岁的时候,父母将我接回北京,送进幼儿园。还没等我和他们“混熟”,他们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背负着重任,去到那些对他们而言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工作了。于是,我成了真正“全托”的孩子:不仅晚上住在幼儿园里,而且周末和节假日其他小朋友回家的日子,我也都待在幼儿园里。
等到我10岁时妈妈回国生妹妹,她已经变成一个陌生人:她穿着从国外买回的无袖连衣裙,烫着一头卷发,和当时国内提倡的“艰苦朴素”作风差得十万八千里,我甚至羞于和她走在一起。
接下来是“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五七干校”,一家人在社会的动荡中惶惶不安,离多聚少。插队时妈妈写给我的信,基本上都是嘱咐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像《人民日报》社论一样,不带私人感情。
我长大了,自然不再像小孩一样渴望妈妈温情的拥抱和触摸,但内心深处,我猜这份渴望就像长明火一样不曾熄灭。哪个孩子不渴望得到妈妈的爱呢?而温柔的触抚,正是这爱最自然最真挚的表达。
后来,妈妈得了认知症,开始渐渐失去日常的生活能力。当我们发现她在冬天用热水擦澡而不是用淋浴时,我意识到她已经不会用燃气炉了。于是,我和妹妹开始帮她洗澡。
帮妈妈洗澡,让我开始触摸到她的身体。我不知道,命运这样安排,是否是借着病魔来打破母女间僵硬的界限?
开始的时候,我似乎只是在完成洗澡这件“事”,妈妈的身体对于我来说,可能并不比一件东西更加宝贵。我们彼此都很陌生,在没有必要时,我不会轻易地触碰她。很长时间,我仅仅是给妈妈擦洗后背,别的地方都是她自己洗。
慢慢地,好像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产生了。
开始给妈妈擦背时,我会感叹,快80岁的人了,皮肤还这么光滑,这么有弹性。
渐渐地,这个饱满丰润的女人的后背,一天天失去了光泽,失去了水分,皮肤下的肌肉在不知不觉间萎缩了下去,皮肤上开始有了一条条的褶皱……
触摸着妈妈干枯消瘦下去的身体,那种一点点滋生出来的感觉,或许应该叫作“怜惜”吧。
就像乐谱中标注了渐强符号似的,这怜惜每每在我给她涂抹润肤露时开始变得强烈。我的手触抚着妈妈的身体,一点点把润肤露涂匀,再轻轻地揉进她的皮肤里。我好像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减少皮肤的干燥而给她涂润肤露,也在把我的怜惜之情一点点地揉进这个躯体中——对于我来说,它已经不再那么陌生,不再是一个“打理”的对象,而是一种可以激起并投入一些情感的存在。
妈妈能感觉到我的怜惜吗?她喜欢这样的触抚吗?
她从来没有说过,没有表达过喜欢,也没有表达其他的情感。只是,很长时间,她都拒绝阿姨给她洗澡,似乎给她洗澡是我和妹妹的专利。而大多数我们给她洗澡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很乖”。
在妈妈渐渐衰老,还没有患上认知症的时候(或者已经患了但我们还没有察觉),我就常常想在过马路、上台阶的时候拉她一把,但通常她都会甩开我的手,好像那是对她的不信任。她从未主动地挽过我的手,更别提“勾肩搭背”这种亲密的行为。而我和我的女儿却一直很亲密,她二十几岁了,出门时仍然会和我手拉着手。
手拉手,一个无比简单的动作,里面包含着相互信任、共同分担、彼此支持,传递着亲密、温暖和爱,是给予也是得到,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感表达啊!
我知道不能怪妈妈,她一定是小时候缺乏这样的经历,才把情感压到内心最深处看不见的地方。
不管怎样,就让我拉起她的手来吧,在她变得步履蹒跚之时,在她忘记来路、忘记归程茫然一片之时,让我拉着她干如枯枝的手,慢慢地走,慢慢地走,走回她的童年记忆,走向不可知的未来;让我手中的温热,慢慢地捂,慢慢地捂,捂热这颗缺少情感滋养的心吧……
学习心理辅导时,我的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告诉我们一句话:Counseling is touch life,她把它译为“心理辅导就是触抚生命”。我很喜欢“touch”这个单词,它可以译为“碰”“触碰”“接触”“触到”“打动”。有了“touch”这个动作,原本没有关系的双方,就建立起了联结。当然,这样的touch应该是无比温柔的。
中国人喜欢说“血浓于水”。但所谓的亲情就是血浓于水吗?我一直不怎么相信。我想,如果没有日复一日共同的生活,如果没有在生命某个阶段的相互扶持(爸妈对孩子的照料,孩子对爸妈的照料),如果没有身体上的亲近,没有带着怜惜和爱意的触抚,没有touch,即便是亲人,也难以建立起深情。如果说,Counseling is touch life,那么,在亲人之间,touch本身也具有一种安抚和疗愈的作用吧?
也许,妈妈的衰老,妈妈的认知症,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通过对她身体的照料——这最自然而然的touch,去彼此联结,让温暖在心中慢慢地升起,就像初升太阳的光芒一点点地漫过无边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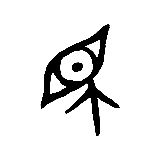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