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
讲用刀有冲、切两类,的确是只讲了个大概。吴昌硕是在篆刻领域里无论是意趣、配篆、章法还是用刀诸方面都是不可不谈的大家,他的用刀,绝对是不能以冲刀、切刀去规范的。吴氏早岁对浙、皖两派都有深邃的研究。他熟谙钱松用刀的奥秘,也领悟到吴熙载用刀的妙谛,有两强相辅,为今后用刀的出神入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作为智者的吴昌硕是绝不步武前贤的。在用刀方面,他除了从印内吸取钱、吴的精妙处,更从敦实、古朴、天成的封泥、瓦甓中去捕捉、提炼、升华出无古无今、纯属自我的用刀。他早岁所刻“道在瓦甓”一印,可以视作其用刀变法的宣言。封泥、砖瓦文字那天人合一,似直而曲、似实而虚、似凹而凸、似方而圆、似接而离、似碎而完的线条,给了他无尽的灵感与启迪,使他在三十几岁时即创立了非冲非切古贤所无的独特的残损用刀技法。以拙之见,他在中岁所刻佳印,一般都先以冲刀深刻(入石之深为他家所少见),镂出线条。传统的冲刀至此已是运刀过程的终结,而对于吴氏来说,这才是其用刀的序幕。换言之,这仅是为镌刻这根他所追求的线条“打底”。之后,吴氏在这线条的表层部分,再以会心、感悟到的瓦甓文字线条,作或披或刮、或铲或推、或击或擦的细微、繁复、严谨而颇具特效的处理,宛如身怀绝技的石人在顶天立地的石柱上雕龙刻凤。这是一种大胆而全新的用刀技法,是用刀史上概无前例的创造。传统理论上所谓的“补刀”,指的是刻刀不能准确完成使命而通过补刀来使其完备。而吴氏“补刀”的神奇处理,其作用不是补前刀的不足,而是使本已完备的线条得到一种质的升华。如果说,在吴昌硕之前的印人,刻刀所产生的线条是一重空间,而吴氏独创的残损用刀技法,营造的是二重空间,使钤盖在纸帛上的印蜕,不由地在平面上产生出似屈铁、似古藤、似坠石、似屋漏痕般的雄浑、苍古、气旺神满的浮雕般的艺术感染力。加之他使用质地厚实的潜泉印泥,更能使钤于纸帛的印蜕,有一种立起来、耸出来、活过来的神采。前贤所创造的精妙用刀技法,令我们可触可摸地玩味到刀法之美。刀法的功能是不容忽视的,它在流派印章里始终凸现出永恒的魅力。不过,再经典的个案,也会缺乏共性及适用的普遍性,刀法可以揭秘,可以借鉴,但我们最终还是要在了解古人、了解今人、了解自我的长期的践行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注重主客观的有机结合,注重篆法、章法的磨合,边创作,边感悟,边探求,逐渐地形成自己行之有效的用刀套路。一些印人以为吴氏的印作是随心所欲、一蹴而就的,这是十足的误解。笔者曾请教过王个簃先生,个老告我,缶老刻印极神速,然而,修饰的过程很漫长。一印甫成,置之案头,时而上手,静神凝视,操刀修荫,时作时辍,一日多次。一印告成,往往要十日半月,足见其神思之专,用心之深。
用刀一如绘画的用笔,有工笔与写意之分(姑且借用国画的名词)。如汪关(图十五)、林皋(图十六)、王石经(图十七)、陈巨来(图十八)的印作,当属于慢工细活的工笔。苏宣(图十九)、高凤翰(图二十)、曾衍东(图二十一)、吴昌硕(图二十二)、钱瘦铁(图二十三)、来楚生(图二十四)当属于解衣盘礴的写意。对于用刀的工、写,无高下之分,而各自有好孬之别。见仁见智,好山乐水,是因审美观决定的,诚然,也有兼容并蓄的刻家和赏者。
一般来说,工者心苦,若陈巨来刻印,用刀似顾绣,自是耗时费神,容不得一丝尘埃。而钱瘦铁刻印,鼓刀入石,立马可待,豪气激情,漫溢于朱白之间。钱氏的冲刀以勒为主。刀刃逼杀于字口,宛若狮子搏象。这种运刀技法,使刀刃上的强力,自然地转化为线条的张力。他的用刀技法,大别于乃师缶庐的“既雕既凿,复归于朴”,但却意外地获得了“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佳趣。
在工、写的两大阵容里,工笔者要力戒呆板,力戒刻意求工;修葺过头,付出的代价是自在;写意者要力戒浮躁,力戒刻意求放,不衫不履,付出的代价是精严。所以笔者认为,自在的工笔与精严的写意方式称得上是高妙的工笔与出色的写意。从理论上提出标准容易,而实际上极难兑现,故而回顾四百年流派印史,达标者可谓是了了。
在用刀的工、写之间,还存在着兼工带写的一类,而且这是印坛十之七八的大宗。若程邃(图二十五)、邓石如(图二十六)、徐三庚(图二十七)、赵之谦(图二十八)等,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的用刀,聚结着自在的理想与精气神,同样地令人赞佩。若程邃的圆融,邓石如的凝重,徐三庚的鲜活,赵之谦的恣纵,都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典范。
在近当代印人中,笔者认为要提及一位用刀高人方介堪。方氏是名列20世纪十大印人中的一位。其印风转益多师,雅妍有致,化古为今,风标独出。他的用刀是属于冲刀的范畴,但表现为推刀的运作,即以几次延续的短冲刀完成一根线条。冲刀是凭借腕力自一根线条的起始处一次直冲到末端,这不仅要腕力过人,且长刀直入,不偏不倚,精准到位。要完美地做到这一点很难,考察古来印人,唯黄牧甫一人而已。推刀则至少降低了对腕力的要求。然而,运刀化整为零,使用刀更易达到稳、准、狠的标准。方氏中岁在上海鬻篆,求者甚众,其在磨平的印面上并不篆字,而是以无名指蘸墨少许将其涂黑,即以刀为笔,刻出印文,一如在纸楮上信手写字,下刀肯定,极少补刀,轻松而精准。刻出的印,或巨印,或凿印,或小玺,或元朱,无论朱白皆有致有韵,绝无仓率粗陋之弊,尤其是刻缭绕细密的鸟虫印,刀走石间,如神龙穿云,使转裕如,观者不禁叹为神技(图二十九)。方氏大致一天能刻印五十钮,既快且精,刀法听命于手,文字喷吐于胸,足见其功力的了得。
刀法是一处必须研究的课题,是一门值得把握的学问。谁漠视它,它也就会同等地怠慢谁。篆刻艺术,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一个“刻”字。佳妙的篆法、章法与想法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有了好的篆法、章法、想法,也弥补、替代不了用刀的缺失。可以断言,没有精妙绝伦且自具特色的用刀,就不可能创作出上好的篆刻作品。诚然,用刀又不是孤立自闭的,它也只是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它只有与篆刻艺术的诸要素共融,才能显示出其不寻常、回味无穷的活力与魅力。换言之,仅有用刀的高妙,篆法、章法不对,观念陈旧平庸,同样创作不了上好的篆刻作品。历史上并不缺乏这方面的先例。我想,在九泉之下失意了一个世纪的用刀好手赵仲穆(图三十),在这一点上会有太多太多的懊伤。
(完)
2004年6月4日于德国之爱莎芬堡
(本文摘自韩天衡《中国印学精读与析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
本文感谢韩天衡美术馆公号支持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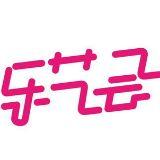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