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登的苦林一直支持着公众号,非常感谢他-----raingun
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与一战结束后的德国
一个多世纪前,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王路易十四时期修建的宏伟的凡尔赛宫召开,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彻底结束。实际上,当时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许多地方都召开了会议,结果是诞生了至少五个和约,分别以巴黎的各个郊区命名——每个和约都针对一个战败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本文的主角——1919年6月28日在镜厅与德国签署的《凡尔赛和约》。根据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的记载,两位战战发抖的德国代表走到凡尔赛宫的镜厅前,在和约上签了字。“沉默是可怕的”,尼科尔森这样写道。“德国代表脸色苍白……他们故意避开了那两千多只眼睛盯着他们的目光。”
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充满了快意的复仇,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甚至泪流满面地宣称这是“美好的一天”。签约时间和地点都是法国人精心考虑的:开始日期是1月18日,这是法国的国耻日,因为1871年的这一天德皇威廉一世在镜厅中加冕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一战胜利后,对此刻骨铭心的法国人终于得以一雪前耻。

上图: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镜厅加冕图。
然而,《凡尔赛和约》墨迹未干,各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它真的是一款和平条约吗?还是说它为二战埋下了种子?
最有力的质疑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他当时任英国驻巴黎代表团成员,但对会议结果很失望。他在1919年12月参加了一场名为“和平的经济后果”的辩论,并在辩论中谴责《凡尔赛和约》是“迦太基式的和平”(这一术语来源于罗马对迦太基的彻底摧毁和征服),称这是“将德国整整一代人变成奴隶的政策”,会导致“整个欧洲文明生活的消亡”。1961年,英国历史学家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也在其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断言“凡尔赛的和平从一开始就缺乏道德上的有效性”,并声称“一战为二战埋下了种子,事实上是导致了二战”。同样,美国著名外交官兼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在1984年也表示,二战是由于“对德国施加的非常愚蠢和羞辱性的惩罚”而导致的。
实际上,无论参加和会的那群“和平缔造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播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有一点需要明确,即德国的命运远不是协约国议程上的唯一问题。一战让整个欧洲的政治版图被硝烟和革命所撕裂,四个伟大的帝国王朝——沙俄罗曼诺夫王朝、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烟消云散。几个世纪以来,这几大帝国一直统治着欧洲大陆的中心和东部。在战后的一片破碎中,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他们的武装力量已经在缔造新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或恢复像波兰这样的旧国家。因此,巴黎和会的一大议题就是清理混乱的政治局面。
战时协约国的三大强权此时也各怀鬼胎:克莱蒙梭和法国人专注于削弱德国,因为当时德国人口比法国多一半,且其经济在1913年是欧洲最发达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虽然急于从德国获得赔偿,但也认为德国经济对欧洲的复苏至关重要,他担心过度的惩罚会助长德国人复仇的欲望,并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缺乏对欧洲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他一心想要建立“国联”,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上图:签署《凡尔赛和约》时的“三巨头”,从左至右分别是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照片摄于1919年6月。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出炉的和约实质上是这三巨头之间妥协的产物:法国人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在被普鲁士击败后于1871年割让),但未能永久吞并莱茵兰地区,相反,如果法国进犯莱茵兰非军事区,英美两国承诺将联合保证德国的安全;威尔逊实现了成立国际联盟的愿望,但国联在背负了无限义务的同时,却根本无力去维护和平。
在被德国、沙俄和奥匈帝国瓜分了一个多世纪后,波兰重新复国,但这遭到了柏林方面的极力反对,尤其是“波兰走廊”隔开了西边的德国本土和东普鲁士。英国警告说,要当心此举引发德国的复仇主义,但面对法、美两国对波兰要求的强烈支持,最终只能选择将横亘在“波兰走廊”上的但泽市(今波兰的格但斯克,当时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变成一个“自由市”(而不是波兰的一部分)来缓解这种情况。
妥协不仅是几大巨头间争议的结果,也反映出协约国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无论法国人的意愿多么强烈,他们在1919年都无法对1871年的战败进行充分的报复,因为1919年时的德国没有被入侵、征服和占领。对数千万德国人来说,停战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把失败归咎于和平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特别是犹太人的“背叛”。在某些极右翼分子(比如阿道夫·希特勒)看来,1918年德国根本没有战败,这就是为什么斐迪南·福煦元帅私下里说,《凡尔赛和约》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的休战。一语成谶,二战果真在二十年后的1939年爆发。
因此,1919年协约国施加给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凸显了协约国胜利的不彻底性。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在1918年打垮德国人的战争意志至关重要,但由于未能在参议院获得必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故美国政府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由于威尔逊将美国对法国的安全保证与《凡尔赛和约》挂钩,这样一来,不签字就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法国的安全承诺。英国人也不愿意给法国人背书,这就让法国愈加暴露在德国复仇的危险之中,反过来法国也就更加强烈地要求削弱德国。
这就回到了凯恩斯所说的“迦太基式的和平”。不过,巨额赔偿虽然让德国人怒火中烧,但还不至于压垮德国经济。事实上,巴黎和会并未确定具体的赔偿金额,《凡尔赛和约》只是在第231条中确立了“德国及其盟国应对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失负责”的原则,但同时也在第232条中承认德国的资源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赔偿”。在和约中,有不少类似的为战败国“开脱”的条款,但只有德国人(出于宣传原因)将赔偿问题视为协约国对其“战争罪行”——这是和约中几乎未出现过的字眼——的清算。

上图:巴黎和会召开时的场景。
1921年,协约国委员会为德国制定了1320亿金马克(当时约合330亿美元,加上利息)的赔款计划。然而,这个高得令人咋舌的数字主要是用于满足英法两国强硬派的虚荣心。在实际操作中,协约国只要求德国在36年内赔偿大约500亿金马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赔款其实是法德这对世仇新一轮针锋相对的开始。当法国政治家在1919年考虑赔偿问题时,他们想到了1871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即俾斯麦击败拿破仑三世后强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俾斯麦则想到了拿破仑在1807年强迫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中对普鲁士的不平等待遇。1921年的赔款计划最多每年拿走德国国民收入的8%,这低于法国在1871年战败后每年担负的比例(国民收入的9%至16%)。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单从经济上来看,赔款并不是无法忍受的。
真正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即德国人根本不接受失败。很多德国人认为,协约国索取赔款是一种政治手段,以弥补1918年未能在战场上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遗憾。总之,正如一位德国官员所说的那样,围绕赔偿问题展开的斗争是“通过其他手段对战争的继续”。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历届魏玛政府都竭尽全力地在支付赔款问题上耍把戏。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经济部门买入了大量外币,以便让德国马克贬值,使德国出口产品更具竞争力,而这种出口繁荣将“破坏与英美两国的贸易,因此债主会亲自找上门来要求修改1921年的赔款细则”。德国总理约瑟夫·维尔特也在1922年辩称:“我们整个政策的目标必须是让英国人不再紧咬着赔款不放。”他警告说,不要试图通过加税等措施来平衡预算,因为这会让协约国觉得德国还有油水可榨,并会要求将平衡预算的税收作为赔偿金。
既然不保持预算平衡,那么要取消赤字就得加印钞票,进而导致通货膨胀。但大实业家胡戈·斯廷内斯在1922年表示“要么选择通胀,要么选择革命”,这也得到了大部分德国大亨的赞同。然而,通货膨胀引发了另一场危机:从1922年秋季开始,价格上涨在德国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其程度令欧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相形见绌。
无奈之下,德国只得拖欠赔偿金,在这种情况下,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派军队强行进入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区,并以武力劫掠实物作为赔偿。愤怒不已的德国人自发开展了一系列抗议活动,这些地方性的抗议逐渐升级成了一场由德国政府支持的抵抗运动,并在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曾任魏玛共和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的领导下蔓延到了全国。
当这场抵抗运动接近尾声时,德国马克已经贬得不成样子了,鲁尔区甚至一度处于饥荒边缘。在战前的1914年1月,1美元能兑换4.2马克,短短10年后,名义上的汇率就涨到了4.2万亿马克(增加了12个零)兑1美元。在1923年,德国人每天用篮子或手推车领工资,然后立刻就要去支付账单或买东西,因为纸币每小时都在贬值。最终让德国摆脱这场困境的是伦敦和纽约银行家(尤其是美国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道斯)的金融干预。1924年,在英美银行的资金支持下,德国发行了新货币(帝国马克),取代了此前早已毫无价值的战时纸马克,并在国际贷款的扶持下恢复了较低水平的赔偿活动。鉴于其巨大的影响力,这一系列金融方案便被冠名为“道斯计划”。随着“道斯计划”的完成,德国人也将法国人赶出了鲁尔区,同时法国又继续从德国获得赔款。

上图:严重通货膨胀时期,用小车推着大笔钞票的德国人。
“道斯计划”也证明了美国金融业在德国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投资者纷纷进军德国,其中于1924年10月面世的“道斯贷款”由美国的400家银行和800家债券公司发行,此举引发了大量美国投资,并吸引了英国和其他资本的涌入。1924年至1930年间,德国借款的金额几乎是其赔偿金额的三倍,赔完款后的剩余资金被投入德国实业(福特和通用汽车都并购了数家德国汽车厂)、股票和市政债券,用于建设公寓、学校和其他基础设施。总的来看,外国贷款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货币贬值都减轻了德国的赔款负担,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正如货币贬值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一样,当美国资金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后断裂时,德国经济顿时又陷入了衰退。到1932年,德国工业产值仅为1929年的60%,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失业,还有数百万人被削减工资,且德国大部分银行倒闭破产。德国萧条是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最严重的萧条,刚走出恶性通胀不到10年,德国人就再度经历了第二场噩梦。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德国人转向民族社会主义。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赢得了18%的选票,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党魁希特勒也大肆宣称“我会确保物价维持稳定”,而且“这就是我的冲锋队所要做的”。历史学家尤尔根·冯·克鲁德纳指出,如果没有大萧条引发的灾难性后果,那么希特勒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综观从巴黎和会召开至战后初期的这段历史,可以说一切都与《凡尔赛和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幸的是,这是份妥协性质的文件,却两头不讨好,既没能让德国人心服口服,又让他们心生愤恨,当希特勒大权在握时,他撕毁《凡尔赛和约》的举动得到了数百万德国人发自内心的拥护,也为另一场更惨烈、影响更大的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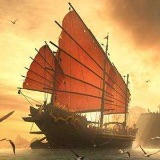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