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鸿沟,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已接近65%,对于中国这一巨型的农业国家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乡土中国正在向城乡中国转型。但是,中国城镇化目前尚面临一个显著悖论,即大规模的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所形成的常驻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鸿沟。由于这一悖论的存在,中国城镇化仍然只初步走完了上半程,即农民在就业和收入上挣脱乡土的过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镇化将经历下半程,即农民工重新在家乡的城乡社会空间体系中重新分层级沉淀下来,重构一个城乡之间的新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形态的过程。
一、挣脱乡土:中国城镇化的上半程
中国自1949年到1980年,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表现为低度城镇化,造成这种低度城镇化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刚性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以及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至20世纪末的城镇化初期阶段和21世纪初的高速发展阶段。在前一阶段,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是乡镇企业就业和农民外出务工,前期以乡镇企业为主,1990年代以后外出务工的作用才日益显现,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在乡镇企业大规模发展的时期,与“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模式相一致,中国采取了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路径,城镇化慢于工业化,依旧带有“低度城镇化”的特征。
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首先来自政策的推动,调整后的城镇化战略,极大的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其次,中国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迅速改善,城镇承载能力显著提升。最后,加入WTO以后,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快速建立,东部沿海地区很快成为“世界工厂”,为大规模流动人口提供了海量就业机会。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推动下,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经历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进程。2000年,中国城镇化率仅36.1%,到2020年已达到了63.89%。20年时间中农村人口净减少2.98亿人,城镇人口净增加4.46亿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从50%下降到了23.6%,合计共减少1.83亿人 。二十年时间中,中国由一个人口主要居住和生活在农村的国家转变成了人口主要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的国家,全社会主要就业渠道由农业转变成了二三产业。显然,世纪之交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乡土中国,而当下则已经转变成了城乡中国,中国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城镇化进程。
二、“半城市化”:大规模流动人口与中国城镇化的悖论
过去二十年,中国城镇化虽然飞速推进,经历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也具有一些自身特征。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一个最独特的特点是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存在。
七普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四分之一,中国形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城乡人口流动浪潮。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仅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规模巨大(比美国全国总人口还要多),更独特的是这一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长期“漂泊于城乡之间,形成“候鸟式”流动状态,而未在城市彻底扎根下来。中国之所以形成这种独特的城镇化模式,其中的一个核心机制就是地方政府以“经营土地”为核心的”经营城市”行为,这一机制与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流动人口等因素都密切相关。
“经营城市”既大力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极大提高了城市承载能力;同时又以低土地、低税费成本吸引了国内外产业投资,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海量就业机会。正是通过“经营城市”,地方政府将土地、金融、财政、招商引资、农民工就业等诸多要素联通起来,比较精巧而有秩序的推动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但是,这种模式本身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病,最核心的是由高房价等因素造成了流动人口在城市落地扎根的困难。
结果,在过去二十年中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就出现了一幅矛盾的图景。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园区日新月异,一派繁荣景象,甚至出现了明显超越现阶段实际需要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农民工长期“漂泊”于城乡之间,无法彻底完成城镇化。城市的繁荣与农民工的长期“漂泊”,都是这种城镇化模式“一体两面”的结果。在宏观统计上,这幅矛盾图景集中表现为两个不同步:一是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不同步;二是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同步。
因此,总体而言,中国城镇化可以说仍然只基本走完了上半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城镇化的重点应该会转移到流动人口的落地扎根上来,进而完成城乡关系的彻底重构,这可以称为中国城镇化的下半程。
三、回归乡土:城镇化的下半程
当前阻碍农民工在东部城市地带扎根的首要因素,仍然是住有所居问题。“经营城市”模式在大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工业园区开发和建设的同时,也必然导致城市住房价格高企。不仅如此,东部城市地带高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日常生活成本,也是阻碍农民工扎根的重要因素。除前述经济性因素外,农民工之所以更倾向于选择家乡的中小城市(镇)落地扎根,还与社会文化性因素密切有关。一方面,中国人具有很强的乡土或家乡情结,这是乡土中国最深沉的社会底蕴之一。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很强的完整性,他一旦远离家乡,在东部沿海地带彻底扎根,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这一重要的社会网络。
当然,现在的家乡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小规模的村落社区,而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横跨于城乡的新社会空间。由于交通、通信等各种基础设施的改善,市场网络的铺展,人们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等都从相对封闭和自成一体的村庄社区中解放出来,传统村庄也被高度整合到了更大范围的市场和社会网络之中。这一更大的新社会空间,最典型的就是城乡县域社会,即以县城为中心,以小城镇/集镇为节点,以村庄社区为基础的层级分明而又高度整合的新经济社会空间。农民工的真正城镇化和市民化,很大程度上会通过返回家乡实现,他们会在家乡的城乡空间体系中重新分层级扎根下来,尤其是县域范围内的县城和小城镇,是农民工返回家乡后的主要空间载体。
但是,当前来看,农民工逐步回归乡土,在家乡“分层沉淀”还只是一个趋势和势能,尚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和困难。首先,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关键,就是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其中最典型的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次,当前中西部地区县域社会能够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这对农民工真正扎根落地形成了更为根本性的障碍。在一些中西部县城甚至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去工业化冶现象,在县域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并显著低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县域第三产业则呈现“虚假繁荣”景象。
以县域为基础的新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形态的重塑,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行动单元。当前,由于农村中青年群体大规模外出务工,老龄人口留守在家种地,因此中西部地区普遍形成了一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形态。在农民工通过“分级沉淀”的方式逐步实现就近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这种“半工半耕”的家庭形态还会长期存在。总之,大规模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下半程最关键的任务之一。
四、结论
实现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的关键任务之一。农民工会在家乡的城乡间体系中分层级重新扎根沉淀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返乡农民工作为主体力量,将对以县域为核心的城乡空间体系和社会形态完成重塑,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形态将被塑造出来。但是,由于县域非农就业空间有限,农民工家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跨区域的“半工半耕”家庭形态仍然会长期存在,这也反映了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中国城镇化进程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称为城镇化的上半程和下半程。在城镇化的上半程,中国实现了空间和产业的城镇化,中国农民挣脱了土地和农业的束缚,加入到了城镇和工业的洪流之中,但这也形成了极大规模的长期“漂泊”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大规模流动人口的重新落地扎根,是城镇化下半程的核心,他们将在家乡的不同城乡空间体系中沉淀下来。中国城镇化的上半程是挣脱乡土的过程,而回归乡土则是下半程的主题。从挣脱乡土到回归乡土,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一次巨变。
从中国城镇化的下半程的路径和形态来看,中国的乡村振兴,不能机械和静态地来理解,要把乡村振兴战略放在城镇化下半程的历史进程中,放在城乡关系剧烈调整的动态格局中来把握。因此,乡村振兴就不是简单的村庄振兴,而是以城乡融合为轴线的县域振兴,以县城为核心纽带的全面发展。站在中国城镇化的上半程和下半程交会的历史瞭望台上,我们相信中国能够统筹好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动态辨证关系,为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探索出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乡村发现转自:《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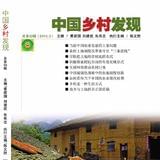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