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何被称为“国内音乐剧译配第一人”,这个1990年出生的浙江姑娘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和“大好前途”,选择从事音乐剧译配工作——这在当时的国内还未曾出现过,甚至都称不上是一份专业的全职工作。即使是在10年后的今天,国内从事专职音乐剧译配的人也屈指可数,据程何介绍,音乐剧汉化是一个“跨学科”的细分领域,需要掌握戏文系、声乐系、文学系、外语系等多种学科的专业基础,从业者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由于目前国内市场发展尚不成熟,相关从业者的收入并不高,大多数人都长期处于入不敷出、“为爱发电”的生活状态中。
即便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于音乐剧领域。他们向往自由,热爱表达,不甘于眼下的庸碌平常,愿意倾尽一腔热血,只为舞台上的燃烧。程何目前担任七幕人生音乐剧剧本总监,从业十几年,她参与了国内大部分引进音乐剧的译配工作,包括《我,堂吉诃德》《音乐之声》《狮子王》《妈妈咪呀!》《猫》《吉屋出租》《一步登天》等。她让引进音乐剧在国内舞台上有了更为本土化的呈现,很多人也因此而第一次走进剧院,开始感受和欣赏音乐剧独有的魅力。
以下是《瑞丽服饰美容》与程何的对话——
—你第一次接触音乐剧是在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接触音乐剧是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正好《剧院魅影》来中国巡演,我记得是在上海大剧院演了100场。我当时是在我的家乡湖州—— 一个18线小城市——碰巧看到了《剧院魅影》的广告,就对它产生了兴趣,因为Logo看起来很有意思。正好我有放学之后去书店逛一圈的习惯,然后在书店里看到了《剧院魅影》的磁带,就买了下来,回家听了之后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
—音乐剧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我最开始其实就是觉得音乐剧的歌特别好听,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喜欢听跨界的东西,比如莎拉·布莱曼,我当时特别喜欢那种古典流行跨界的东西,正好《剧院魅影》的原版也是她来演唱的,这也是我买磁带的一个原因。当时听了觉得这就是我要的感觉,音乐真的很好听,把古典和流行结合得特别好,这就是我一开始的想法。后来我把那盘磁带翻来覆去听了几十遍,才慢慢意识到不仅歌好听,它还讲了一个故事。那时候我的英语其实不是很好,还不能完全听懂里面的内容,但是它在我听不懂歌词的情况下把一个故事的起伏讲得清清楚楚,光是听音乐的情绪转换,我已经能感受到故事里面的情感,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迷人。
—是怎样的契机让你从一个普通的音乐剧爱好者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剧译配人员?
这个说来话长。首先是我意识到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从事科研,到了清华之后,我发现自己跟真正的学霸比起来差距很大,同时我又是特别要强的性格,一旦我在某个领域不能做到顶尖的程度,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给这个领域再添加一个中庸的存在。
在大二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能不能做出一点事情来,碰巧我的一个朋友老Joe*从国外回来,想做音乐剧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我们找到了现在的合作者,他鼓励我们做一个自己的剧本朗读会,去给一些潜在的投资人和观众做一个展示,看有没有人愿意为我们的作品买单。这种事情也挺常见的,就是把一个外国的剧本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然后做一个展演,让投资者和制作人来评判和提意见。
其实在当时,音乐剧“中文化”是一个不存在的状态,在1987年的《异想天开》和《乐器推销员》,还有1996——1998年的《音乐之声》之后,这些年就没有做过百老汇大型音乐剧的中文商业演出,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做了一件“开先河”的事情。
*约瑟夫·格雷夫斯(joseph Graves),百老汇著名戏剧导演、莎士比亚戏剧专家,
北京大学外国戏剧与电影研究所艺术总监。
—在对引进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你个人认为最困难的是哪一点?
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专业能力跟不上,包括英文能力、中文能力、视唱能力。很多英文原版的音乐剧也是从2001年左右才开始引进的,在2000年之前,其实并没有专业的人在做这些事。因为音乐剧的“中文化”是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这个领域要求掌握的内容跨了戏文系、声乐系、文学系、外语系这几个专业。它需要你对戏剧结构的理解,需要你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和语言学的能力,同时需要对英美文学有所研究,对一些历史和典故有所了解,还需要你懂乐理、会读谱,并且能做一定的阅读分析。而且它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少,也没有一个大学愿意去做这样一个跨专业学科,去培养一批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饱的学生。
—你被称为“国内音乐剧译配第一人”,恰恰说明你这类人才在行业内的稀缺,据你了解,目前国内有多少音乐剧译配从业者?
首先这个活儿如果真的全职做的话,是养不活自己的。所以现在绝大部分的从业者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在做音乐剧相关的工作,有的在做音乐剧制作人,也有的在做职业的教育者等。
因为这个工作的报酬很低,而且每部剧的打磨周期都很长,一年大概只能做两三个。一部剧就是一个零到正无穷的过程,你要做的话,就得从头跟到底,我有一部剧就是从2015年一直改到现在。如果你不签约公司,只靠接项目的话,肯定养不活自己。所以这个行业需要很多热爱,在全球都是这样,戏剧行业就是“用爱发电”的。
—回顾这些年的工作经历,最让你骄傲和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创作者,更准确地形容自己的话,我是一个传播者,我在做的事情是把其他语言的戏剧以中文的方式进行再创作,通过再创作完成对更广泛的中文母语人员的传播。我是国外音乐剧进入国内的重要一环,我觉得我这一环做得不错,我成功地进行了几次传播,让我喜欢的、我认为好的一些戏剧在国内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受众。
—在你参与译配和制作的音乐剧当中,哪一个对你来说具有更特别的意义?
肯定是《我,堂吉诃德》这部戏,它是我至今翻译过的作品当中相对评价最高的一个,我个人对它的文本也是相对比较满意的。
—如果要为之前从未接触过音乐剧的朋友们推荐一部音乐剧,你会推荐哪一部?
对于完全没有接触过音乐剧的观众,我会有两个选项:如果你喜欢传统一点的剧目,我会推荐《悲惨世界》;如果你比较欣赏现代一点或者潮流一点的东西的话,我会推荐《汉密尔顿》。《悲惨世界》的话,首先它的歌很好听,所以你会第一时间感受到它是一个很亲切的东西,其次是它在艺术上真的能够体现出音乐剧的叙事功力,你在听的过程中就能感觉到,它的音乐真的在讲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熟悉,也不用花心思去做功课,对入门者非常友好。推荐《汉密尔顿》是因为它真的很流行,而且它对音乐剧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就像说唱这种曲风,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喜欢、非常热爱的。我们怎么样去用说唱这种形式讲一个非常严肃、非常古板的课题,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也非常好听。
不过这两部剧目前在国内都看不到,因为还没有引进。所以如果想要现在就在国内看到的话,我可能要自卖自夸一下,我还是挺推荐大家来看《我,堂吉诃德》的。
正在巡演中的2022年音乐剧《我,堂吉诃德》
中文版十周年纪念版
左滑查看更多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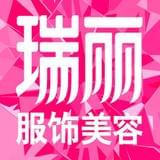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