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购买本书
全网首发(7.31发货),6.5折包邮(偏远地区除外),2周后恢复常规折扣
以山为业
东南山场的界址争讼与确权
丛书:历史人类学小丛书(第二辑)
杜正贞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关于本书
古代的文人、画家常常对山林寄托以出离尘嚣缰锁、比邻烟霞仙圣的想象,但现实中的山耕、山居,是另外一部历史。“以山为业”一方面是说人们以山场为生计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在说人们围绕着山场资源形成各种权利关系,这些权利关系,在传统中国通常被笼统称为“业”。
唐宋以来,东南山场被加速开发。从最初的“无主”状态,即山场上的所有资源对所有人都开放,到山场被现代测量手段精细测量划界、人们以各种权利证明对山场中的特定资源和各种权利进行确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界”的出现,是这个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界”是山场确权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也是山区的人们在“以山为业”的实践中,逐渐创制并明确的一套有关山场的知识。
关于作者
杜正贞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社会史、法律史,研究兴趣涉及基层社会、法律、习俗和民间信仰等。著有《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等。
目录
引 言 1
私占与定界 19
依山而居 21
树封立界 26
山坟与坟山 37
寺观占山 46
结界与经界 67
作为山林寺院神圣空间的“界” 72
南宋经界与寺观山场的登记 87
积步与税亩:山业记录中的界址和面积 97
争山争界 117
南宋的山界争讼 121
鱼鳞图册中的山场信息 132
明清山场争讼及鱼鳞册籍的应用 148
未登记山场的界址争讼理处 183
界址的定名和演化 203
民国时期的地籍调查与山界争讼 233
民国地籍调查中的山场信息 237
土地陈报与山场争讼 250
政区之界与山产之界 264
结语:界与确权的历史 277
“洞天福地”的另一面:作为生计资源的山 279
在“公地悲剧”之外:从历史角度看山场确权的出现 294
赋役制度与山场确权 309
山场的“权利束”与权利的边界 325
后记:山里人的故事 347
自 序
1930年1月13日,任职于浙江省建德县(今建德市)统捐局的安徽桐城人方琦(梅庵)向建德县县长告状①。据他说,自己早年即响应当地政府种植森林的倡议,在民国十七年(1928)春正式向县政府承买了位于东乡杨家庄的一处官山,整个承买程序的档案卷宗历历可查。
方琦在承买官山的申请书中说:
民素报实业主义,当民国七八年间即蒙张前知事良楷面谕提倡,即经在于杨家庄地方调查得无主官山数十亩,圈收入户,先后种植松树,为数不计……惟是山虽管有,税尚虚悬,图免日后之纠纷,宜谋产权之确定,自应查照承买官荒条例,报请勘查,估价给照,俾裕赋课而保永久,为此照绘山图,注明土名亩分,备书呈请,仰祈钧府鉴核,派员勘查饬估,仍赐转呈定案,须照执业,毋任企感。
申请书写得入情入理,也说明了承买官山的完整程序。经过田赋征收主任查勘、绘图、定价、山邻保证等程序,承买申请上报至浙江省财政厅。省财政厅重新核定山价,其间两次要求重新绘图。最后,在1928年9月9日颁发给承买执照。执照上盖着“浙江省政府财政厅印”的大红章,明明白白白地写着:
方梅庵承买坐落建德县东乡杨家庄(土名)徐回坞、塘吼垅地方官有官产山地……计开四至:东至徐家塘,西至山降,南至山路眠羊里,北至黄山杉树湾。面积东西共……(空白,加印“详细丈尺粘载图中”)△△顷三十亩一分△厘,每亩价银二元一角,共计价银六十三元二角一分。
这样一张官颁执照看起来已经确凿地证明了“产权之确定”。但是过了不到两年,因为要土地陈报②,方琦惊讶地发现掌管该庄地籍簿册的册书朱逊德已将前项官山③归入蔡姓、陈姓、郑姓等名下。
朱逊德是建德县城人士,家里世代掌管着东乡杨家庄的庄册,负责这个庄的钱粮国课和田土推收等一应事务。进入民国,他们在新政府里有了一个新名号,叫“清理书”,但其实职权并没有变。百姓缴纳税粮、过割产业都还在他们手上去做。1928年7月,老朱册书身故,朱逊德就从父亲手里承当了这份职业。不承想才过了一年余,他就被这个名叫方琦的外乡人以“私相授受”的罪名,告到了县长那里。
朱逊德的呈报也说得很有理据。他说,方琦曾拿着执照和山图到他那里要求登记,但是他查了自己手上的底册,发现财政厅执照中写明的四至范围内的山林面积,超出其上登记数字数倍。而且这些山并不是无主荒山,均系有人完粮之产。内计:“汪守芝一户山八亩八分,完粮壹钱三分二厘,系民国九年间奉前知事张谕饬,查明晰收;又陈凤林山七亩,完粮一钱五厘;陈兆余山三十四亩,完粮五钱一分,是十五、十六年间,凭各户老册晰收;又蔡汝标山十七亩三分,完粮二钱六分;胡德富山二亩五分,完粮三分八厘,由该户出立认字,认承开垦完粮,晰收过户。”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那么,这些山到底是有主的“完粮之产”,还是“无主官山”?1928年方琦承买官山的卷宗里保存了申请承买时再三查勘、绘图的档案,为什么彼时没有发现山主?册书手上的庄册和由省财政厅签发的执照,到底哪个才是更过硬的管业凭证?
其时主政建德县的蒋县长传集两方对簿公堂。出现在县政府堂上的,除了方琦、朱逊德两人外,还有庄册上登记的上述山产的“主人”,他们对自己的管业来历都言之凿凿:
问陈顺桃 你今年几岁?
答 四十一岁。
问 你系什么地方人?
答 本地下唐人。
问 你作何事业?
答 务农。
问 小坞的山你有多少税呢?
答 是民外婆家遗下的坟山,土名徐湾坞,计税五分,民家经管数十年了。
问陈凤林
答 民叫陈朝贵,凤林是民父。
问 你今年几岁?
答 三十八岁。
问 你是何职业?
答 务农。
问 你住何处?
答 住在郑家垄。
问 你的山究竟什么字号?
答 民的山坐落八百七十一号,土名火烧山,计税七亩,内有二分送王姓做坟的。
问 这块山已经方姓买去承管,你应该晓得吗?
答 方姓并没有来管过,我也不晓得。
问郑福培
答 福培是我娘舅,民叫方锡韩。
问 你今年几岁?
答 四十六岁。
问 你是何处人?
答 仙居人。
问 你住何处?
答 住小里埠。
问 你作何事业?
答 务农。
问 徐家塘的山你有多少?
答 计有十余亩。我娘舅还有几亩地,都由我还粮的。每岁下半年,他有姑伯兄弟来此一次。
问陈大森
答 大森是民父,我叫兆馀。
问 你今年几岁?
答 三十八岁。
问 你住哪里?
答 住小里埠。
问 你什么职业?
答 务农。
问 小坞的山你究竟有多少?
答 小坞即塘海垄,民有十余亩山,还是洪杨前管起。今呈上老册一本,请阅。现在方姓又写一张契送我,请看。
问蔡德松 你今年几岁?
答 二十三岁。
问 你住何处?
答 住郑家垄。
问 你做什么职业?
答 务农。
问 你有几亩山,究竟坐落于何处?
答 冀为坞有六亩多山,塘海垄有九亩山,塘海垄外面有二亩山。曩时张知事提倡森林,民国七八年间发贴布告,无论官荒私荒,都准农民垦植森林。至民国十四年由先父手晰收户册是实。
三月十四日供单
这些人与方琦、朱逊德不同,他们是真正在山里生活的人,是管山的人。在他们的观念中,山产或是祖传(尤其是坟山),或得自亲友的赠予或托管,或有着长期实际占管以及承粮登记的事实等,这些都是拥有山场权利最重要的证据。
从这些“山主”的供词中,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这些山场“有主”的历史其实很短。在民国时期陆陆续续到册书朱逊德那里“晰册”(承粮)之前,他们管有这片山的确切时间也都不清不楚。其中只有一个人提到一个含糊的时间点“洪杨前”,即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这里之前。在建德,大量山场失管、无主的状态,的确与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情况已经很难追述,而此后这些一度失管、无主的山场又是怎样被重新占有、重新确权的呢?
在清代的制度下,一般的程序是:人们向县衙提出申请,县衙责成册书进行调查,如果确为无主之山,即报告县衙,由县衙出具执照,业主凭执照回到册书那里登记入册,从此开始每年交纳税赋。在这个程序中,册书的晰册本来只是一个中间环节,但是由于赋税征收由册书把持,人们往往绕过县衙这一层级,直接在册书那里登记、交税。换言之,大量山产已经有山主缴纳赋税,但是在县衙门里却可能完全没有登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普遍。正如朱逊德在具呈中所说,它成为一种在国家制度之外的“习惯”。
方琦(梅庵)是一名外乡来的地方公职人员,他挑战了当地庄册的“习惯”和旧的山场占有方式。他的“武器”是1914年7月31日颁布的《官产处分条例》:“迨民三以后迄于今,兹凡无人承粮之产,国家为收入起见,一律划在官产范围,必须经过国家处分价卖给照,方可取得产权。”根据此条例,以报荒承粮获得“产权”的制度,被新的官产承买制度所代替。正如他在呈状中所说:“对于册书职权论,民三以后,清理官产条例未奉废除。凡遇荒山荒地,只有官厅处分,毋再准民间报荒升科理,今册书为蔡、陈等姓晰收,而时间又明明注民十四年之后,此项晰收显于条例抵触,当然根本取消。”《官产处分条例》对官产的处分分为三种形式:一变卖、二租佃、三垦荒,并且在第十八条规定“以前私垦之官荒自本条例施行后应补缴荒价,照章升科。”④换言之,人们在报荒升科之前,需履行承买的环节,才能获得产权。这在产权获得方式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这场纠纷中,方琦正是利用了这条新的法律。在被问及承买时为什么没有到册书那里查询时,他说:“我们查不来的。”后来,他这样解释“查不来”的含义:
无主之产,册书利在民间收付,于官卖非其所愿,盖一公一私绝不相容者也。承买官产而曰必先查庄册,是犹夺食于虎口……民间同一出钱,恐将乐于册书私人之拨付,又何事报官勘查,缴价请照,作种种麻烦之手续乎。
方琦指责说,册书所言私晰“习惯”不过是当地人规避国家制度的方法。而他自己何尝不是在刻意回避于己不利的地方习惯呢?1928年方琦承买荒山的一系列程序中,负责此事的田赋征收主任和作为上级最终核审机关的浙江省财政厅,也都没有要求其向册书核实官荒。这种对旧习惯和地方制度的漠视,也许源自民国新政权对册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套旧体制的反感,但这种漠视显然于清理山场产权的目标并无补益。
这场山产纠纷距今仅仅百年,它凸显了官产承买制度和以承粮纳税获得管业权的旧制度的差异,并且生动再现了在民国推行山林国有化和地籍整理的大背景下,地方上各类人群如何应对和利用这种制度的转换。当然,其中包含的新旧制度的差异还不止于此。例如,为什么在财政厅给出的执照上,这片山的面积是“东西共△△顷三十亩一分△厘”,但是朱逊德却说四至之内的面积超出此数数倍?两个数据分别是如何得来的?又例如,为什么执照上只标有山场土名、四至,而朱德逊的庄册中,每一块山都有一个或数个字号?同时代的人们对同一片山的认识和记录为何有这样的不同?这种对山场的认识(知识)是如何产生的?等等。
从这个个案出发,在历史的维度上,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究:这片山场的权属之争是第一次发生吗?这些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第一任的主人?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在明代或者更早的时代,当地人是怎样利用、管理这些山场的?他们怎样确权?人们以山为业的故事到底该从何时开始讲起呢?⑤
历史人类学小丛书 第二辑
以山为业——东南山场的界址争讼与确权
杜正贞 著
想吃好的——明清中国的稻米种植和消费
张瑞威 著
妇人杨氏之“复活”——雍正年间麻城杨氏案研究
卜永坚 著
乡村图景——贺登崧的华北民间文化之旅
邓庆平 著
游牧、农耕与都市——蒙汉交融与土默特社会
麻国庆 著
边徼圣境——明清大理的土官政治与地方社会
连瑞枝 著
高玉柱——一位民国西南女性精英的生命史
温春来 著
归去来兮——明清以降南麂列岛的海域人群
张 侃 著
浮生的土地——番禺沙湾的宗族与沙田开发
刘志伟 著
民间的秩序——莆田平原的水利与仪式联盟
郑振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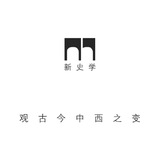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