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吴某于2008年7月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富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凯公司),吴某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有关贸易及投资咨询业务。

同年12月,吴某成立富凯公司驻上海代表处,并以其名义租赁上海市索特大厦(该大厦系高端写字楼)的办公楼作为办公场所。公司成立后,吴某指示公司员工随机拨打电话并开设相关网站宣传公司的投资理财产品,以招揽投资人。
该公司对投资人许诺到期归还本金并每月以1%-3%的固定利息作为收益回报。截至2009年5 月,吴某通过上述方式先后与杨某、谢某、李某等共11名投资人签订各种投资理财协议,吸纳上述11名投资人投资款共计人民币214.5万元。

吴某将该款项部分用于投资日本某株式会社基金项目,部分用于维持公司运营等。至案发时,吴某向上述投资人按约定利息支付的利息款共235,292元,归还李某、段某、戚某、张某四人全部或部分投资本金共计74万元,除此之外,吴某从投资人处获得的投资款中仍有117万余元未能归还。
2009年5月,当吴某得知其投资的基金项目失败而难以收回前期投资款后,先授意他人将原由吴某本人出资设立的深圳市立信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信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通公司)。

后又以其表哥林某某的名义设立凯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隆公司,经查明该公司成立后未运作过任何项目),同时将凯隆公司办公地搬迁至本市越洋广场的万茂金融中心高端写字楼。
自2009年8月起,吴某在明知没有投资项目和偿还能力的情况下,用其实际控制的信通、凯隆公司的名义,通过开设网站等方式对外宣称提供由信通公司担保的投资理财产品,并向投资人承偌到期归还投资本金以及每月1%-3%的固定利息收益作为回报。

截至2010年1月,被告人吴某通过亲友、业务员介绍等方式先后与周某、杨某、张某等9名投资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向上述9人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130万元。
截至案发时,除向9名投资人支付约定利息款30,754元,以及郑某索回部分投资本金3万元外,其余款项因吴某支付员工工资、公司运营费用及前期投资人本息等而消耗殆尽。2010年3月,由于协议陆续到期而无力偿还,吴某遂离沪逃匿。

分歧意见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吴某成立公司的目的是违法犯罪,且公司成立后以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人吴某的前行为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同时,被告人吴某的后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明知没有投资项目的情况下向郭某等9名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数额巨大,依照我国《刑法》第192条之规定,吴某的后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吴某及其辩护人认为,本案中吴某通过合法成立的公司对外经营,以公司名义收取投资款且投资款用于维持公司运营、支付工资等目的,该行为是单位的一种经营行为,故本案系单位犯罪。

吴某的后行为为维持公司运营等目的而筹资,其主观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将投资人的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且吴某离沪的原因是在投资人及员工的围堵下被逼无奈的选择。因此,吴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
此外,通过亲友、业务员介绍的9名被害人亦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公众”,不是集资诈骗犯罪所指向的对象,故吴某的后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争议焦点
第一,吴某的前行为成立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
第二,吴某的后行为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三,吴某的后行为中,通过亲友介绍的9名被害人能否成为集资诈骗罪中的“社会公众”。

本案的分析
(一)吴某的前后行为均属于个人行为
吴某前行为属于个人行为,成立自然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这是因为,在香港注册的富凯公司虽经合法程序设立,具备单位成立的形式要件。但是,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从事有关贸易及投资咨询业务,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核准,不具有合法集资的资质,其通过上述方式对外宣传招揽理财投资人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非法集资。
此外,经查明,该公司除通过上述方式吸收社会公众资金以外,并无其他合法业务。因此,可以认为吴某是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即该公司的设立目的非法,且公司设立后以从事非法募集资金为其全部业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25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吴某作为富凯公司的负责人虽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募集资金,并将募集资金用作投资和维持公司运营等目的,但因该公司的设立目的非法,且公司设立后以从事非法集资犯罪为主要活动,因此,该公司不具有刑法上单位犯罪主体资格,吴某的前行为成立自然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吴某的后行为属于个人行为,理由同上,在此就不再赘述。

(二)吴某的前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控辩双方均认为吴某的前行为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首先,吴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吴某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富凯公司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核准,并不具备合法募集资金的资质。
吴某在明知没有集资资质的情况下,通过指示员工随机拨打电话并开设相关网站宣传投资产品等公开方式吸引投资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观上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其次,吴某客观上实施了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吴某通过上述方式宣传投资产品,并向投资人承诺到期归还本金以及每月1%-3%固定利息作为收益回报的方式,总共吸纳杨某、谢某、李某等11名社会公众存款214.5万元,数额巨大,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属于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因此,吴某的前行为触犯《刑法》第176条之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三)吴某的后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吴某的后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吴某的后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本案中争议焦点之一。辩护人认为吴某不具有这一主观目的,其理由是:“吴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也并非将集资款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挥霍,而是为维持公司运营、支付员工工资等目的向亲友筹集资金,且吴某是在被投资客户及公司员工围困下被逼无奈而离开上海。
其主观上并非想逃避返还集资款,故吴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集资,不能成立集资诈骗罪。”有人认为:吴某的后行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前所述,对集资诈骗罪中该目的的认定主要是通过司法推定实现的,重点考查行为人是否具有“排除意思”。

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结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防止客观归罪。首先,吴某该行为具有排除权利人(即投资者)对资金的支配和控制,将投资资金作为自己的财物进行支配的意思。
吴某在明知没有投资项目和偿还能力的条件下,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对外谎称提供附有担保的投资理财产品,以到期还本和支付 1%-3%的固定月息收益为诱饵吸引投资者,实质上是一种诈骗手段,目的在于募集资金,其主观上并无返还的意思,由于没有投资项目,客观上亦无法返还投资者本金及利息。

吴某将吸收来的资金用于支付前期投资人本息(实际就是一种“借新偿旧”的行为),维持公司运营,虽然不是用于个人挥霍,但通过吴某的行为表现可以认定吴某主观上具有排除投资者对资金的支配,将投资者的资金作为自己所有物进行支配和利用的意思。
其次,吴某主观上没有回报投资者的意思。吴某的公司既没有投资项目,也没有其他合法业务,其吸收的资金根本无法投入到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按照约定回报投资者。据此,可以认定吴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通过亲友介绍9名被害人是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公众”,吴某后行为构成非法集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
如果吴某后行为中的9名被害人不能成为非法集资的行为对象即“社会公众”,则吴某的行为就不构成非法集资。有人认为,这9名被害人是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公众”。如前文论述得出的结论,“社会公众”指的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其概念的核心在于“不特定”上,“不特定”是从纵向上说明犯罪对象处于随时增加的可能。

行为可波及的范围广泛,行为后果具有不可控制性,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实质违法性。本案中,该9名被害人部分是通过吴某朋友程某介绍、部分通过其他业务员何某、李某等介绍而来。
首先,从吴某主观上募集资金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来看,其授意员工随机拨打电话并开设网站宣传投资产品,通过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方式招揽投资人以募集资金,其主观上对于招揽投资对象并没有特定的指向和范围,不管其客观上通过这种方式是否募集到资金,其主观上具有面向社会公众集资的故意。

其次,从募集资金的对象上来看,这9名被害人并不是吴某的亲友,而是通过介绍而来的投资者,其范围是不特定的。并且,如果吴某没有案发,那么该案被害人还有随时增加的可能,符合社会公众的“不特定性”。
因此,吴某非法集资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这9名被害人是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公众”。综上所述,吴某的后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未经国家有权机关批准,使用诈骗方法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数额特别巨大,构成集资诈骗罪。

(四)吴某涉案行为的罪数形态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通说以犯罪构成作为罪数的判断标准。根据此判断标准,吴某的前后行为分别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吴某作为一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符合刑法关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要求。
吴某的前行为主观上具有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数额巨大,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因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吴某的后行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使用诈骗方法向周某、杨某等9名社会公众募集资金。

数额巨大,既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又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因而构成集资诈骗罪。且吴某的前后行为之间没有任何牵连、吸收等关系,符合不同的犯罪构成,因而吴某的前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吴某的后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应数罪并罚。

本案的研究启示
本案中,吴某前后两个行为的行为方式基本相同,都是授意员工随机拨打电话、开设网站宣传投资产品,并许诺到期还本付息的方式进行集资。由于吴某第一个行为具有明确的投资项目,并将集资款用于维持公司运营而认定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吴某第二个行为因没有投资项目,并将集资款用于支付前期投资人本息,而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这也是近年非法集资案件呈现出的一个特点,即行为人一开始往往为了生产经营、扩大生产、或是资金周转的目的开始集资,后因资金链断裂。

为了偿还投资人本金以及许诺的高额利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继续进行非法集资,最后案发。如浙江绍兴叶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信用卡诈骗案;浙江温州吴顺陆等四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案等。
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重要标准,准确认定该主观目的对行为人行为的准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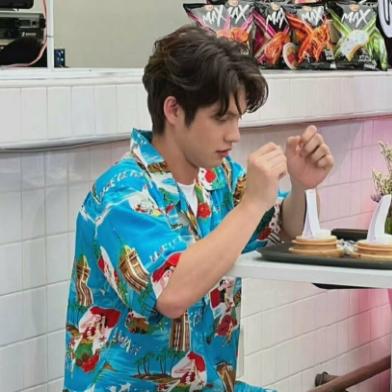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