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09年12月20日,这又是一个星期天,北方一座小城的公安分局刑警队队长罗士杰长下午就可以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妻子了。
探望病人的时间终于捱到了。
当他蹑手蹑脚地推开静悄悄的病房房门时,迎面看到妻子正缩着身子,藏在羊毛毯下瑟瑟发抖。他快步走到床前掀开毯子,妻子闭着眼睛恐怖地尖叫起来。
“别怕,是我!你怎么啦?”罗士杰用手按住妻子颤抖的肩头。
当妻子看清原来是自己的丈夫时,才惊魂稍定,嗫嚅着说:“你,你快转过去看看。”
罗士杰转过身,发现妻子邻床躺着一具用白布遮盖着的人体,“怎么,邱小露怎么了?”
“吓死我了。”罗士杰妻子用手捂住眼睛。
“亏你还是警察的妻子呢,怕什么。”罗士杰竭力安定妻子的情绪,使她慢慢镇静下来。罗士杰走过去,伸手掀开邱小露脸上盖着的白床单时,竟也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仿佛白床单下正有一种恐怖向他袭来。邱小露平时那张娴静漂亮的面孔不见了,满脸的肌肉正紧紧地抽搐在一块儿,拧扭在一块儿……随即,他惊奇地发现邱小露的脖子上系着一条白色的围巾。
“难道是被人勒死的?”他边想边用手拉了拉围巾,不意白围巾显得松松垮垮的。他索性取下白围巾,邱小露那雪白的脖子上并没有被勒的痕迹。
奇怪!
这时,门开了,进来两个男护理员,手中推着担架车,看样子是想把人拖走。出于职业的本能,罗士杰上前探问道,“她是怎么死的?”
一个男护理员瞟了他一眼,信口说道:“医院里死人,总是病死的喽。”
“她得的是恐惧症。”又进来的一位中年医生补充说,“今天凌晨她大喊了一声,随后就死了。”
罗士杰陷入沉思。每次来医院探望妻子,虽然没有直接跟邱小露说过话,但从妻子那儿,罗士杰还是了解了一些有关邱小露的情况。邱小露是由于受到惊吓刺激而进院接受治疗的,前些日子已差不多痊愈,却不料……
“请你们暂时不要把尸体运走。你们报告过公安局了吗?”罗士杰问道。
“这属于正常死亡。”那中年医生推了推头颈里的听诊器,说,“她是精神病人,病情完全受情绪控制,只需一个幻觉,一丝惊恐,就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以至发生生命危险。”
突然,医生似乎觉得眼前发问的这位有些不同寻常,便问道,“你是……”
“我是分局刑侦队的,”罗士杰亮出证件,“请你们暂时不要破坏现场。”
的确,仅从外貌来看,罗士杰绝不会让人想到刑侦警探之类。他高高瘦瘦的个子,活像一根“晒衣裳的竹竿”,何况又是便衣,然而就在医生和护理员都疑惑不解的当口,罗士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了几个号码键,喊道,“李兵,你马上带法医到铁路中心医院来,住院大楼6病区17号床,对,快一点!”
不一会儿,外面跑进来四个身着警服的人,跟罗士杰打过招呼后,即开始勘察现场。
很遗憾,毫无结果,除了刚才那三位医护人员和罗士杰的脚印外,并没有其他人的足迹,因为工务员一早已经拖过地板了。
这时,罗士杰妻子轻声地对他说,“你不知道,今天凌晨邱小露醒来时,突然惊叫起来,那声音像是死亡正在向她逼近,恐怖至极发出来的,我见她拉着头颈里的白围巾。”
“白围巾?是她的?”
“好像不是,从来没见她戴过。”
那么,这白围巾是自己飞来的?
罗士杰陷入了沉思。哦,恐怖,魔鬼。心理学上使用的“联想”使他把各种表象联系了起来。白——黑,恐怖——静谧,魔鬼——人。根据这种无边无际的联想,罗士杰判断邱小露的死不会是正常死亡,肯定有着某种复杂的背景。于是,他提出要解剖尸体。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死者母亲的激烈反对。
这是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妇人,她恸哭道:“这是我的孩子,我唯一的孩子,你们不准动她!”
很显然,要说服这样的母亲是很困难的。解剖只能秘密进行。
解剖结果显示:死者胃囊中并没有任何有毒成分。这更说明邱小露是被活活吓死的。
罗士杰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凌晨,病房里静谧得有些可怕。一个幽灵,蹑手蹑脚地推开了房门,来到邱小露的病床前,就在邱小露惊恐得睁圆双眼时,幽灵狞笑着举起了那条惨白的围巾……白围巾,白围巾,罗士杰的思绪中老是晃动着那条白得有点耀眼的围巾。
罗士杰将白围巾给邱小露的母亲看,这位悲痛之中的母亲更是悲不能禁,双泪长流。她告诉罗士杰,这条真丝白围巾是邱小露生前最喜欢的,她已好久没见女儿戴过了,入院以后更是没有戴过,怎么会出现在医院里呢?只是在女儿病后,听女儿在梦呓中叫过,“围巾!围巾!”那声音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白围巾——恐怖——死亡,这种联想符合逻辑吗?罗士杰手里抚摸着白围巾,手感光滑而又柔软。他下意识地把白围巾往自己脖子上围去,在感到一股冰凉的同时,脑子里突然触电似地一震,仿佛一下子开了窍。他立即召来花蓉、李兵、张伟甲等手下强将,一一面授机宜:“开追悼会那天,你们分别……”
殡仪馆内哀乐阵阵,空气好像凝固了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邱小露的追悼会设在一个中厅,一切均已准备就绪,亲朋好友,正纷至沓来。然而进入追悼厅内的人无不掉头回顾,互相窃窃私语几句,又释然无事地回过头去。原来,在中厅的门口,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穿着入时,俏丽但不轻佻。她身披白色的裘皮大衣,脚蹬黑色的长统皮靴,站在门口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
然而使悼念的人们大惊失色的是,这一身打扮活脱脱是邱小露的再现,尤其是脖颈里围的那条白色围巾,不是邱小露又是谁?
当然,在吃惊之余,经过仔细分辨,熟悉邱小露的人还是能够发现,她不过跟邱小露有点像罢了,真正的邱小露此刻已经躺在那道黑色的帷幕后面了。
站在门口的这位姑娘其实是女警花蓉,她是根据罗士杰的吩咐,故意化妆打扮成邱小露的模样以观察来客反应的。而罗士杰自己则和李兵、张伟甲一起扮成参加追悼会的客人,分散在厅内四处,一双双火眼金睛不动声色地扫视着进进出出的人。
一个中年妇女远远走来,看见站在厅外门口台阶上的花蓉,下意识地猛然收住脚步,几乎就要后退,再定下神细看,这才绕着花蓉远远地从另一边进了厅内。罗士杰朝这女人侧侧脑袋,李兵会意,立即跟了过去。
又来了个矮个男青年,门口抬眼瞥见花蓉正朝自己微笑,这一惊不小,手中的提包“啪”地掉在地上。等他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从地上捡起提包,强作镇静,眼睛仍盯着花蓉,脚下一步一步地从另一头溜进了追悼厅。张伟甲也若无其事地跟了上去。
此时追悼会已经开始,花蓉想回到厅内,罗士杰轻轻地对她说,“再等一会儿,等到绕场告别的时候再进去。”
“还会有人来吗?”
“先等一会儿,看看再说。”
果然,才5分钟不到,弯道上转过来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他刚踏上台阶,花蓉正从门后转出,又恰恰是一阵风把她胸前的那条白围巾吹得遮住了脸。那位青年像是突然僵住了,脸色惨白,随后一个趔趄,差点从台阶上跌下来。
花蓉轻启朱唇,娇滴滴地问道:“去参加追悼会的吗?请吧!”
“不,不,”男青年朝花蓉脸上又瞄了一眼,这才恢复了常态:“噢,是的。您是……”
“我是邱小露的远房表妹。请进去吧。”
这时,罗士杰仿佛气喘吁吁地刚刚赶到,一边连连说,“来晚了,来晚了,”一边傍在男青年的身边一同进了追悼厅。两人一前一后地排在瞻仰遗容的队伍里,缓缓地朝前走着。当走进邱小露的灵床时,罗士杰用眼睛的余光密切地注意着男青年的脸。他发现,那张略显紧张的脸上呈现出种种稍纵即逝的复杂表情。痛苦?忧伤?内疚?似乎是,又似乎不是。罗士杰心中更添一层疑窦。
蓦地,一阵悲痛欲绝的长嚎声震大厅,邱小露的母亲在第二次走到灵床前时,终于抑制不住,不顾一切地扑在女儿身上大哭起来。顿时,队伍大乱,互相挤成了一团。才一转眼的工夫,罗士杰发现那个男青年已经不见了。他不由举目搜寻自己的三名手下,不见李兵和张伟甲,却看到花蓉正站在那位中年妇女的身后,朝自己微徽一笑,便放下心来。他知道,张伟甲仍在盯着那矮个青年,李兵或许也已经盯上了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的那个英俊青年,于是便排在队伍中,一心一意地走完了第三圈,正式向这位不幸的姑娘道了别。
回到局办公室里,罗士杰坐在办公桌后,一任思绪浮想联翩。一条白色的真丝围巾在不停地飘拂,一会儿飘到那位中年妇女的胸前,一会儿又飘在那矮个青年的头颈里,接着,矮个青年变成了那个英俊青年。罗士杰明白这是形象逻辑受到外界的刺激在起作用,他不想打断这种在他看来十分有益的想象。恰在这时,张伟甲推门而入,花蓉紧随其后。他们分别汇报了跟踪侦查得来的情况:
矮个男青年系邱小露小学时的同学,两人青梅竹马,相处甚好,成年后,男青年虽然个子长得较矮,感觉有些自卑,但对邱小露的感情却与日俱增。前些时候,他曾给邱小露发过短信,表明了自己的爱慕之情,邱小露在给他的回信中却委婉而明白地表示了拒绝之意,引起他心中不满,因而,不能排斥他的作案动机。
中年妇女名叫邱小晴,是邱小露的堂姐。她们的父辈是亲兄弟,都是小有产业的人,都只生了一个女孩儿,如果邱小露死亡,她有可能继承一部分叔叔的遗产。而且据从派出所了解到的情况,她近来在从事服装批发生意时,可能蚀了本,所以,她作案的可能性也并不能否定。
正说着,李兵一头撞了进来,大口喝了一杯水,报告说,那个英俊青年是市医学院的走读学生,读的是精神病学专业,名叫查志国。校方并不掌握他校外的情况。他住的地址是花园路55号。
“花园路?”罗士杰不禁重复了一遍,“那他与邱小露住在一条马路上?”
罗士杰看了一下手表,对部下说,“今天晚上,三位随我一同去拜访一下这位与死者不是邻居的邻居。在这之前,请各位查出三位嫌疑对象在案发那天的活动情况。”
四花园路一边是高级住宅区一边是未改造的平房区。这条马路行人稀少,马路两旁,法国梧桐粗壮茂盛,橙黄的路灯透过梧桐树叶酒下斑斑点点的光亮,更增添了这条马路的神秘色彩。
罗士杰一行在路端就跳下了警车,步行过去。在一个弯角的夹缝里,总算看到了55号门牌。这间平房虽然简陋,倒也干净整齐。罗士杰笃笃敲了敲门,一位老妇人便把门打开了。显然,这是查志国的母亲。罗士杰说他是查志国学校的老师,来家访的。她说,查志国凑巧不在。罗士杰说,这不碍事。于是他和查志国的母亲聊了起来。大约半小时光景,他礼貌地告辞了。
罗士杰对这次“家访”十分满意。查志国母亲不仅道出了“孩子脾气太犟”,“有很多热心人替他介绍对象都不要的”怪脾气外,还说出了“有人亲眼看见他同一个戴着白围巾的姑娘走在一起”的重要情况。
当他听到这一消息时,差点跳起来,“那姑娘是谁?”他问道。
“这倒不知道。”老人家叹息着摇摇头。
罗士杰忽然发现墙角上挂着一张和查志国一模一样的遗像,于是问道:“老人家,这是谁的照像?他和查志国真是像极了!”
“噢,这是志国的哥哥志强。他俩是双胞胎。——唉,病死的。”说着,伤心地擦了擦红了的眼圈。
罗士杰在返回的路上,细细思忖着。那戴白围巾的姑娘究竟是不是邱小露呢?结论很难下,因为这种白围巾生产量大,在市面上比较抢手,戴的人不少。
综合调查结果表明:邱小露的堂姐邱小晴,星期天一早拎着菜篮子和她丈夫一起去菜场买菜,路上正好碰上居委会一个干部,他们三人一起排队买肉、买鱼、买蔬菜,一边闲聊着,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回到家门口时才与居委会帆布分手。那个矮个青年叫庄德安,是一家造纸厂的工人,星期六晚上他上夜班,星期天早上六时下班,被一个同事拖了去喝早茶,八点多钟回到家,那位同事因家中房屋正在大修,早上就睡在了他家里。这两位,基本上都排除了嫌疑。
唯有查志国,身上的疑点越来越集中。星期天早晨五时许,同在公园打拳的一老人曾看见过他,但他没练几下就不见了,因此,他作案的可能性最大。
目标集中在查志国身上了。但他是怎么作的案呢?
“用一条白围巾把邱小露勒死?可验尸报告说并没有发现死者头颈里有被卡勒的痕迹呀。”李兵不知点了第几根香烟了。
“戴一张‘夜狐脸’去吓她?恐怕也未必就能把人活活吓死吧。”花蓉也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现场也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证明查志国去过哪里呀。”张伟甲不停地挠着头皮。
“我们现在假设是查志国杀了邱小露,关键是要说明查志国为什么要杀死邱小露。”罗士杰在屋内踱着方步,像是自己问自己,又像是在问别人。
医科大学精神病学专业的本科生。恐惧症。白图巾。“夜狐脸”。英俊青年。遗像……罗士杰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不断地互相作用。他充分展开他那富于联想的大脑。
唔,对了!也许应该先查清查志国的哥哥查志强是怎么死的。他立即命令花蓉和李兵去各家医院,自己则带上张伟甲直奔邱小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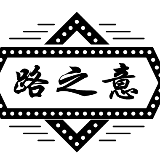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