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社员焦淑婵一家,是山西省运城县车盘公社郑费大队一个小康之家:老汉牛定国在太原当工人,月薪六十多元;未婚的儿子联民、联仓在家务农,可谓是两个血气方刚的壮劳力;淑婵一日除忙活三餐外,见缝插针还下地干活,在队里也顶上半个劳力了。四口之家,拿钱、挣钱的就占了三个半,一年到头吃穿不愁,花钱顺手,光景岂不美哉!
然而,月有缺圆,天有不测风云。1980年11月6日夜间,十七岁的小儿子牛联仓被凶杀在村南五里外的硝池滩。
一具男尸,头南脚北,俯卧在硝池滩老公路排水沟的一滩血泊中。
分散在运城、解州四十里一带的十几个公安人员,一个钟头前接到报案后,几乎在同一个时刻11月7日晨八时许,前后脚汇集到牛联仓的被害现场。
指挥现场勘察的,是运城县公安局梁副局长。他一跳下自行车,环视被害现场,就发现在围观群众圈里,有一个青年蹲坐在尸体近旁,当即问:“他是谁?”
刑警队长李文法回答:“死者的哥哥牛联民,是也昨晚最先发现尸体的。”
现场勘察绝对保密,非公安人员怎能进入现场?梁副局长抬手一挥:“无关人员全部撤离现场!”
听取了现场汇报梗概,梁副局长依据死者是到解州火车站卖一块带日历的走私表途中被害的情况,旋即决定把侦察范围的重点,放在火车站与死者所在的郑费大队两个方向,并相应组织了三支力量:第一路到郑费大队重点察访;第二路赶赴车站方向侦察;第三路实施现场勘察。其余人员留现场附近搜索,重点觅寻罪犯作案后可能抛弃的凶器。
“11·6”案件的侦破序幕拉开了。
第一路很快就摸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据车站行李员反映:11月6日午夜之前,有个上穿劳动布西服,下着咖啡色筒裤,且留着大背头的青年,腕露带日历走私表,与另一位操太原口音的青年在候车室鬼鬼祟祟溜达过。从衣着外形特征判断,这个着劳动布西服的青年乃是公安局要缉拿的流窜犯——“大背头”。
那么,他腕露的那块走私表,与死者有无联系?而东行太原的186次列车,也恰在发案之后的凌晨一点途经解州车站,“大背头”一伙是否作案后携赃外逃?
到车站售票处检询,东行的186次列车,售出车票两张。票数吻合,更增加了侦查人员对“大背头”的怀疑。
晚饭后,忽然又获群众报告:下午六时三十分,有人见“大背头”进了解州电影院。《大篷车》正在放映中。侦查员借助银幕折射的微弱光线,扫视着一排排座椅,搜索着一张张面孔,想从中“筛选”出“大背头”,但未能发现。
一个钟头之后,电影散场了。刑警、民兵守候在影院门口,警惕地扫视着媚动的人流:终于,穿劳动布西服、咖啡色筒裤的人出现了……没错,是他!
经过两个钟头的讯问查证,“大背头”在凶杀案中的怀疑被排除,他的其它问题,当另案处理。
郑费大队的重点察访,也正在同时进行着。还是在现场刚接触案情时,细心的侦查员就对死者的哥哥划上了问号:“头天夜里就寻见了尸体,为什么第二天才报的案?”此时此刻,第二路侦查人员不谋而合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是受害者,还是凶手?牛联民必居其一。
郑费大队的查访,就从认定牛联民在案中处何位置开始。
侦查员慢声细气地询问:“牛联民,你昨天晚上十点就找到了兄弟的尸体,为什么等到今天早上才报案?”
牛联民这个粗野大汉,转动着双目回答:“我寻尸回来赶到大队院,门从里关着。我隔门缝问治保主任在家吗?看门老汉光说到运城开会了,没有给我开门。”
查对。结果是;看门老汉夜里从未离开门房一步,根本没有听见牛联民叫门,更没跟他搭过话。
假话——刚接上“火”,就给侦查人员划了一个问号。
侦查员继续问道:“你说怕兄弟天黑去车站卖表被人暗算,昨晚六点在村口挡住他的自行车,这以后的时间你都干啥了?”
牛联民又续了一根烟,喷吐着团团烟雾,稳了稳略微慌乱的神色:“我夺过自行车后,绕村边拐进大巷,回家放下自行车,就到路北小学校看电影了。”
“什么片名?你进场时滨到什么地方?”
“咝咝”的烟头快烧着手指了,牛联民也忘了扔:“《甜蜜的事业》,演到那男的女的生娃多。”
侦查人员又派人询问公社的放映员。结果是:电影晚七时开映,从拷贝的转速推测,画面至此,约八时许。牛联民此刻入场,且有证人。
真话—从时间上却给侦察人员划了又一个问号:村口至学校的放映场,骑车、徒步,往返绕行二里地,半个小时也用不了。那么,从六点以后至八点的一个半小时里,牛联民又干了什么?
侦查员目光灼灼逼人:“你在看电影前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都干啥啦?又有谁可以给你作证?”
罩在烟雾中的牛联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答话也显得语无伦次:“我……没干啥。记不清……”
曙光在望的询问,就这样陷入了僵持。
伴随着冷飕飕的西北风,现场勘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老法医经三个多钟头的尸体检验认定:死者是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熟人用硬质棍棒的镜器所杀。
现场侦查人员花费了近两个钟头时间,用石膏提取了一个“菱形”花纹的完整脚迹和仅留三朵“梅花”的脚迹。
经查对,“菱形”花纹的脚迹系牛联民寻尸时留。那么,另一“梅花型”脚迹,又是谁所留呢?
从7日八时许至次日七时,二十三个钟头过了。此刻,梁副局长在郑费大队队部院内踱步,他对嫌疑犯牛联民的一串串问号:拦车后,二里路何能费时两个钟头?当夜发现尸体,为啥次日才报案?死者又是在毫无戒备情况下被熟人……种种迹象表明,牛联民很可能就是凶手,但是,怎样才能使罪犯伏法呢?他往踱几个来回后,一个“织深突破”的战斗方案,便成竹在胸了:搜查牛家,提取罪证。
侦查员们向牛母焦淑婵出示了《搜查证》后,一场搜查在牛家院的里里外外展开了。
步至小灶房,揭开墙角的破烂,露出一双洗后末干的塑料底布鞋:鞋底是呈“梅花型”花纹,鞋帮上还残留着隐隐可见的斑斑血痕。
拐进东厢里间,打开靠隔墙的衣柜,拿掉上层的衣物,搬过下层的被子,露出了一个塑料鞋刷盒。拧开一看,里面有块带日历的手表。经牛母辨认:确系小儿子生前要卖的那块走私表。
随后,侦查员又在柜下搜出一根尺把长的铁管。牛母看后也犯疑说:“他爸从太原捎回两根,原说是做铁耙梁用的,怎么剩下一根啦?”侦查员看这根末见血迹的铁管,脑子里闪过死者头部的道道钝器伤,旋即产生了疑问:丢失的另一根铁管,会不会就是凶器呢?
证据稳操,梁副局长断然指示:“‘突审’牛联民,要害是交出杀人凶器!”
一场别开生面的“突审”,在“闪电雷鸣”中开始了——
审讯员单刀直入地厉声讯问:“牛联民,你是要继续犯,还是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们已拿到了你犯罪的证据!”
“证据?”牛联民眼望公安人员腕露的手表,企图以烟压惊。可飞腾的团团烟雾,怎么也罩不住他那惊恐绝望的神色:“我愿意交……交,到运城或解州都行……”
审讯员心里一咯噔,问:“为什么?”
牛联民垂下头:“我怕你们绑我走,村里人笑话。”
“你既然愿意交代,那么我问你,你从兄弟腕上抹下的那块表,放在哪里?”
“我家衣柜被子下的鞋刷盒里。”
审讯员乘胜追击,突然打出了第二张牌:“你行凶时拿的什么家伙?”
“我爸从太原捎回的铁管。”
“作案后,你把它扔到什么地方了?”
“那天晚上,我就……把它扔到火车站路西……水壕里了。”
现场搜查人员在牛联民交代的地点,打捞出了凶器——一根尺把长,且粘有毛发、血迹的铁管。
从头天八时许现场勘察,到次日八时许起出凶器,历时二十四个钟头,足智多谋的侦查人员就依法逮捕了牛联民这个杀人犯。
那么牛联民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弟弟呢?
对牛犯的预审,较之侦破还要艰难。几天来,每每问及凶杀动机。他总是一口咬定:“因为在一次争吵中,兄弟挖苦我‘领着咱妈改嫁’,我从此怀但在心,就产生了杀害兄弟的念头。”
“一次口角,何能构成残杀胞弟的‘因果’关系?”思维敏捷的梁副局长,却抓住了“领着……改嫁”这一线索,引导预审人员停审进行社会调查,使预审很快结案,短期内就将罪犯交付法庭惩处了。
侦查员走访了为牛家保媒牵线的张氏,访问了悔痛中的焦淑婵大嫂,并提审了在押犯牛联民,遂解开了硝池滩奇案之谜:
牛联民,1960年三月出生。当他懂事步入学校,恰逢那个岁月。他上至二年级,仅学会一位数加法,减法不通,乘法更不屑提及。也导致他的人生哲学是以我为圆心,金钱为半径。为了“我”,他能以拳头敬人,还能以“上吊自杀”要挟对方。
成年之后,他不安心于艰苦的农村,做梦也向往着繁华的城市。他没得“后门”招工进城,却虔诚地等着“天赐良机”。
1979年秋天,47岁的焦淑婵与前夫离婚。熟人张氏怜她年纪轻,且两个孩子还未成家,登门提说了比焦氏年长十三岁的老光棍牛定国。年龄的过大悬殊,焦淑婵原本不同意。但知识贫乏而利欲熏心的大儿子联民,摸清了牛定国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工人,若是退休又未有直系亲属可以“顶替”时,却答母亲动了心。随母过去另改姓氏,不是可以作为牛家“后代”名正言顺地“顶替”接班,顺手拈来个吃“官粮”的铁饭碗吗?
联民主意拿定,不顾焦氏的竭力反对,硬领着母亲改嫁到了牛家。他一踏进牛家门,便迫不及待地向继父提出:“你退休我‘顶替’!”
牛定国满口应诺,并在婚后的当月,向厂里进上了申请“顶替”的报告。
万万没想到,牛联民好梦未醒,中途又杀出了他兄弟联仓这个程咬金。因为大儿子联民好吃懒做,性情暴躁,远不如小儿子联仓勤快和善,故焦氏背着老汉,遂产生了让小儿子“顶替”的偏念。
牛定国申请退休的报告,眼瞅着就要批复了。一天,在牛家院的东厢外间,焦氏对小儿子说:“联仓,过几天咱到太原去,看看让你接班的事弄成没有。”此话,大儿子在里间听得真真切切。
于是,牛联民经过苦思冥想后导演了一出血案。
1981年3月,牛联民被押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这个家庭的悲剧,震动了郑费大队。村里的男女老幼,争相传告、议论着这一奇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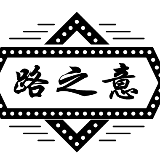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