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冀然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彦言,1989年生于江苏无锡。200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201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2016年毕业于IESA-法国巴黎高等艺术管理学院当代艺术硕士研究生。
扇子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最早出现于商代,“锦雉翠羽,遮尘蔽日帝王威严,多加仪度”,称之为“障扇”。当时的扇子并不是用来取凉,而是作为帝王出巡之时仪轨的一部分,同时也有遮风挡雨的实际功效。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对“扇”的释义为门扉,意为门扇。而也正是在东汉,扇子演化为丝、绢、绫罗之类织品而制,这便是团扇的滥觞。西汉班婕妤《怨歌行》诗云:“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澹泊云糕之咔噗剋Kē剋Kè,绢面设色,21.5x17 cm,2021年,陈彦言
唐宋时期,团扇无论是在功能上还是在审美上均得到极大发展。特别是在两宋,相较于折扇,团扇的形式与形状更贴合于一般情境下的作画状态,故而成为了宋画的重要媒介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女性虽然是宋代团扇绘画的重要收藏者与欣赏者,但其并不仅限于女性群体。发展到了明朝,书画折扇成为了文人身份的标志之一,其影响和传播力逐渐大于团扇,最终取代了团扇的地位,自明朝以降大为盛行。从此团扇渐渐囿于女性使用,成为了女性身份与符号的象征之一。
Twilly,绢面设色,21.5x17 cm,2021年,陈彦言
团扇作为艺术家陈彦言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媒介,也是形式。而她解构传统绘画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主题、语言与符号。诚然,主题与语言也隶属于符号体系,但在此,符号则为一般意义上的视觉符号。首先是主题,在作品《尖叫鸡》中,本应作为重点刻画对象的“尖叫鸡”反而被遮头去尾,前者是被奢侈品遮蔽,而后者则是被作为形式的团扇所截取。在画面剩余的母题中,例如花、叶与蝴蝶等,竟还是延续着传统花鸟画特征。所以,该作品不仅是对主题的“异化”,更是辅以不同的创作技法,使得主题中的矛盾与张力显得更为多维且具体。
尖叫鸡,绢面设色,21.5x17 cm,2021年,陈彦言
其次是语言,《WHY》与《露滴》构成了两种不同的以文字为载体的创作脉络。在《WHY》的画面中,折扇上的汉字整齐地跟随着扇面的起伏与褶皱,信封上的文字信息也暗喻着某种情结与格局。而大写的英文“WHY”却可以超脱画面中“物理”限制,并以“背景”反转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里,艺术家用语言反思一些刻板印象,继而扩展到对于体制与权力的思考。《露滴》取自于沈约《咏檐前竹》中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原意为对竹的审美观照,及其人格化的象征意向。而在画面中的母题,“露滴”变为了“滴露”,从诗意突然演化到了商业符号,进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反讽与幽默,这种幽默不啻于画面本身,更是体现在作品名称与绘画对象之间。
WHY,绢面设色,21.5x17 cm,2023年,陈彦言
露滴,绢面设色,21.5x17 cm,2022年,陈彦言
最后则是视觉符号,实际上在上述分析中也已涉及这个部分,体现在另一件作品《苹果》中,该层面的表达则更为凸显。该作品填补了苹果品牌图标上缺失的一角,而真实亦或是作为图像的苹果却被去皮切割。
苹果,绢面设色,21.5x17 cm,2020年,陈彦言
主题、语言与符号并不是独立存在,这三种方法在艺术家那里交汇、融合、叠加。加上前文中关于团扇与折扇的历史背景,使我们能够更为多元地理解陈彦言的创作脉络,以及她那独特的隐喻与幽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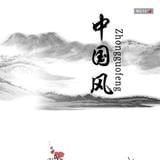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