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份,对前军统大员沈醉来说,是极重要的一个月。因为这一年,67岁的他终于能与妻女在香港相见。
1月6日,收到消息的香港媒体很快把这件事,登在了报纸头版。大批媒体,都等待着报道沈醉的一言一行。
这些媒体里,有正义的媒体,自然也少不了台湾方面控制的无良媒体。对于这些无良媒体来说,能挑到沈醉的哪怕一点点问题,都将会是“大功一件”,他们能凭此去反动派那邀功请赏。
对于这次相见,沈醉提前准备了很久,也早就跟中央领导们报备过,他自认已经完全能应付媒体的种种“狂轰滥炸”。
不过,在出发前,原国军大将杜聿明却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的,要保持晚节……”
沈醉与子女团聚为什么要去香港?此次,沈醉在香港会遇到些什么?
杜聿明又为什么要和沈醉交代这样的话,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交情?
这一切,要从功德林说起。
一、功德林里修功德
很久以前,在北京城的德胜门外有一座佛寺,名叫功德林。这里原是一座始建于金代的古刹,旧称“石佛禅林”。
“功德”二字,原本是佛家用语,专指念佛、诵经、布施等事。相传,唐代僧人玄奘去西天取经,在其经文上就有“功德”二字。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经工巡局大臣、大学士那桐奏准,在功德林创设“京师习艺所”,宗旨为“收容犯人,令习技艺,使之改过自新,藉收劳则思善之效。
从此,功德林开启了他的监狱生涯。
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那时的它,还叫“京师第二监狱”。后来的它又成了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监狱。与其他监狱不一样的是,这里的战犯很特殊:军官,仅限军队将级以上;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
这些战犯长期位居国民党高层,为蒋介石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对于战败并不服气,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改造的难度不小。
所以,新中国对他们的改造比较重视,在生活待遇上也要比其他地方高一些。
据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回忆:
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后,生活待遇提高了,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这等于过去中了举人后,选送太学来学习差不多。”引得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
不过,刚刚来到功德林时的沈醉可不是这样认为。

那是1957年的秋天,沈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转送到功德林监狱的战犯改造所。
刚到功德林的沈醉见到了很多老熟人,兴奋地聊天之余,忽然发现房间内放着一个床铺大的石膏模型,模型里面躺着一个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
沈醉的心情有些沉重,身为军统大特务的他曾经心狠手辣,见识过不少刑具。但这种“刑罚”,他还真是头一回见。
都说功德林是安置高级战犯的地方,但这高级战犯的待遇,让人实在有些心理不安。
心中忐忑的沈醉上前仔细一看,更是大吃一惊,戴眼镜的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杜聿明。而在几年前,沈醉曾听说犯了众怒的杜聿明已被下令枪决了,没想到竟在这里碰见了活人。
尽管在解放前,沈醉和杜聿明的工作没有太多交集,也谈不上什么友情。但是现在,看着躺在石膏模里的杜聿明,同病相怜的沈醉心里别是一番滋味。
沈醉悄悄问了几位从重庆过来的老熟人,战犯管理所是重庆的好,还是北京的好。大家都说北京的好,因为这里的管理干部政策水平高。
沈醉奇怪了,指着睡在石膏模型里的杜聿明问:“那这是什么意思?”
杜聿明听后哈哈大笑:“这是给我治脊椎病的呀!我患了脊椎结核后,脊椎变形了,管理所特意为我定制了这个石膏模,用来矫正我的脊椎。”
沈醉这才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和大家放松攀谈起来。
后来他才知道,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担任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时,毛泽东曾经发表过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但杜聿明一直负隅顽抗,直到部队溃败后,他开始化装逃跑。当时他冒充军需官,被俘后查问时,却答不出军需处长的名字,就被当作特殊人物看管起来。
一场淮海战役,杜聿明输掉了国民党几十万的精锐部队,自觉对不起蒋介石的信任。他一方面出于“愚忠”,另一方面又怕被人认出后不得好死,就决定来个痛快,自行了断。
于是,杜聿明乘看守人离开之际,拣起砖头往自己头上乱拍,直到昏死了过去。但解放军的军医很负责任,又把他救了回来。
此时的杜聿明状态很不好,多年的战场生涯给他带来了多重困扰。肺结核、肾坏死和胃溃疡等诸多疾病,长期折磨着他。
自觉自杀没戏的杜聿明,决定换种方式达到目的。他知道自己疾病的严重程度,但闭口不言,一心等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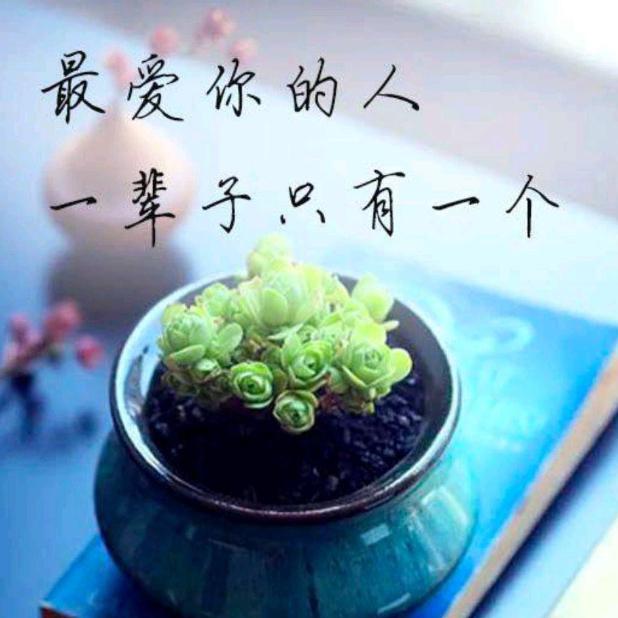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