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即使一个人受到伤害,
不得不发出怒吼,
他依然要庆幸自己能够做到这些。”
W.H.奥登被公认为T. S. 艾略特之后现代英语诗歌的又一座高峰。他的作品用“鹰的视角”关切社会历史,也用如歌的语调对人生和情感细腻抒写,在分裂与动荡的现代世界中寻求个体信仰的意义。
《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是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汉弗莱·卡彭特为奥登撰写的权威传记,书中披露的大量珍贵资料,包括奥登的信件、日记、笔记以及青年时代的未刊诗作,以800余页篇幅,让我们即使隔着遥远的时空,也能探索奥登隐秘而浩瀚的人生景观。
我们选取了本书译者、著名奥登研究者蔡海燕教授的译后记。从少年时起,“亲爱的A先生”便助她形塑独立的品格。如今迈入不惑之年,奥登的影响仍深刻地嵌入生活中,教会她如何与时间和解。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行动者和诗人的奥登对自己的生活都保持缄默,而在比以往更加让人迷茫的现在,这块面纱将要在你面前揭开……
蔡海燕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学翻译与实践,尤其在奥登研究和英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扎实成果。出版专著《“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20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史论》等;出版译著《奥登诗集》《某晚当我外出散步:奥登抒情诗选》《书虫小鼠》等。

译后记
与奥登相伴多年,而且是在人生的 20 至 40 岁期间,正是内在的触角小心翼翼但又毫不妥协地向外探寻的年纪。早已奉他为人生导师,就像他在人生暮年感恩曾拥有“一位可以倾诉衷肠的导师”,我在人生中途时常感喟奥登助我形塑了独立的品格。不敢遑论有多了解他,但汉弗莱·卡彭特的《奥登传》,一直以来都是我从事奥登诗歌翻译与研究的案头书。
起念翻译《奥登传》,要追溯到十年前。那时,我译出了前两章,明媚如春风的苏州女子易海舟翻译了半个章节,但我们踌躇满志的译事却没有就此生根发芽。《奥登诗选》尚未出版,编辑似乎并不期待《奥登传》面世,再则考虑到版权事宜,林林总总很是让人气馁。在过去的十年间,相继与几位出版社编辑聊过此书,最终都不了了之。我一度以为这本传记没有汉译的可能性了。时间辗转倾流至 2020 年,许是柳暗花明,有人相邀翻译《奥登传》,且来自不同的出版社。最终,上海明室拿到了版权,我与赵磊编辑的合作就此开启。
其间,我的研究生张玮琦、郑逸梵、杨瑶,还有我的师妹张茁,他们抽空帮忙校对了译稿,在此必须奉上由衷的谢意。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两战之间英国诗坛代际关系研究(1929——1939)”(项目编号:23NDJC028Z)的立项资助,也为我“清心志于一事”提供了有力支撑。大学“青椒”的忙碌应该是众所周知之事,我虽然年届“老椒”,但在很多统计数据里仍然忝列“青年”,有安身立命所需的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要完成。若想在学术事业上走得更远,翻译绝不是一个首选,尤其是这么厚重的一本书。不过,这是“亲爱的 A 先生”啊!

专注于钟爱之事,这其实正是奥登给予我的最重要的生活智慧。奥登年纪轻轻就立志要成为大诗人,由于始终铭记初心,他此后的人生选择和诗学取向都是朝着最初设定的诗歌理想前行:当现实的处境让他感觉到这个理想难以为继的时候,他就主动选择“他乡”作为新的创作环境;当创作的主题让他察觉到自己难以产生共鸣的时候,即便要在痛苦中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也要在痛定思痛之后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斯彭德作为“奥登的心腹、学家和注释员”,曾谈到他对晚年奥登的印象,认为他“一直保持着目标的一致性”:“他只专注于一个目标——写诗,而他所有的发展都在这个目标之内。当然,他的生活并非完全没有受到非文学事务的扰攘,但这些扰攘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其他人(包括我自己)都深陷于生活的各种事务中——工作、婚姻、孩子、战争等——与当初相比,我们大家都像是变了个人……奥登也在变化,但始终是同一个人。”用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梅里尔的话来说,奥登主动选择了一种文学性的生活。由于始终铭记自己的独特面孔,他每走一步,都不是白费,而是积累。他不仅仅积累经验,也积累智慧。关于这一点,黄灿然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奥登不仅提供了一条成功的途径,而且提供了一条哪怕不成功,也仍然可以活得自足、自在、自信,从而免受外部力量左右的途径。”小径多分岔,许多时候无关对错,却关乎初心。

在翻译的过程中,奥登的生命画卷随作者细腻的笔触缓缓铺展。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我这些年来在各类文献资料里接触过、推敲过的细节。童蒙时期的“那个堆满书籍的房间”,奠定了奥登广博的阅读兴趣和兼收并蓄的思想倾向。青少年时代的公学生活,让他在之后的岁月里始终对权威保持一份警惕,并且尽量避免自己沦为某种“权威”的代言人。成年之后渴望以“灵性之爱”抵御人世浮沉中的种种诱惑与磨难,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样把爱的信仰浇灌到日常生活里,不管对方(切斯特·卡尔曼)“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诋毁它、遗弃它、/对它抱以冷眼与怀疑”,他都“永不弃绝”。在体验了成长的欢愉、创作的激情、思想的交锋之后,衰老不期而至。雕塑家亨利·摩尔曾赞叹,奥登的脸是“深深的犁沟”“横贯田野的犁沟”。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说,这就好像“生命本身细致地勾绘了一种面部景观,借以展现‘内心无形的愠怒’”。诗人布罗茨基说,四面八方的皱纹纠缠在奥登的双眼之间,形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地图。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则不无抱怨地指出,为了看清楚奥登的模样,须得熨平他的脸。最生动的描述来自奥登本人——“我的脸看起来就像是一块被雨水打湿的婚礼蛋糕”。奥登的脸就像是他留给我们的一张上了锁的私人面孔,而这本《奥登传》无疑是一把适配的钥匙,借此可以敞开他盎然的诗意人生。

译稿完成之际,我已届不惑之年。所谓“不惑”,并非没有疑惑,而是不再与疑惑缠斗。有人说,一个读书人往往处于深刻与茫然之间,书山的背后也许恰恰是巨大的虚空。我虽尚未拥有“深刻”,但类似于浮士德走出书斋的感慨时常生发。而今,每每遭遇如是困惑,总是念及“亲爱的 A 先生”。他一直深信,“诚”与“真”的最高形式是践行,也就是说,阅读、思考和写作,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可感的生活里。
我手里握着的时间正在变薄,与其追赶时间,不如模仿时间。布罗茨基曾说,很多人之所以不喜欢晚年的奥登,是因为“他达到了声音的中立,嗓子的中立”,但恰恰是这种“中立”异常难能可贵——“它来自当他与时间汇流在一起。因为时间是中立的。生活的实体是中立的。”
Many happy returns of the day, Mr. A.
蔡海燕
2022 年 2 月 21 日初稿
2023 年 1 月 15 日定稿
[英] 汉弗莱·卡彭特
蔡海燕 译
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4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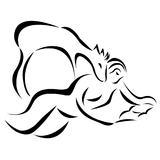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