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那间古朴凝重而又整洁敞亮的书房。由于1958年夏季过早降临,这里的许多奇花异草还未吮足春日的温馨,就向着晴朗朗的蓝天,竞相盛开五彩缤纷的花瓣。
尼·赫鲁晓夫是第二次来访中国,也是第一次走进这幢房屋。
一连两天会谈下来,双方都坦诚列举出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观点,主要是国际局势方面。中国政府已经表明,坚决支持苏联政府在联合国上提出的“和平倡议”。同时,要求美国从约旦和黎巴嫩撤军。可是,一涉及到国内事务,赫鲁晓夫发现,这位站在他面前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远远地将历史车轮推到了时间前面。
“什么?中国人要改装‘米格’飞机?”他愕然。
“什么?中国人拒绝成立苏中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
他一连三次追问翻译有没有听错。

……更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方才直言不讳地通知他:“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人要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核工业力量。”
这一点赫鲁晓夫始料不及。这不,趁着午间小憩,他与毛泽东在小庭院里展开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对话:
“中国人不具备搞原子弹的条件,还是先缓缓吧!”赫鲁晓夫说道。
毛泽东沉吟不语,半晌,点燃一支“大中华”。随着袅袅上升的烟团,他说:“中国的人口比苏联多,面积比苏联小一些,中国的和平要靠自己来保卫,以防人家拿核武器来讹诈我们。”
赫鲁晓夫诡诈地一笑,眯缝着眼睛应道:“如果必要,苏联政府随时准备履行自己的诺言。”
毛泽东很快挥了挥手,表示异议:“自由和独立是联在一起的,我们的方针是用核武器来保卫我们的和平。但我们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点,请苏联朋友放心。”说到最末一句,毛泽东特地拖长了一个尾音,以示加强语气。

一年前,中国政府曾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在发展原子弹方面给予一定援助。当时,作为总理的赫鲁晓夫慷慨答应,并有物质表示。但是,一旦中国人真的拉开原子弹试验序幕了,他却又出尔反尔,断然拒绝了。对此,毛泽东非常生气,他这样说:“中国确实还很贫穷,我以为,贫穷的历史总会过去的。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我们宁愿再勒紧一下裤带,把核武器搞上去。因为失去和平,就失去一切……”
午后的阳光悄然西斜,两国领导人会谈进入白热化。一个固执己见,一个据理力争。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将自己的财富有限地施舍一点给别人,甚至自己的敌人,都可以办到,可是,要把通向宝库的金钥匙交给别人,那就违背了他的个性。
于是,从这一天起,他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关注他身边的朋友了。
第二年夏天,他断然撒走了在中国从事核试验的全部专家,还带走了每一张演算过的草笺和卡片。

转眼五年过去了,1964年的一天。
“嚓”,索索抖动的手终于拨亮了一个老式打火机,火苗凑到了一堆架着干柴的枯草堆上。很快,枯草点燃了,霎时,通红的火舌直往上窜,将四周照得雪亮。原来这是间破陋的木棚,呼呼北风卷起的戈壁滩黄沙直往这里灌,使木棚内与外界一样寒冷。木棚原是供牧民放牧时小憩用的,此时的木棚已成为这远方来客最好的歇脚点了。
在中央篝火旁,坐着一位脸型瘦削、身板硬朗的将军,他的周围,都是些年轻的士兵。在这寒冷而又起风的戈壁之夜,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这位现代中国核工业奠基人之一,一支终年转战荒漠戈壁大军的卓越指挥者,已经是第四次西出嘉峪关,跋涉中国西部了。此行,他又一次肩负中央军委命令赶赴原子弹试验基地,视察工程进展情况。

半月前,据有关情报部门报告,在核试验基地附近,突然发现有美蒋侦察机踪迹。一听到敌情,将军一跃而起,风风火火离开北京,轻车简从,投入戈壁滩广袤的怀抱。他要亲自调查此事,辨别真,伪,以便党中央决断。几天连续的奔波,多兵种的协同侦查,并未发现这一带有何异常情况。原来,敌机“出现在核试验基地上空”,纯系有关人员在执勤时的幻觉而已。
直到此时,将军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所以在调查区域内吃过晚饭后,他就登上吉普车,连夜返回核试验基地指挥所。
那里,有一个特殊的会议在等着他。
核基地的夜,一顶顶帐篷在闪烁的灯火中忽隐忽现,威严而高耸的发射塔在夜幕下严阵以待,各种型号的卡车和推土机的灯光交织成一束束耀眼的光环,映照得沙漠如同白昼。大规模的施工项目已经竣工,所需的二万件设备、仪器安装已近尾声……
不太宽敞的会议室里挤满了各路兵马的指挥员和专家,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与将军一起从枪林弹雨中闯荡过来的,彼此十分熟悉。在他的面前,一溜整齐的报告,触目地放在桌上。这是他早就期望见到的报告……

当晚,一份电报从沙漠的核基地飞向中南海。
“……由党中央决定这一举世瞩目的爆炸时刻。”
一架伊尔型飞机在一片孤零零的低谷间盘旋,它忽高忽低、忽疾忽缓。稍顷,掉头向沙漠东部飞去。
将军惊呆了——
突然,太突然了。他默默地注视着眼前一组照片,照片上除了一片金色的沙漠外,正中焦点处有一堆未燃的枯柴堆、骡子走过的蹄痕以及显然是人工凿出来的深深水坑……
一切都是在6小时前发现的。
一切照片都表明,这里有人,有人曾出现在这是谁出现在原子弹爆炸的区域内?
按预定方案,爆炸区已经列为“禁区”,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曾有人在这里蛰居过,现在,怎么会突然冒出来呢?
照片无可置疑,是飞机从八百公尺高空拍摄的。

“马上调查!”将军果断拍板。一方面,他紧急下令,命空军基地集中现有侦察机,进行高空追踪。另一方面,抽调一批经验丰富的官兵组成小分队,开赴沙漠,实地搜索。
夜深了,面露倦容的将军却丝毫没有睡意,不知为什么,一团阴影总是弥漫在他的心头。试想,如果按期发射原子弹,万一爆炸区域里,有人怎么办?若是推迟发射,万一又是一次幻觉,怎么向党中央交待?这次核爆炸举世瞩目,自不多叙,况且,已经上报党中央,发射迫在眉睫……大意不得,草率不得啊!戎马一生的将军,深知“军令如山倒”,多少次转战大江南北,他从未临战前丧失过出征的勇气,也从未因犹豫不定而错失良机……
这一次,他沉默了。
中南海。
刚刚结束一次国务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正准备吃点夜宵。他习惯地坐在那张宽厚的大沙发上,拿起筷子——
一位秘书行色匆忙走到面前:“总理,加急电报。”
周恩来闻声接过,一看电报,就急忙站起,走到宽大的办公桌前。这是从一个当时仅为少数人知道的绝密电台,夜深人静时拍来的急电,一定是出现意外了。

当他仔细阅完电报,浓浓的双眉顿时紧锁在一起。接着,他思索着踱了几步,尔后,习惯地交叉双臂,嘱咐秘书说:“告诉主席,我要马上见他,这是一。第二,代我拍一封电报,告诉核基地同志,迅速查清人员下落,妥善处理。记住,在中国,不能出现第二个广岛……”
这一夜,他直到凌晨3时才走进卧室。
越野车又一次驶向广袤无垠的戈壁滩。这一回,车上不再是将军和他的随行人员,而是一群由将军精心挑选的小分队战士。他们中间有来自野战兵团的团指挥员;有常年在边远地区行医的白衣战士;以及神枪手、驯兽员、气象兵、向导和报务员。
这一行12人,除携带两支冲锋枪和一批手枪外,更多的是粮食袋和医药箱。在他们的上空,两架直升飞机随时为他们护航。不过,这是发现特殊情况时,才能动用的。否则,吓跑了那些“人”怎么办?
“将军想得可真仔细。”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老军医指指挂着的一串红辣椒,不无深情地说,“听说我爱吃这玩意儿,他特地让伙房为我准备的,酶,喷啧。这玩意儿,还驱寒呢……”
戈壁的白昼变幻无穷,刚才可能是酷日当头,燥热无比,眨眼间,就会乌云翻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在这充满艰难而漫长的路途上,小分队顽强地搜索向前。
“找,一定要找到。”这一个信念激励着中国士兵。可是,查遍了整个原子弹预定命中区域,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再找!”将军听完参谋人员报告后,又下一道金牌,“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幅射区城。”
好家伙!这个区城内不但天气、地势复杂多变,而且大部分地区从未有人涉足过,光是在这里坐车兜一圈,也要花几周时间。

“时间再长,也要弄个水落石出。”将军决心已定,奉陪到底。
直升飞机又一次轰鸣着升上蓝天。
小分队调整方向,向更宽阔的荒漠地带长驱直入。
这里有一片沙枣树,隐没在一个凹凹的斜坡下。
地图上,这是三号目标。
8天后傍晚,小分队在这里意外发现了一顶被遗忘的旧帐篷。帐篷周围,散乱地丢弃一些干柴和一柄破损的刀鞘。重大的发现,使得小分队战士欣喜若狂,他们几乎为此流下激动的热泪。
物证很快送到基地指挥所,同时附有一份分析报告。专家认为,从遗物推断,很可能是一伙早已在我国销声匿迹的“马匪”。
“马匪”……将军久久凝视着破残的刀鞘,一幕幕往事迭现在大脑屏幕上……
红军艰难地跋涉在北上抗日的道路上。马步芳、马鸿逵部队凭着熟悉的地形,优势的骑兵旅团向我冲击,逼得西路军四过草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屠夫的马刀,那高高的雪山,无际的草地,沉埋了多少英烈?1949年,我第一野战军挥师西进,在兰州城外合围“双马”大部,激战连月,多少将士壮烈捐躯;追歼顽匪,又有多少英雄血染疆场……

“马匪……”将军身边的随员恨恨地说:“找回来干什么?将军,我们跟他们打了多少次仗啊!还不趁此机会报销算了。”
将军没有答复,从军事家角度来说,他希望敌人越少越好。可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消灭敌人的肉体并不是最高目的。而征服敌人的意志才是行动的准则。
何况,“中国不能出现第二个广岛……”
几条敏捷的黑影迅速从一团沙枣树后面穿过,接近不远处的几撮烁烁闪闪的篝火。这是一个无风的夜晚,月朗星稀,不出百米,就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对方的身影。一个低低的声音在悄悄往“后传:“注意动静,带武器的上前。”
小分队拉开临战前的队形。渐渐地,他们的眼前出现了目标。
几个身容枯槁、衣衫褴褛的男人在火堆间晃来晃去。
一声孩子的啼哭,划破了夜的宁静。
有人倒水。其间,夹杂着一阵粗野的叫骂和马蹄远去的声音。
这是一支杂色的队伍,一、二百人,破羊皮袄一块块象秋天即将飘落的黄叶,挂在树干一样的身体上。女人的红棉袄脏得变黑,发出的腥臭飘得老远老远,几十匹老马在沙尘中凄厉地嘶鸣着。可以断定,这帮离异了人间的丑类,要不了多久,就会在地球上绝迹。
“是他们。”一阵涩苦的热草味扑鼻而来。
“我去看看。”一个小战士鱼跃而起。
“趴下。”年老的指挥员伸手将他按住,“天亮再说。”
夜空中升起奇特而又亲切的无线电波。
清晨。将军刚刚漱洗完毕,值班参谋兴奋地跑了进来:“首长,找到了,找到了……”
将军一听,抓住电文纸,急不可待读了起来:“好,果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告诉后勤部,派车去接他们。三天后,我要亲自为他们洗尘。”
三天后,一群在戈壁沙漠上游弋数年的“马匪”,坐着现代的交通工具,终于走出了茫茫沙漠。当他们驶进第一个供给站时,等待他们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年轻姑娘。
当然,其中一位老军人深邃的目光使他们过目不忘。

1964年10月17日15时,北京。新华社就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授权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这以前,对于已有的核大国,声明总归是声明,而事实常常走到它的对立面。现在,在这片充满和平阳光的土地上,却奇迹般地连在一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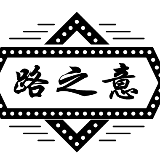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