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随老年大学诗词班师生一行到浙西辉埠小学采风。辉小徐校长带我们走进了书法展览室,从中让我感受到书法校园蔚然成风;然后走到学农基地上,可见师生们亲手种下的蔬菜、水稻丰收在望;再之后,又来到农耕文化展示馆参观,在犁、耙、耖等古老的农具旁我不禁停住了脚步,把我带入了久久的回忆之中。
四十多年前,我有好几年时间在老家种田,学习犁耙耖的用牛场景至今难以忘怀。
我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只得老老实实地回到老家,和父老乡亲一道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那时还是生产队集体化劳动,一年四季的犁耙耖使用自由“老把式”掌控。没想到后来,大田分到了一家一户,耕种收获就由各家各户自己承担了。
当年,我家也分得三四亩农田。老父亲由于年轻时就患严重的内风湿,常年负责生产队管水,犁耙耖技术没有学到手。受传统风俗的影响,比我早出生的三个姐姐也没有学会耕田技术。因而,自家责任田的犁田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一个男儿的头上。
说到耕田,小时候在家门口也见过叔叔伯伯们鞭牛扶犁,似乎优哉游哉地好玩。逢到星期天,我们一班小伙伴常常紧随其后。翻耕出来的稻田中,有鱼鳅黄鳝可捡拾。这不仅让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还能为家中的餐桌上添得一碗荤菜。可当自己要亲手使牛去耕田的时候,真的比做数学题还难。
记得是那年春天,我家一块几分阔的红花草田准备翻耕种水稻。父亲微笑地对我说,你也长大了,就试试学耕田吧。于是,从邻居租来耕牛和犁耙耖,跃跃欲试地来到田边。
我把牛轭套在牛的肩上,两边的铁锁链撸平勾住犁头。左手牵着牛索,还要执一牛鞭,右手专门用于扶犁。一会儿,把牛赶到水田中,“嗨”的一声,牛就往前面走去。不料,犁头却没有插入田块中,等于空走了一趟。

一圈下来,我又拽住了耕牛,然后把犁用力一插。也许插得太深,牛和犁竟然原地不动了。我高高挥起牛鞭,敲打在牛屁股上,仍然不见前行。我再一次用力一打,牛跳将起来,突然挣脱锁链向前奔去。这一奔,大事不好,牛直接跑到了前面的一块秧田里,把人家秧苗踩得稀巴烂。顿时,秧田人家暴跳如雷,骂得我只想往地下钻进去。好在老父亲就在不远处,连忙上去牵牛,给人家赔不是,而我气得就往家里跑。
回到家里,我偷偷地哭了起来,还把老父亲藏在衣柜里的香烟“偷”出来,一连抽了好几支。
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一再安慰我说,第一次学耕田没那么容易的,以后小心就是了,是男人就要有担当。我慢慢释怀之后,答应父亲,下午接着去耕田。
午间休息的时候,让牛吃了个饱。随后再来到田边时,父亲把多年记在心里诀窍教给我:要学会与耕牛交朋友,让牛听懂人的话,比如牛走偏了,要用方言“嗨”“哇”“辟”来喊牛调整方向;牵牛鼻子不能太用力,防止牛痛得发牛脾气;套牛轭之前,要用手轻轻抚摸牛的头和肩,让牛和人达到惺惺相惜的默契。果然,经过牛和我的配合,不到一个时辰,几分红花草田翻耕过来了。
接着就是用耙和耖平田。父亲说,要耙平一丘田,关键靠眼力。耙田主要是把泥块从高处往低处耙平。耖田的时候,泥不能带得太多,太多了牛走不动。泥带轻了,牛便轻松地乱跑。然而,待我具体操作起来,牛还是不怎么听使唤。整整一个下午,我勉强才学了犁耙耖的皮毛。没有耖平的田块地角,老父亲就用锄头去整平。
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我利用休息时间把困顿的经历记录下来,耕田日记常常出现在我的笔下。
一转眼,到了秋天,晚稻收割后,又要用到犁耙耖了。我渐渐懂得:上半年红花草田翻耕,犁是从田塍边开始的;下半年旱地耕作是从中间起犁的。那一年,我家的两块山排田——经过我和老牛合作,从田块的中线开了第一犁,将田分成两厢逐渐扩开。然后,按照自己的目测估算,一畦一畦地唤牛扶犁耕作,终于完成了由大田变成块地目标任务……
如今,放眼祖国的大江南北,耕田种稻几乎多是机械化操作,传统的犁耙耖耕作已经很难见到了。过去的历史对耶非耶?自有他人评说。但这难以磨灭的记忆,对我来说犹如雪泥鸿爪,涂鸦成篇聊寄一粒心声罢了。我坚信:勤劳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南丰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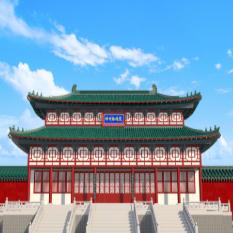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