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3世纪,欧亚北非大陆各文明间的跨文化交流进入空前繁荣的时代,尤其是大陆东西两端的文明,直接交往日渐增强,因此中国与印度最为先进的科技发明得以向大陆的西部传播。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发明的印度—阿拉伯数字、甘蔗制糖与棉花种植技术,就是在该时期传播至西欧最为重要的科技成果。

▲资料图。(图片来源中新网)
众所周知,中国造纸术早在唐代就已经传入阿拉伯地区。自12世纪中叶开始,中国造纸术又通过阿拉伯地区和拜占庭帝国传入西欧。中国的初级火药知识亦是在唐代伴随着炼丹术而传到阿拉伯帝国。中国最早有关火药配方的记载是宋代的《武经总要》(1044年),大约两百多年后,阿拉伯帝国和西欧地区才出现相关记载。罗杰·培根(约1214—1292年)和阿尔伯特·马格努斯(约1200—1280年)是西欧社会最早记录火药配方的学者。关于指南针,中国最早在《武经总要》《梦溪笔谈》(约1088年)中已有较详细记载,并在12世纪初应用于航海活动;一个多世纪后(约1190年),西欧热衷于航海科学的亚历山大·尼卡姆(1157—1217年),才在其《工具论》和《论事物的本性》中首次对之进行描述,将之用于航海则是13世纪初期的事情了。尽管西欧至14世纪末15世纪初才先后有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但前者直接源自中国的雕版印刷,后者则是间接受到中国印刷术的启示而进行的一次再发明,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3世纪中国与西欧之间物品与人员的密切交流。
印度人最早发明零,形成了0至1的数字体系。至9世纪,原先由“.”代表零的符号变为“0”,并在这一时期传入阿拉伯帝国。至12世纪,翻译家巴思的阿德拉德(约1080—1152年)、塞维利亚的约翰(活跃于1135—1153年)、克雷莫纳的杰拉德(约1114—1187年),将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密等介绍印度数字体系的著作译为拉丁文,印度数字由此传入西欧。印度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技术最早由萨珊波斯王朝皇帝克斯罗伊斯(在位时间为531—579年)引入西亚,阿拉伯人征服该地区后又将之传播到帝国统治的其他地区,西欧社会继而通过阿拉伯人将之引进。印度的棉花种植技术与棉花纺车亦经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欧。大约在10世纪,阿拉伯人将之引入地中海地区,后经西班牙和西西里传入西欧。自12世纪末起,由于西欧社会羊毛短缺,棉花种植受到重视,于是棉纺织业首先在意大利发展起来,后传入法国。
从中国和印度传入西欧的这些科学技术,对其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影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降,众多西方思想家曾就其价值作过深刻阐述。一些人文主义者将之作为“今胜于古”的进步主义观念的铁证。如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让·波丹(1530—1596年)在《史学易知法》中论道,我们时代的发明创造在诸多方面是古人所不能比拟的,“指南针的发明使我们能够进行环球航行……整个世界由此变为一家”,“单是印刷术的发明就足以与古人所有的发明相抗衡”。意大利数学家哲罗姆·坎丹(1501—1576年)认为“磁罗盘、火药和印刷术”具有世界性影响,并首次将之称为“三大发明”。最为经典的评价当属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他在《新工具》中论道:“我们应该注意发明的威力、效能与后果……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者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况:第一种在科学方面,第二种在战争方面,第三种在航海方面;并且无数的变化由此衍生而出,以至于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派,没有任何一个星辰,能够比这三种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威力与影响。”此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也都盛赞中国的这些发明对于西方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史研究的奠基者乔治·萨顿将印度—阿拉伯数字体系的西传视为“数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史学家希提将蔗糖视为“传入西方的第一种美食”。棉花种植虽然在中世纪西欧还不起眼,但它最终在近代成为一种引发西方工业革命的植物纤维。
这些从欧亚北非大陆东部发源的科技发明传播至西欧的印迹,已被流淌的岁月洗刷得斑斑驳驳,模糊不清,以至于许多近代西方学者将之视为欧洲自己的独创。直到现代,一些有识学者尤其是东方学家从卷帙浩繁的故纸堆中进行爬梳,拂去其蒙尘,才基本理清了其大致的传播路径。确实,上述发明创造都是中国和印度经过几个世纪乃至千年之久的探索才完成的。它们的西传并为西方人所用,亦历经波折和漫长的岁月。这些来自欧亚北非大陆东部地区的发明创造,何以在11至13世纪大量传入西欧呢?究其根本,离不开这一时期各文明间空前繁荣的交往与交流。
阿拉伯帝国与西欧国家的先后崛起及其宗教的急速传播,蒙古人大规模的东征西讨,以及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与繁荣,客观上推动了这一时期的跨文化交流。阿拉伯帝国在崛起过程中几乎将欧亚北非大陆各文明的优秀成果尽收其中,并在11至13世纪将之传播至落后的西欧社会。上述中国与印度的科技发明之西传无一不与阿拉伯密切相关,因此,阿拉伯成为该时期大陆东西两端文明交往和交流中不可替代的桥梁和媒介。而西欧人与蒙古人的碰面,使得东西两端的文明进入到比较频繁的直接交往与交流的时代,由此带来的则是欧亚北非大陆东部地区的发明创造大量涌入西欧。中国火药的西传即是显例。
一方面,西欧通过阿拉伯帝国这一中介知晓了中国的火药知识。新近的研究表明,罗杰·培根和阿尔伯特的火药知识共有一个阿拉伯渊源。许多学者认为,记载火药配方的《焚敌火攻术》很可能是西班牙犹太人依据阿拉伯人配方集编辑而成,后又将之译为拉丁文,培根和阿尔伯特都曾阅读过该书。培根于1267年写成的《大著作》《第三著作》等所记载的火药配方与《焚敌火攻术》中的火药配方十分相近。尤其是培根所提倡的用柳枝烧木炭的方法显然来自阿拉伯人的柳碳法,而阿拉伯人的这一方法则源自中国的柳碳法。同时,培根也与一些翻译家相熟,如活跃于13世纪中期的翻译家赫尔曼·阿勒曼努斯可能做过培根的老师。因此,他有机会通过这些翻译家了解阿拉伯人所知道的火药知识。
另一方面,西欧通过与蒙古人的直接交往而获得了相关的火药知识。1235—1241年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一直打到波兰和匈牙利,从而引发整个西欧社会的震惊和恐慌。蒙古人在战争中所使用的火药武器肯定也引起他们的关注。同时,蒙古西征打通了欧亚北非大陆的陆上通道,使得大批西欧的教俗使者、旅行家、商人往来于西方与蒙古乃至中原地带。这些东行者中就有一些培根相熟的方济各会友,如曾于1253至1255年间出使蒙古可汗宫廷,并写有《东行记》的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的威廉(1215—1270年)。培根所记载的“纸炮”是中国儿童已经玩了一百多年的玩具,很有可能是与培根相熟的东游者带回来送给他的。可见,早在培根记载火药配方之前的13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就已经通过与这些东行者的交往而了解一些火药知识。
总之,在11—13世纪,欧亚北非大陆的跨文化交流使得相对发达地区的科技知识不断向落后地区传播,加上翻译运动的影响,西欧社会于13世纪后期在科学技术方面逐步追赶上其他文明的发展步伐,笔者认为,欧亚北非大陆由此进入第二个辉煌的“轴心时代”。如果说第一个“轴心时代”主要有赖诸文明的独立发明创造的话,那么第二个“轴心时代”则更多有赖于诸文明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完)(原标题:11-13世纪中国与印度科技知识向西欧社会的传播)
作者/徐善伟,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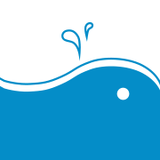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