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笔 许述
【按语】前段时间,本工作室在搜集整理“近10年美国等国对解放军弱点的研究”主题资料(31份,点击标题可回看)时,发现绝大多数材料都会提到同样的一点——解放军几十年不打仗了,缺乏实战经验。
缺乏实战经验的确是个问题,但凡事也需要辩证地看。兰德公司曾专门撰文“解放军缺乏实战经验还能不能打胜仗”,该文作者曾在美军印太总部“中国战略研究组”工作过5年,其结论是“也可以”。从某个角度看,没有所谓的经验桎梏大脑,反而会更具创造性;反之,经验太多太成功,有时未必是好事。经验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成功或失败,关键是怎么用,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下文就是美军经验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摘自笔者新著《这也是美军:美军的50个弱点》,原文题为“美军机械照搬经验,铸成史上最大败笔”。

“经验”,是褒义词、贬义词,还是中性词?
至少在创新面前,经验是个贬义词。有太多例子证明经验主义害死人,马其诺防线是人所共知的经典案例。不过,人不可能彻底告别经验,相反,如果灵活应用经验,会少走不少弯路。经验之所以被贴上陈旧保守的标签,往往不是经验本身的错,而是经验运用上出了问题,导致经验变成教训。
在很多人印象里,美军是创新的化身,全身贴满了革新的标签,绝不照搬经验——不要说别人的经验,连自己的经验都不用。
其实,这是个误会。即使浑身充满创新细胞的美军,也并非完全无视经验,甚至在西点军校成立了“经验总结中心”。当然了,美军也曾因为机械照搬经验,铸成史上最大败笔——越南战争。
经验主义在越南战争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把“数字化管理”从公司企业和官僚机构机械移植到战场。说到这里,有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1939年,麦克纳马拉在哈佛大学读完MBA,次年留校执教,成为哈佛商学院最年轻的助理教授,其授课内容正是“量化分析在管理上的运用”。1946年二战结束后,29岁的麦氏(上校)和几个战友“集体转业”[1]到福特汽车公司。当时,该公司业绩正在下滑,但麦克纳马拉视危机为挑战,利用数字化管理等办法,迅速扭亏为盈。1960年,他因功升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president)。注意,该职位之前一直由福特家族的人把持,从不对“外人”开放。14年时间就从一个“军转干部”混到“公司总裁”,这是麦氏人生的高光时刻,他非常感谢数字化管理给自己带来的成功。
1961年初,麦克纳马拉“商而优则仕”,换了个更高大上的地方当老板——美国国防部,成为五角大楼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部长。当时,总统肯尼迪给了他两个选项——财政部长或国防部长。财政部长似乎更适合麦氏,但他挑了后者。可见,麦氏喜欢挑战陌生领域,在他看来,在财政部获得成功不算成功,在国防部获得成功才是成功。
就像麦氏当初去福特汽车公司时得知该公司业绩正不断下滑,他到国防部前也很清楚五角大楼的头儿不好当。国防部成立14年来(1947-1961年),部长走马灯似地换了7个(平均两年一换),甚至首任防长福雷斯特尔因压力过大住进精神病院而自杀身亡。
管理美国国防部比管理福特汽车公司难度大多了,麦克纳马拉Hold得住吗?
麦氏Hold住了。他一干就是7年,总统从肯尼迪换成了约翰逊,他这个国防部长还在,成为两朝元老。更重要的是,麦氏彻底改变了国防部长在在军队和老百姓眼中软弱无能的刻板印象。他把福特汽车公司的数字化管理经验带过来,对国防部进行了一场管理革命,使这个重复建设严重、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面貌焕然一新,威震全军,把军队整治得服服帖帖。

在商界和军界都大获全胜,这充分证明了麦氏的领导能力和数字化管理的威力,他一时间风头无两。然而,当麦氏把屡试不爽的“数字化管理经验”搬到越南战场,却屡屡碰壁。
先来看麦克纳马拉是怎样对越南战场进行“数字化管理”。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管理办法是“数尸体”(body count)。看起来这很科学:敌人被打死一个少一个,北越有生力量会越来越少,一步步走向失败。执行起来也很简单,不就是数数嘛。麦克纳马拉信心满怀:“各种定量分析的结果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2]
可惜,结果证明万灵丹“数字化管理”在越南战场上不灵了。
第一,打死敌军的数量不好衡量。一般来说,战场伤亡数据以赢家的统计为准比较靠谱,因为胜者清扫战场。但在越南情况不同,很少有正规战,基本是游击战。在游击战中,北越人中弹后不管是伤是死,战友会尽量以最快速度带走,美军追过去常常只能看到血迹或丢弃的武器。那么,这个算不算打死了呢,算几个呢?
第二,部队倾向于谎报战果以邀功请赏。衡量企业某部长能力的标准是业绩,衡量军官的标准是战绩,都需要拿出具体数据作为升迁的依据。越战亲历者、后来担任参联会主席的鲍威尔回忆道:“数尸体由此成了死亡人数统计竞赛,连与连比,营与营比,旅与旅比。好的指挥官报上来的尸体数量高,他们因之得以晋升。假如你的竞争对手夸大尸体数字,你能不夸大吗?”[3]
美军在越南战场搞数字化管理,表面上很现代,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因为这招老早就被古代中国的军队用过了。想必大伙儿从历史课本里都知道商鞅变法中著名的“军功爵制”,斩敌一首升爵一级,“首级”一词就是这么来的。到后来,秦军这招被发扬光大,而且计量办法得到改进——敌军人头不便携带,那就割敌人的鼻子或耳朵。那些没割掉敌军头颅(鼻子或耳朵)的官兵怎么办呢?easy,大刀向老百姓的头上砍去……
美军也许不了解古代中国军队的招儿,但在越南战场无师自通,也打起了普通老百姓的主意,理由还杠杠滴——越军很多时候不穿军装。“美莱村大屠杀”被归因于美军压力大有些片面了,美国大兵滥杀无辜,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杀人领功。这不是笔者抹黑美军,而是越战亲历者鲍威尔自己承认的:“类似美莱那种丑恶的事件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在于美军热衷于另一种虚构的神话,即越南战争中创造出来的令人厌恶的衡量标准——‘数尸体’。”[4]
麦克纳马拉在公司企业和官僚机构进行数字化管理很成功,但把这一经验搬到战场却败了,原因在于他至少忽视了两个问题。
第一,美军在越南进行数字化管理不具“可控性”。麦氏之前取得两次巨大成功有一个前提——“可控性”,无论是福特汽车公司还是国防部,都是自家人的机构,管理起来既方便又容易。但在越南,要对敌军伤亡数据进行准确的数字化管理,没有全面客观的情报支持几乎不可能。退一步说,就算美军关于打死越军的统计数据准确,又如何知晓北越补充了多少兵力?
第二,战场上不是所有要素都适用于数字化管理。不可否认,数字化是个很好的科学工具,但也有边界,并非所有领域都能通吃。价值观、传统、文化、意志、民心、士气,这类因素用数字如何统计?鲍威尔有个评价一针见血:“麦克纳马拉的计算尺精英们算出的精确指数不过是在衡量不可衡量的东西而已。”[5]
麦克纳马拉上任之初,民主党曾讥讽他是“一台长着腿的IBM电脑”。这本是反对党恶意攻击,不必在意,只要麦氏干得好,类似攻击自会随风而去。可是,麦氏在越南失败了,民主党这个评价就显得很有先见之明,令人印象深刻。

越南战争,美军死亡5.8万人,北越死亡110万人。[6]1条命换对方近20条命,看起来美军的代价很值当。北越近20个人才换美军1个人,居然还能坚持,美国人无法理解。麦克纳马拉看到的数据比例应该更高,作为一个商人,他非常注重“性价比”,如果实现目标付出的代价太大,可能会选择放弃。因此,麦氏很难理解北越人为什么死扛,又凭什么能死扛。从军事维度看,美军在越南是成功的,但从政治和战略维度看,美军是失败的。战争结束后,美国痛苦地发现:只要对手不承认失败并坚持打下去,美军就不能说成功。
麦克纳马拉黯然离开国防部后,并未就此退出江湖,而是在新的山头再任掌门——在世界银行担任总裁长达13年(1968-1981年),也许这才是适合他的舞台。不过,时间并未驱散麦氏心中的越战阴影,他于1995年出版了一本长达400多页的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总结出11条教训[7]。

大概是1991年海湾战争治好了越战的伤痛,加上美军在之后的多次军事行动中屡战屡胜,便把越战的11条教训抛诸脑后,轻率发动了师出无名的伊拉克战争,随后长期陷入泥潭……看到美国重蹈越南覆辙,麦克纳马拉忍不住出来公开表示:“我们(在伊拉克)所做的一切都错了,无论是从道德、政治还是经济上。”[8]
机械照搬数字化管理模式只是美军在越南犯下的经验主义错误之一,甚至不是最严重的错误。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军把对苏作战的办法机械照搬到越南。知情人表示:“我们以为去越南打仗,好像在中欧平原与苏联人作战一样。我们接受的是这样的训练,武器装备也是这样配置的。但在越南,我们无法使用这样的方式取胜,还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耐心。”[9]无独有偶,驻越南的美军陆军情报官科恩也披露:“军官队伍受到的教训是针对苏联人的,他们预想的是大规模坦克战和机械化步兵战——力量与力量之战。但在越南,每个军官都梦想着有一天那些乞丐一样的越南人会跑到大路上来开枪,但他们从不这样做。”[10]
1991年海湾战争是个漂亮的翻身仗,使美军走出了越战阴影,憋屈了20多年总算扬眉吐气。所谓“一俊遮百丑”,这场胜仗其实遮蔽了美军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错误的经验主义。战前,美军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预测伤亡,最高数据是1.8万人,并准备了相应数量的装尸袋。美方是如何得出这个数字的呢?他们用了一个公式,而这个公式是基于美国在欧洲打垮苏军的军事演习。[11]
到了伊拉克战争,情况变好了吗?
很遗憾,没有。
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要求中央司令部拿出作战方案,发现报上来的计划不过是把当年海湾战争的计划简单改了一下而已。拉氏十分不满,要求推倒重来:“这是一项陈腐、缓慢而且过时的计划……海湾战争来去匆匆,已经过去了十年,而作战计划似乎停留在了那个时间。”[12]作为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只好不断调整作战计划,“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简报”[13]。由此可见,军方摆脱海湾战争成功经验的桎梏有多难。
谁都不想被贴上经验主义的标签,经验(尤其是成功的经验)却往往不离不弃,顽固植根于脑子里,或多或少影响判断和决策,即使美军也是如此。
《这也是美军:美军的50个弱点》
连续两周蝉联京东世界军事图书热卖榜top1

参考资料:
[1] 麦克纳马拉于1943年参军,主要在数字化管理办公室工作,利用自己的数字化知识为部队提供服务。
[2] Karnow, Stanley (1983).Vietnam A History. Viking,p254
[3](美)科林•鲍威尔著、王振西主译:《我的美国之路》,北京:昆仑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4](美)科林•鲍威尔著、王振西主译:《我的美国之路》,北京:昆仑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5](美)科林•鲍威尔著、王振西主译:《我的美国之路》,北京:昆仑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6] 两个阵亡数据都是双方各自统计,估计越方的实际阵亡数字超过公布的110万人。
[7](美)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电子版),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93-194页。
11条教训:(1)正如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我们对敌人(在这里指北越和在中国)的地缘政治意图进行了错误的估计,夸大了他们的行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2)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模式来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领袖,认为他们渴望并决心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3)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里是指北越),它们可以鼓动人民为它们的信仰和价值去战斗,并付出牺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在重复着类似的错误;(4)我们对敌友分析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在我们与苏联不断发生的对抗中,也经常出现这种失误——如在柏林、古巴、中东等问题上——我们好像从未听到过汤米·汤普森、奇普·波伦和乔治·F·凯南的告诫,这些高级外交人员曾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会有何种反应。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建议在形成我们的判断和决策时毫无作用。高级官员在做出关于越南事务的决策时,也缺乏精通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来提供咨询;(5)正如我们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的。同样,我们也没能够把我们的军事策略与赢得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灵与思想的任务结合起来;(6)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对于美国是否应当大规模卷入东南亚的军事冲突,没有能与国会和美国人民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争论;(7)当行动已付诸实施,意外事件迫使我们背离既定方向时,没能一直征得公众的支持。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充分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在让公众理解我们面对的复杂局面以及他们会如何对必要的改变做出积极的反应上,我们缺乏应有的准备。而此时,我们的国家正面对一片未知的领域和一个远在天边的陌生国度。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其军事的强大威力,而是其民众的同心协力,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此点;(8)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9)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对我们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外——应该在得到国际社会全力支持(而非只是做个姿态)的情况下,与多国部队共同进行;(10)我们没有认识到,国际事务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对于将解决问题作为其生活的信仰与实践的人们来讲,这的确是很难接受的现实。然而有时,我们也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并不整洁的世界里;(11)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最基本的错误是,我们没能组织一个高层的行政领导班子,有效地处理一系列异常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为此,我们承受了极大的风险,付出了生命损失和沉重的代价,长期处于动用军队的紧张压力下。假如这类军事和政治问题是总统和其顾问们面临的唯一问题,那么,这种组织上的缺陷将会使我们付出高昂代价。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我们还面对一系列其他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因此,我们没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讨论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我们的目标,用其他方式处理它的风险和代价,以及在失败已很明显时改变战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我们的行政委员会所做的那样。
[8] 李晔:《美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越战主将到反战演》,《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2月12日。
[9](美)托马斯•E•里克斯著、吴亦俊等译:《大国与将军:从马歇尔到彼得雷乌斯,美国军事领袖是怎样炼成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9页。
[10](美)托马斯•E•里克斯著、吴亦俊等译:《大国与将军:从马歇尔到彼得雷乌斯,美国军事领袖是怎样炼成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6页。
[11](美)科林•鲍威尔著、王振西主译:《我的美国之路》,北京:昆仑出版社,1996年,第657页。
[12](美)拉姆斯菲尔德著、魏骍译:《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306页。
[13](美)拉姆斯菲尔德著、魏骍译:《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
“许述工作室”创始人简介
许述,军事学博士,出版过《这才是美军》《兵道》《这也是美军:美军的50个弱点》,现创办工作室,聚焦研究美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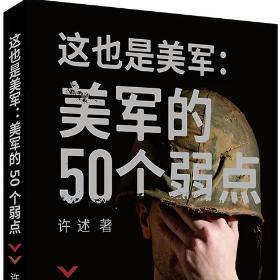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