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耕地论争回顾
原《襄樊晚报》编者按:迫不得已,旧事重提。南阳市长最近发表谈话,提到南阳昔日繁华和想象中襄阳的落后,推理出诸葛亮不可能躬耕于襄阳。
南阳的一位文化人则说,不论从任何角度讲,南阳不能没有诸葛亮。
本市学者获悉后,认为从南阳市长的谈话和文化人的发言来看,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确实很有必要,用学术的态度讨论学术问题更是必要。
本报特邀请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市诸葛亮研究会副会长、襄樊学院教授余鹏飞撰文,全面介绍躬耕地论争的来龙去脉。
一、三次争论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望的问题,在隋唐以前是不存在有争论的。只是在元代以后才出现襄阳与南阳两地的争论,虽说争论已有几百年了,但不是每年都争,只是在某个时候因某一件事引起而发生争论,所以它具有阶段性。大体上说来,从元明清时期算起至今共有三次:
东汉末年,北方军阀混战频繁,人们为免遭战乱的蹂躏,纷纷向南迁徙。诸葛亮约在十三四岁时,便随同叔父诸葛玄依“旧友”荆州牧刘表辗转来到荆州首府襄阳。诸葛玄去世后,时年十七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诸葛均到离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寓居。他在这里一边躬耕陇亩,一边读书拜师交友。十年后,即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寻求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随即回答刘备所提出的问题。不久便离开了隆中,辅佐刘备、刘禅治理天下。
从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后,直到元代中期这一千余年间,史籍上都明确记载诸葛亮是寓居在南阳郡邓县隆中,从未出现过一条不同的记载。元代元武帝至大二年(1309),南阳府开始修建武侯祠和诸葛书院。明嘉靖七年(1528)《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为乞赐祀典题额》中,御赐卧龙岗“乃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之地也。”该《题额》中还依据“询之父老,考之郡志”,断定卧龙岗“亦隆中也”。此后修纂的《南阳府志》、《南阳县志》便按《题额》的说法称卧龙岗为诸葛亮躬耕地。但明万历年间(1573—1619)《重修卧龙岗草庐碑》文却曰:“(诸葛)草庐在襄阳者为真,在南阳者为赝哉!”“玄德屯军新野三顾孔明者,实此隆中,非今所称在南阳西南七里者,故曰膺也。”明纂修的《襄阳府志》、《襄阳县志》根据史籍记载,无一例外地明确载明诸葛亮寓居躬耕于南阳邓县的隆中。这样,便引起了南阳和襄阳两地文人学士的争论。由此可知,这第一次的争论是由于明朝时期修纂地方志所引发的。因为当时在纂修地方志时,为了抬高本府县的地位,增加地方光彩,编纂者往往硬把一些本来不属该地的名人拉过来。近年来,其它地方相继出现的所谓扁鹊籍贯之争、董允故居之争、西施故里之争以及擒庞涓地点之争、赤壁之战地址之争等,可以说,都是明清时期编修地方志所惹的祸。
所以人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对地方志的采用都是持特别谨慎的态度,一般情况下甚至不采用地方志的材料作为重要依据。
第二次争论是1988年因发行《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在何地举行首发式而引发的。
原国家邮电部发行的《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中包括一枚“三顾茅庐”邮票和一枚小型张《隆中对》。按惯例,举行反映历史事件的邮票的首发式就在历史事件发生地举行。因此,在襄阳还是在南阳举行首发式,成为两地关注的焦点。此前1987年8月南阳水仲贤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南阳卧龙岗就是隆中。次年四月襄樊丁宝斋在《集邮》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同年十月,南阳张晓刚在同一杂志上发文,针锋相对地指出“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同时,两地有关部门向邮电部呈报,申请在当地举行首发式,南阳方面还要求将小型张《隆中对》改为《草庐对》。至此,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趋于白热化。
1989年12月至1990年4月襄樊方面先后分别在武汉、北京、上海、成都四地邀请全国一些著名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如唐长孺、何兹全、谭其骧、缪钺、朱大渭、高敏、朱绍侯等九十四位学者举行诸葛亮躬耕地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根据史籍记载,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邓县隆中,而不是在南阳宛县卧龙岗。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名为《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由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
南阳方面也有大的动作。他们于1991年4月邀请了九十多位专家学者在郑州举行了诸葛亮学术讨论会。根据出版的论文集《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中洛崤的《诸葛亮学术讨论会综述》介绍,关于躬耕地问题与会者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是邓县隆中说,共有五条主证,两条旁证,两条理证;二是宛县卧龙岗说,共有两条主证,四条旁证,两条理证;三是躬耕于汉水以北邓州之南说;四是诸葛亮游学寓居襄阳、躬耕受三顾于南阳宛县说。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对诸葛亮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不宜急于下结论,而应继续深入进行探讨和充分争论,以取得共识。
第三次争论是2003年7月份开始的。缘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材初中第六册《出师表》一文对“南阳”一词的注释错误而引起的。2000年所编教材中将“南阳”注释为“郡名,在今湖北襄阳一带。”南阳方面得知后,市政府有关方面紧急商议决定“予以还击”。有的市民组织万人签名活动。南阳方面认为,出版社这样做是给长期争论的诸葛亮躬耕地下结论。南阳学术界还要求将教材中选用的《隆中对》更名为《草庐对》。
8月28日,南阳市市长何东成就教材问题接受《南阳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从张衡《南都赋》对汉代南阳的描述,可以使我们看到当时南阳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程度,所以诸葛亮才会选择南阳这个地方来躬耕求志。志存高远的诸葛亮不可能到一个当时比较偏辟,像襄阳隆中这个比较落后,信息不灵的地方去躬耕求志。”又说:“大家可以到襄阳隆中去看一看,明代以前的文物基本没有,而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碑刻等文物则大量是明代以前的(看来何市长对汉魏时期历史还不了解,对南阳武侯祠和隆中诸葛亮故居所藏文物现状更是不了解—引者注)所以谁长谁短,谁深谁浅,谁厚谁薄,大家可以比较。”他认为教科书的解释“是歪曲了事实,伤害了南阳一千万人民的感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应该受到谴责。”
近一段时期内,《南阳日报》、《南阳晚报》发表了大量关于诸葛亮躬耕于今南阳的文章。河南《大河报》于8月13日发表一篇题为《千年未决悬案,忽然又生波澜》的文章,介绍南阳方面活动的情况。襄樊学术界得悉这一情况后也组织了座谈。8月29日的《襄樊晚报》以《又把定论当悬案》为题介绍了襄樊学者们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教材原来对“南阳”一词的注释是不妥的、错误的,应予以纠正。但说两地的争论有千年之久,是不准确的。至于用《隆中对》篇名问题,大家认为两个篇名都可以,但用《隆中对》比用《草庐对》更为科学和准确,而且从康熙九年(1670)进士、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在编辑《榕村雨露》文集中率先使用《隆中对》这一篇名后,内阁学士、进士蔡世远(1682—1733)在编辑《古文雅正》中、进士卞永誉在《书画汇考》中、雷(1697—1760)在《读书偶然》文集中都将这段对话标以《隆中对》的篇名。只有张澍(1776—1847)一人在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中标以《草庐对》篇名。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和《隆中对》篇名问题的争论,目前还在进行之中,南阳方面正筹备举办“诸葛亮与南阳”学术讨论会,以掀起争论的新高潮。
二、两地出现争论的缘由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北伐前夕,在成都向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疏(后人称《出师表》)。在奏疏中他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思是说愚臣本是一名平民百姓,亲自在南阳耕种土地。这其中的“南阳”,是指哪里呢?两汉时人们习惯用郡望来指明自己的籍贯或出生地,无疑这“南阳”是指南阳郡,但具体是南阳郡内的哪个地方呢?只有从其它的文献记载中去寻找证据。从西晋王隐的《蜀记》、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南朝刘宋时盛弘之的《荆州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记载来看,诸葛亮是寓居躬耕于南阳郡邓县的隆中。可以说,元代以前人们对这一结论是毫无疑义的,也从未发生过争论。可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元程矩夫《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记载,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等人依据从隋以来将宛县改称南阳县的情况,加之当时置南阳府于南阳县,于是就认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就是指当时的南阳县,随即到南阳县选择县城西南七里的山岗作为诸葛亮躬耕的地点,并取名“卧龙岗”,并于至大二年(1309)在岗上修建武侯祠和诸葛书院。从此就出现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说。《大元一统志》卷3河南江北行省“古迹”中说:“卧龙岗在南阳县境,诸葛孔明躬耕之地。”同时《大元一统志》又记载襄阳西北的隆中是诸葛亮的隐居地,还说隆中有刘备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中的“三顾门”。可见该志保存了诸葛亮躬耕地的两种不同说法。由此可知,争论是从元代人们对“南阳”这一地域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开始的。
明代官修的《大明一统志》卷30“南阳府·南阳县·卧龙岗”条说,岗上有草庐,“即孔明躬耕处。”“名宦流寓”条又说:“诸葛亮本琅讶人,汉末避乱,寓居南阳之西岗,躬耕陇亩。”而同书卷60“襄阳府·襄阳县·古迹”条说:“诸葛亮宅在府城西二十里隆中山下,蜀汉诸葛亮所居。”“隆中山”条说:“山下有隆中书院,汉诸葛尝隐于此。”“名宦流寓”条称:“诸葛亮,琅讶人,寓居南阳,往来隆中。”由此可知,明代官修的—统志将两种不同说法并存,并且用诸葛亮躬耕南阳卧龙岗,寓居襄阳隆中往来二地来解释两说并存的矛盾。因为史书上没有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宛县的记载。于是,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究竟在何处,便成了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到清代,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中对诸葛亮躬耕地的记载就有所不同。据该书卷347“襄阳府·古迹”条说:“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隆中山东。刘备三顾亮于草庐之中,即此宅也。”而同书卷210“南阳府·古迹”条说:“在南阳西南七里卧龙岗,相传诸葛草庐在焉。”这里用“相传”二字,比明代《大明一统志》的记载较为客观、公正。
在清代私人所撰述的作品中,还有人说襄阳、南阳都是后人附会之说,如张澍在《诸葛忠武侯文集》卷五“遗迹”篇中作按说:“隆中在襄阳县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又以卧龙岗在南阳府,亦失之。”
由上叙述可知,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严格地说是从元代中期开始的。
三、为什么说躬耕于邓县隆中
研究诸葛亮躬耕地这一历史问题,应主要以史籍记载为主,此外还要结合当时两地的政治形势,诸葛亮的人际关系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论证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区域,应以本人的叙述或与该人物同时代人的记述,或与该时代最接近的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这是历史考证最基本的方法。如果用距该历史人物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的材料来论证,那会使论证走上歧路,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隆中,其依据有五:
首先,从《隆中对》本身内容来看:诸葛亮在向刘备提出统—天下的方略时指出:在占领荆州、益州之后,利用天下变化形势,分别从两个方向率兵北伐,攻灭曹魏。这两路中,一路便是派一名将军率领荆州的军队北上,“以向宛、洛”,这一“向”字说明两点:一是宛、洛当时是曹魏敌占区,所以要去攻打;二是说明诸葛亮与刘备对答是在宛的南边邓县隆中,因宛、洛远在北方,所以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方才符合地理方位。如果诸葛亮是在宛城当面回答刘备的问题,那诸葛亮不会要刘备再来打宛城了,就可直接要刘备率兵由宛北上去攻打洛阳就是了。所以《隆中对》中的“向”字是解决诸葛亮躬耕地的最好依据。
再以与诸葛亮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鱼豢撰写的《魏略》记载来说,诸葛亮的好友孟公威因思念他的家乡汝南,“欲北归”,诸葛亮极力劝阻他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从地理方位看,汝南(今河南平舆县)在宛的正东,在襄阳的东北。如从宛去汝南,应是“东归”,而不是“北归”。只有从襄阳出发去汝南才是“北归”。该书又记载说:“刘备屯于樊城……亮乃北行见备。”(当然这条史料是说,诸葛亮自荐见备,不是刘备三顾茅庐,这不可取。但只就诸葛亮去北见刘备的方位来说是可用的。)“北行”,是由南至北才为北行,如果是由宛至樊城,那就是“南行”了。这两则材料说明,生活在曹魏中叶,时任郎中的鱼豢也确信诸葛亮是居往在汉水之南的邓县隆中。
其次,从离三国最近的两晋来说,也有史籍记载诸葛亮的寓居地。据东晋初王隐撰写的《蜀记》记载,西晋惠帝永兴年间(304-306)镇南将军刘弘在镇压张昌起义后,由宛移驻襄阳,他专门到了隆中,瞻仰诸葛亮故居,“立碣表闾”,并命镇南府参军李兴撰写《诸葛亮故宅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到隆中诸葛亮故居。刘弘去瞻仰时,只距诸葛亮去世时70年,而且《蜀记》所依据的材料是王隐的父亲王铨所搜集的。王铨为魏晋时人,略晚于诸葛亮,他搜集整理资料时,离诸葛亮躬耕隆中只不过65年,离诸葛亮去世时只有38年,所以他留给王隐的《蜀记》材料或部分稿本,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至于《宅铭》中说:“天子命我于沔之阳”,是指朝廷命刘弘到沔水北边的宛、穰一带去平息张昌起义,而不是指隆中在沔水北边。
东晋时襄阳人习凿齿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更明确指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
此外,南朝刘宋时期盛弘之的《荆州记》,萧梁时期鲍至的《南雍州记》,南北朝时期的《荆州图副》等书均记载诸葛亮居住在隆中。
因为诸葛亮是在其叔父诸葛玄死后才来到隆中的,时年才十七岁,加之身为布衣,经济又不富裕,所以在隆中居住时一边继续读书、交友,一边耕种田地。诸葛亮的寓居与躬耕为同一地,所以南朝刘宋裴松之在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叙述到“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后,紧接着便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的一段话,标明诸葛亮是在邓县隆中躬耕。
既然诸葛亮是躬耕于南阳邓县隆中,为何不直接写明,而说“躬耕于南阳”呢?这是因为奏疏要求文字要简练,所以只指明郡望。另外,隆中是一小小山村,当时并不出名,而南阳是郡名,又是“帝乡”,无人不晓。另外,诸葛亮想“兴复汉室”,这“汉室”实指东汉,而东汉开国皇帝及其统治集团主要成员均出自南阳郡,所谓“南阳帝乡多近亲”。诸葛亮向刘禅说自己躬耕于南阳,在当时还具有某种政治意义。
第三,以当时襄阳与宛县两地的政治形势来看,迥然不同。公元190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两年后加州牧,治所刚从武陵汉寿(今湖南汉寿)移到襄阳。此后,直到公元208年病逝,一直坐镇襄阳,并采取“爱民养士,从容自保”,以观时变的方针,致使襄阳及周边地区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才聚集,从北方来此避难的士民特别多。而此时南阳郡宛县的情况就不同,该地虽属荆州境土,却一直是战乱频繁的不稳定地区。在诸葛亮躬耕期间(197-207)宛、穰一带正是战乱频繁发生时期。试想,宛县为曹操敌占区,一心想兴复汉室,视曹操为国贼的诸葛亮会去宛县寓居吗?原想诛灭曹操的刘备能跑到敌占区去三顾茅庐吗!
第四,从诸葛亮躬耕时期的人际关系来看,也应寓居在邓县隆中才合乎情理。史载,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中庐(今南漳县境)大族蒯祺,二姐嫁给了襄阳大族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他迎娶的妻子是沔南名士黄承彦的女儿。诸葛亮最崇拜的老师庞德公住在襄阳岘山南,司马徽住在襄阳城东,因为诸葛亮经常去庞德公家求教,庞德公逐渐了解诸葛亮的才志和抱负,便品评诸葛亮为“卧龙”。此外,诸葛亮的好友庞统住在白沙洲,徐庶、崔州平住在襄阳城西的檀溪。上述地方都离隆中很近。所以诸葛亮才能与这些好友游学。另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表长子刘琦因受排挤,曾多次向诸葛亮谋求自安之术。刘琦是随父刘表住在襄阳城内,只有诸葛亮寓居隆中才可用“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的历史典故暗示刘琦要马上离开襄阳城。这一切都说明,如果诸葛亮不是在襄阳生话了十几年,是不可能与住在襄阳城周围的亲朋好友建立如此密切而又错综复杂关系的。
总之,以上四个方面就足以说明诸葛亮是寓居躬耕于南阳邓县之隆中。
四、“宛县说”的依据是什么?
坚持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宛县卧龙岗的主要依据是两条:一条说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上表刘禅的奏疏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就是最可信的直接证据。他们说,这南阳虽是郡名,但南阳郡治在宛县,因此南阳既是郡名,又是郡治宛县的代称,“躬耕于南阳”,既可理解为躬耕于南阳郡,也可理解为躬耕于宛县。
这种说法是极不严谨的。从逻辑上说,“躬耕于宛”,可以说成是“躬耕于南阳”,但不能说“躬耕于南阳”,就必定是“躬耕于宛”。以史料记载而论,唐以前的史籍中不管是正史,还是其他史籍,没有一条关于诸葛亮“躬耕于宛”的直接记载。南阳和宛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此是分得很清楚的,从来没有将宛代替南阳郡名的。如前引《隆中对》中提出的率荆州之军
以向宛洛,就未将南阳代称宛。又如《武帝纪》、《王昶传》、《先主传》等都有证据表明南阳和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域概念,如《三国志·魏志·文聘传》曰:“文聘字仲业,南阳宛人也。”据考证,整个《三国志》中使用南阳和宛这两个地名的地方有139处,其中记载历史事件的南阳用了36次,宛用了39次;记载人物籍贯的南阳用了44次,宛用了2次;记述官职称谓的,南阳用了15次,宛用了2次,还有无地域概念仅借用南阳二字的,有1次。
上述说明,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是指郡名,绝不代称宛县,那种将躬耕于南阳理解为躬耕于今南阳市,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二条证据是,古人云山南水北为阳。历史上以汉水之北为南阳郡,汉水之南为南郡。南阳郡与南郡是以汉水为天然分界线,虽个别县在汉水西南,属南阳郡,但《水经注》记载从今茨河到张家湾这百余里河道是东西向,因此这一段自然以汉水为两郡的分界线,也是襄阳县和邓县的分界线。隆中在汉水以南,故不属于南阳郡。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载是错误的,《水经注》沿袭习凿齿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这种说法是完全依据推测得出来的,没有任何史实作依据。山南水北为阳是正确的,一般来说是以河流作为分界线,但河流的走向总是曲折的,就算缩小到只有百余里的河道,那也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东西走向,更何况用百余里的河道来判定两个郡的分界,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时南郡辖17个县,其中包括襄阳、中庐、江陵等县,而南阳郡辖37个县,这37个县中,居汉水以南的有3个县,可见以汉水为界,那也不是绝对的。隆中是在汉水以南,但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明确记载隆中属邓县管辖,当然属于南阳郡,史籍中还没有隆中不属于邓县的记载。习凿齿是襄阳人,对家乡的历史和隆中的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域变化以及风土人情很熟悉,加之他治学严谨,所记载的史实是真实可靠的。他除了撰写《汉晋春秋》这部书外,还写了一本《襄阳耆旧记》。裴松之在为《三国志·诸葛亮传》作注时就征引《汉晋春秋》材料10条,征引《襄阳耆旧记》3条。有关诸葛亮生平事迹的很多材料,如司马徽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诸葛亮迎娶黄承彦之女,诸葛亮七擒孟获,《后出师表》等,都是从习氏记载中得知的。如果对离诸葛亮寓居隆中才172年的史书记载不可信,难道距诸葛亮寓居地一千多年的明清地方志倒可信吗?《水经注》是公认的历史地理方面的权威着作,把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轻易否定,说“靠不住”是不明智而又错误的。
还有—条史料可证明隆中属于南阳郡。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襄阳县”记载中说:“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这就说明万山以西,汉水以北属南阳郡;万山以东,汉水以南属南郡。而隆中在万山以西,自然属于南阳郡。因此,根据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这两部史籍记载,可以断定隆中当时属于南阳郡邓县管辖。
南阳有人总结说,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宛县有主证8条,旁证15条,理证6条。笔者细观这些证据,发现都不充分。其中除引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作主证第一条外,其余论据多是伪作,如《黄陵庙记》,是明清时期的著作。又如明代何宇度的《益部谈资》、清人汪介人的《中州杂俎》等都经不起考证和推敲,如果加以引用,很难使人信服。此外,更多的是列举唐代李白、杜甫、刘禹锡等诗人所写作的诗作为论据,如李白《留别王司马嵩》云:“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父吟。”杜甫《武侯祠》云:“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刘禹锡《陋室铭》云:“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人所共知,诗文有其文学上的特征,含义比较隐约、笼统,加之又要讲究平仄、对仗、押韵,因此这些诗文不像史书记载那样准确,一般不能作为直接性的史料使用,而且这些诗文中的“南阳”是根据诸葛亮自言“躬耕于南阳”而来的,并未去考究这“南阳”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因此采用唐代大诗人所写的诗,是不能作为“南阳宛县说”的证据的。
南阳方面不仅找不到一条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记载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宛县说”的史料,也找不到一条宛城有诸葛亮居住遗迹的记载,于是他们便在文字上作游戏,说什么“家”、“故宅”、“旧居”、“躬耕地”等词不是一个概念,因而提出诸葛亮“游学寓居隆中”,“躬耕于南阳宛县”。他们在提出这个观点之前没有想一想,襄阳距宛城三百余里,若以每日走100里计算,来回走一趟也得要六天,这农田又如何按农时季节进行犁田,播种,施肥,除草和收割呢?何况宛城至襄阳的通道,常为战乱所阻,难以通行,将居住地与耕种地分隔这么远值得吗?时称“卧龙”的诸葛亮会这么傻吗?再者,诸葛亮刚开始躬耕时只有十七岁,而且住的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茅草盖的房子,又没有大批家业和田产,他又如何在居住地以外的地方去购置田产进行躬耕呢?所以这种提法不仅毫无史料依据,而且不合情理,根本站不住脚,纯粹是一种主观臆测。
五、谁最有发言权
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争论,只是史学界一场小小的地望争论。本来学术问题是可以通过学术界同仁有理有据的探究,最终得出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结论来的。当然这个结论不是取决某位领导的谈话,某一部门的红头文件,某一位史学家的表态或某一研究结构的鉴定,更不是一篇教材的篇名或对某一词语的注释所能确定了的,而是要依据关于这一历史人物活动最早的史料记载,这才是最具权威性的,可靠的,无可争辩的,因为史料是当时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的客观记录,这是任何人无法改变或抹杀的。要推翻第一手材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进行实事求是的考释,来揭示第一手材料的矛盾和作伪的痕迹。简单用后人的看法来否定前人的成就,在方法上是不科学的。其次是对史料的采用、分析和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对史料的考证,要采用严肃的态度,写出的论文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要根据历史事实,而不是靠假设和推论,更不能靠编造和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那种只采用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而对相反的材料采取一概否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笔者认为,只要参与争论的同仁,依据唐以前的正史、别史以及地理类中的文献数据,而不是采用宋元以后的方志、家谱、碑文等材料,因为这三种资料多囿于地方观念,或取传说,或取私家家乘入文,这些都不很可靠,难以辨正。加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切以当时的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去讨论争辩,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就可以解决。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用主观的意愿任意割裂、取舍、否定和曲解史料,那这场争说是得不出结论来的,也违背了开展学术争论的目的,而且这样争论下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学术价值。
六、如何看待这场争论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虽有过三次,但每次争论的背景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如第—次明清时期的争论,虽两地编纂的地方志都声称诸葛亮躬耕地在自己所属范围内,但作为官修的一统志却有自己的看法,一些名人学士的论着仍以史实为依据,坚持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隆中的正确说法,如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97“襄阳府·襄阳县”条云:“隆中山,府西北二十五里,诸葛亮隐此。”甚至当地的官员也认为躬耕地问题已成定论,不必再争论下去。清道光年间南阳府知府顾嘉衡写的一副对联就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民国时期卢弼编写的《三国志集解》以及其后的史学名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编著的《中国通史》等著作,都引用史籍论证诸葛亮躬耕地在今襄阳隆中。连1976年5月南阳地委宣传部编写的《诸葛亮小传》有关章节中也承认“隆中当时属南阳郡邓县管辖”,“诸葛亮在这里度过了十个寒暑”“小小的隆中实际上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自称‘躬耕于南阳’”。在南阳市博物馆编印的《武侯祠简介》中,也确认“南阳卧龙岗上的武侯祠”以及拜殿、茅庐等,是后人根据诸葛亮躬耕时的生活起居而兴建的纪念性的建筑物。1987年3月由南阳市委宣传部编印的《历史文化名城南阳》一书中,多次称卧龙岗武侯祠是“诸葛亮纪念地”,而不是故居。文中还说,“南阳的‘诸葛庐’、‘抱膝石’等等虽系膺品,但由于诸葛亮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唐人刘禹锡在他的名文《陋室铭》中,曾将‘南阳诸葛庐’和‘西蜀子云亭’相提并论,故而南阳武侯祠便颇有名气了。”
上述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凡是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方法,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是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
但是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战略,人们发现利用当地历史名人的声望,借用名人遗迹,不仅可以提高当地的知名度,而且可利用“名人效应”发展旅游业,对外招商引资,从而带动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就出现了有的人不顾历史的真实,不考虑观点是否科学,论据是否经得起推敲,而一味的去争名人,争古迹,争第一,“说你错,你就错”,不需要什么文献数据来证明。仅仅因为教材选用了《隆中对》和对“南阳”的注释错误,南阳方面大做文章,兴师动众。其实这事情很简单,教材注释错误,要求出版社改正就行了,事实上他们己经改正了,但南阳方面仍不放过,准备召开学术讨论会,掀起争议高潮。这些做法就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了。其实正如南阳纪国强所言:“名人之争,学术之争,仅仅只是表像,其实质牵扯到能够造福一方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南阳诸葛亮研究会主要领导成员任积太大声疾呼:“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南阳不能没有诸葛亮。”该会常务理事史定训说:“我们不仅应该把躬耕地的争论坚持不懈地持续下去,而且一定要打好诸葛亮这张牌。”看来南阳方面铁心要将诸葛亮躬耕地从襄阳隆中抢夺过去,否则誓不罢休。
从纯粹的学术争论来说,襄阳、南阳两地出版的多本论文集已将所有史料搜集得差不多了,双方的论点和论据也都摆出来了,全国的史学工作者从中也都明确了躬耕地的真伪,略为有点历史知识的读者,也从中看出了谁讲的有理,谁说的无理。因此,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史料以前,尤其是新的考古资料证实,双方再争论下去就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了。要不就是争论时“炒现饭”,“贩旧货”,这样做既浪费笔墨,又耽误了学者们的宝贵时间,还会使人心烦,失去读者群。
如果将躬耕地的争论作为“名人效应”,硬要与当地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那就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变成另外一回事了。诚然,利用“名人效应”,确实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名人效应”应当与历史的真实性结合起来,只有真实的历史,才具有科学价值,也才具有说服力。不尊重历史事实,或超越历史去讲求“名人效应”,那种“效应”只是暂时的,到头来既失去了历史名人,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固然离不开历史,但历史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决定的因素。在今天世界上或国内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完全靠历史悠久或历史地位的重要而获得较高知名度的是极少数,即使是这些城市,也离不开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比如山东曲阜是历史文化名城,孔子的故乡,但它的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如不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青岛,这就说明,单靠历史名人并不一定就能使当地经济得到发展,更主要还是要靠地方政府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对外改革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积极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等等措施,才能把经济搞上去,知名度才能得以真正提高。
总之,不能把“名人效应”看得太绝对了,那种一味强调名人效应而不顾历史的真实,去争名人,争古迹,这是对历史价值的最大误解,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如愿以偿的。
今南阳武侯祠作为后人纪念,怀念诸葛亮的建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在开发旅游资源的今天,南阳武侯祠不仅应当照样供人参观瞻仰,而且还要对其文物倍加保护,继续增加新的景点,给更多的游人增加休闲、娱乐的场所。我相信,只要扫去附会者散布在她周围的迷雾,她会显得更加纯真可爱。否则,“假做真时真亦假”,她真正的历史价值和作用就反倒会被污染,为人们所不熟悉了。
(该文原刊载在2003年10日3日《襄樊晚报》第12、13、1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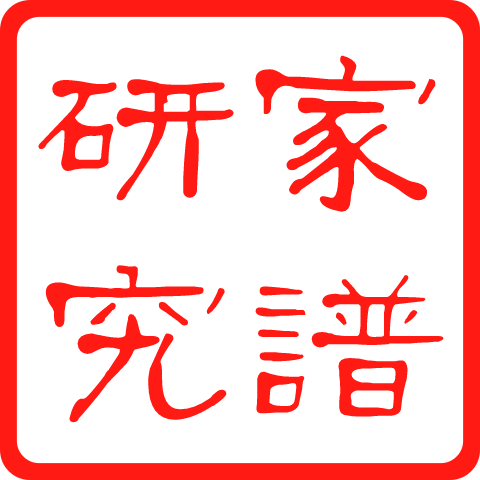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