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近期在法国出差的朋友,饶有兴致地跟我分享了一个冷知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和巴黎共享相似的纬度。
“所以巴黎也是满街五颜六色的莓子,都跟我们小时候园子里种的一模一样。”
给我发的照片里,她站在一个果蔬摊前,背后红色、蓝色、淡粉色的莓果映衬出她灿烂而好奇的笑脸。我立刻认出了品种:托蓬儿(树莓)、嘟柿(蓝莓)、灯笼果(醋栗),于是开玩笑:去了半天,你还在咱大东北啊。
很少有人知道,东北的夏天也是莓果的夏天。这里不仅有沙瓤西瓜、糖罐香瓜、沙果、菇娘、李子等土著水果,还有树莓、蓝莓、醋栗。夏天一到,它们便会早早占领市场。
只可惜本地人很少频繁光顾。它们要么带着些野性未脱的酸,要么要花上一些大价钱,对于已经长大成人的东北小孩儿来说,这些莓果与他们的交集,更多的发生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它们,是极其特别的存在。
树莓是跟我们最熟的。
古早年代,我们叫它“托蓬儿”,一般在某个小平房的后墙根儿,或者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也许挨着一片废墟,也许被野生藿香、鼠尾草包围,大人上下班无意路过,托蓬儿的命运因此改变。
他们总会一眼瞟到它,之后便像宣布重大新闻似的在饭桌上播报,惹得一分钟之前还要将零食当主餐的孩子端起饭碗,筷子刨地飞快,完成“吃饭”任务后奔向大人口中的目的地。
一个结了果的半人高灌木十分骄傲地扇动树叶,孩子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宝藏。从此以后,他会在上学放学之余频繁光顾,看着果实的颜色从白色变成红色,再从红色变成更深一点的红色,再从深一点的红色变成要渗出汁水的红色。
其实果实从白色刚变成红色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品尝了一番。只可惜迎接他的是不小心吃下中药的苦涩,以及迅速破灭的奢望。他也学习到了一个生活常识:不是所有水果,都会像沙果、野杏子一样,在青果的时候就可以勉强吃到肚子里,必须果蒂某天轻轻一碰与果实自然分离,托蓬儿才拥有了清新浓郁的浆果味——它的酸度在蓝莓、醋栗中排在最末。虽然只有一丝浅浅的甜,但你就认为这是一种美味的水果,甚至把它看作友谊的象征。
“诶,告诉你一个秘密,老俱乐部后面有一棵托蓬儿,现在已经熟了。”
“托蓬儿是什么?”
“就是一种可好吃可好吃的水果。”
“放学我们一起去。”
“嘘,小点声。”
孩子很难做到像大人一样对某件事守口如瓶。没过几天,托蓬树下就围上了大大小小的孩子。大家一致认为站在树下边摘边吃是最美味、最科学的食用方式,每个人都在急迫地寻找下一个目标,鲜红的汁水不小心蹭到衣服上、裤子上。
作为第一个发现它的哥伦布,你的心里会充满了小小的失落,进而“发出这是我先发现的”傲人宣言,即便所有人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颗最红最大的果子,没人注意到你说了什么。
这棵树莓就这样承包了一整个夏天。因为它的出现,孩子们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树莓树,你也开始意识到,分享似乎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让你失去了第一颗树莓,也让你拥有了更多抢占树莓的机会,每次靠近它都会促发一次百米赛跑,偶尔还会爆发因食物引发的战争,吃到一颗甜度过高的树莓喜极而泣也是有可能的——手舞足蹈摔了一跤。
许多年后,当树莓以装成小盒的形式出现在超市或早市,你会想起当年那个为了树莓奋不顾身的自己,满心欢喜买上一盒,然而下肚以后,味道的陌生又让你与之划清界限,心里忍不住盘算着,有朝一日摘种一棵,如果味觉记忆可以像旧照片一样储存下来。
食物的乐趣在于食物以外的参与感,是树莓带来的启发。
小时候蓝莓不叫蓝莓,叫“嘟柿”,一串串紫色球体挂在草甸冻土层,果树是低低矮矮的小灌木,它们似乎喜欢与人捉迷藏,采摘者总是有备而来,在不起眼的小灌木面前及时驻足,才能像鄂伦春人或者鄂温克人那样,从鸟雀那里分得一杯羹。
跟树莓不同,嘟柿的酸是一种尚未驯化的酸,酸得刺激而原始。围着它边摘边吃的行为,仅限于罕见的嗜酸勇者,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把它们直接放进篮子,等待白糖的救赎。
洗干净的嘟柿撒入大把大把的白糖,腌出紫红色的汁水,就是放学后的零食;和白糖一起熬成黏稠的果酱,也是另一种储存方法;倘若长辈有时间,愿意将嘟柿里加入大量的水,再撒入白糖煮到软烂做成酸酸甜甜的饮料,那滋味更是难得的快乐。
那时的它还是一种小众水果,存在只是为日常饮食注入仪式感: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吃糖拌嘟柿;今天的面包是一块上好的面包,所以抹上嘟柿做成的果酱;今天的客人是一位重要的客人,所以我们要从冰箱拿出提前做好的嘟柿果汁来招待。
那时的嘟柿,售价平易近人,一年一茬,皮薄易坏,很少有人为它做广告。没多久,人工种植的蓝莓接踵而至。后者扁圆的外表,硕大的个头,味道毫无攻击性,充满诱惑的甜显然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味蕾而生。在塑料大棚的帮助,它们取代了嘟柿在一部分人心目中的地位,开始肆意向各个领域进击。
蓝莓酒,蓝莓果干,蓝莓软糖,“大众水果”开始成为它的标签,直到有一天,人工种植蓝莓在万物休养生息的冬日也正大光明地到来,它彻底离开了嘟柿的世界。那是一年中蓝莓身价最贵的季节,味道有时是一种不确定的甜,在吃惯了嘟柿的本地人眼里,它们呆滞,木讷,像在侮辱一条灵活敏感的舌头。
因为蓝莓的带头作用,翌年夏日的嘟柿也进阶为贵族水果,为了成为当季第一筐抵达早市的嘟柿,它们在匆忙的采摘中混杂了未完全成熟的紫红色果子和青果,唯一值得尊敬的,大概就是果皮表面挂着象征新鲜的白霜。
昔日的嘟柿自由人,沦陷为嘟柿的价格俘虏,他们一窝蜂地跑到本地蓝莓采摘大棚,野不野生不再重要,尤其当一种大小类似嘟柿,但甜度略高的蓝莓近年开始出现。采摘大棚变成了蓝莓爱好者的天堂,这里有更高的性价比,也能体验站在灌木旁大快朵颐的快乐。
契诃夫有篇小说《醋栗》,写的是一个人对醋栗的执念,他要买下一座庄园,“他不能想象一座庄园,一处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居然会没有醋栗”。最终他实现了愿望,醋栗果树却是从其它地方运来的。它们第一次结果,这个人眼含热泪兴奋得说不出话,但吃了醋栗的客人对它的评价“却是又硬又酸”。
醋栗家族成员众多,本地醋栗有两种,一种是黑色的,一种是红色的。黑醋栗在本地被叫做黑豆果,也叫黑加仑,红醋栗则统一叫做灯笼果。它们的果树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低矮的灌木,叶子呈手掌形,黑豆果的树没有刺,灯笼果树上的刺跟玫瑰花差不多。
我们最早认识醋栗,也是缘于大人们。他们在山里作业,经常会带一些小物件回家:松塔、蘑菇、圆枣。某一天,他们带回一些绿色、黑色的小果,绿色口感酸脆,略带透明,里面纹路清晰可见,黑色汁水充盈,酸中带甜。它们无一例外都有一股鲜活的山野气息,这就是灯笼果和黑豆果。为了丰富自家果园的多样性,大人们像契诃夫小说里描述的那样,种下黑豆果、灯笼果的树苗,醋栗由此成为自家果园的一份子。
夏季是醋栗的采摘季。黑豆果完全成熟,一颗黑黑的小豆粒,灯笼果还没有,触目惊心的绿色。孩子们去找伙伴们总会带着它们,裤兜塞得满满当当,大摇大摆站在伙伴中间,夸张地把醋栗往嘴里塞。
这是一次无比认真的咀嚼,放慢速度,等着小伙伴提问的到来。在对方充满艳羡的眼神中,缓慢咽下口中的浆果,一脸无所谓地将准备好的开场白脱口而出:
“这是我爸,不,我姑姑从苗圃地带回来的”。
“好吃吗?”
“好吃。”
虚荣心得到满足,心情也愉悦起来,拿出几颗与大家品尝变得十分容易。这时的你会心满意足地听着伙伴们对黑豆果的称赞,聊起灯笼果时又被激起斗志:
“啊,太酸了。”
“一点也不酸。”
说完,硬着头皮将几颗灯笼果一股脑儿地放进嘴里,牙齿在打架,脸绷成严肃状,完全下咽才勉强挤出一丝轻松的微笑。如果对方乐意效仿,赶紧回家再摘上一兜,发起新的一轮灯笼果挑战。
它们就是这样没等成熟就吃完的,所以我们很少看到所谓的“红醋栗”,只有同样急不可耐的黑醋栗及时慰藉那些跃跃欲试的东北小孩儿。
今天,醋栗依然保持着朴实无华的售价,买完醋栗的人提着它走在街上,多半也会遭遇亘古不变的提问:酸不酸?这时你会发现,生长在大自然里的它们,果然很难变得受欢迎,除非也像嘟柿一样接受人工改良。但你又不希望它们像嘟柿一样,被改得个性全无,面目全非。
或许,富有层次感的酸才是它们的水果底色,正如四季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高纬度地区。这些,才是属于这里最有生命力的滋味。
本期作者|王文静
编辑|梅姗姗、斯小乐 视觉/创意|BOEN
摄影|小红书@小函的小森林、如如ru、肉丝儿、馋猫日记、sapbear、Cx330-rong、是吃货小徐、Chen、至尊盖、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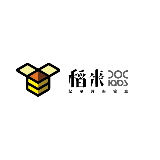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