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剧演员生活五十年
陶古鹏
花鼓戏的种类和发源地、花鼓戏的唱腔和演变、花鼓戏乡班种种、花鼓戏进武汉城市以后、楚剧定名与血花世界、宁汉合流中楚剧又遭挫折、楚剧参加抗日宣传、日寇投降到解放

我是湖北省黄冈县阳逻乡人(现为新洲县),一八九六年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父亲和姐夫都会唱高跷戏和花鼓戏,但他们都是业余演唱者。我受他们的影响,十四岁起就跟他们学高跷戏和花鼓戏,我学的是小生戏。我从二十岁,搭入花鼓戏班,开始成为正式演员,演小生戏,兼演老生,至一九六五年,我七十岁,共演了五十年。这五十年的演剧生活,在旧社会经历过无数的坎坷、曲折,也受过各种不同的伤心遭遇;解放后,获得了翻身,我的伤心往事,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将我在五十年的楚剧演员生活中,所知道的楚剧的情况,回忆写出来,供作参考。其中所提出的材料,有不全面或错误的地方,请知情者予以补充和指正。
花鼓戏的种类和发源地
清朝末年,湖北的地方戏,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大戏,即汉剧;一种就是花鼓戏,即楚剧。大戏有悠久历史,盛行于全省,白天、晚上都可以公开演唱。花鼓戏虽也盛行有年,但不为社会上所公认,只得在夜晚偷着演唱。
花鼓戏有东、西两个路子。西路子花鼓戏,指黄陂、孝感、云梦、天门、沔阳等县所唱的调子而言。东路子花鼓戏,指鼓戏,指黄冈、浠水等县所唱的调子而言。东、西两路子花鼓戏的戏码一样,只在腔调上稍微有点不同。花鼓戏的演员以黄陂人最多,黄冈、孝感入次之。
汉戏和花鼓戏都是由黄陂、黄冈这两个地方兴起来的,后来发展于黄冈的沙水口镇。汉戏中有西皮、二黄。为什么叫西皮?黄陂县旧称西陵县,后改为黄陂。至今黄陂尚有古老的西陵寺存在。西皮可能指的是西陵县兴起的调子。二黄,一般指黄陂、黄冈两地所兴的调子而言(编者注:现代戏曲史家,对西皮、二黄的起源,还有争论)。花鼓戏盛行于黄冈、黄陂、孝感、云梦、鄂城、红安、浠水、天门、沔阳、大冶、沙市、宜昌等地区。除坐馆的专业演员外,在农民、小手工业者之中,还有很多业余演,员。业余演员多在农闲时,由农民邀请在村子里搭台演唱,不要报酬,只接受吃喝招待。专业演员在农村演唱,靠农民收米和点戏收入维持生活。在茶馆搭班的专业演员,伙食靠茶馆老板供给,工资靠观众点戏所得分账。当时点一出戏,给一二百文钱。
在京汉铁路未兴建前,汉口还不十分热闹。热闹的地区却是黄冈县阳逻上面的沙水口镇,即沙口、水口河会流的处所。这是一条交通要道,许多两广、湖南等省去北京的客、货由这里起坡、换车、转北上,所以这个镇上非常热闹。花鼓戏就在这个镇上的茶馆里演唱。这时花鼓戏仅有《访友》、《送友》等二十多出小型戏。镇上仅有两、三家花鼓戏演出场所,沙水口镇上唱花鼓戏最出名的演员,小生中有牛伢!何伢!好伢!唱花旦的有嗯伢!都是黄冈人。在旧社会,人们把唱戏的,尤其是唱花鼓戏的不当人,称呼他们伢、伢的。连姓名都不称呼。伢即娃娃的意思,当时他们都是中年人了,但唱到老,仍被人喊为某某伢。除此之外,还受地痞、流氓的压迫,好伢因对流氓的欺侮,进行反抗,终被流氓打伤,最后是死在流氓手中。
花鼓戏的主要唱腔和演变
花鼓戏的唱腔,有下列几种:雅腔、悲腔、仙腔(分别时用)、讨学钱腔、纽丝腔、四平腔、十姊妹腔、西江月腔、卖白布腔、卖棉纱腔等等。其中雅腔、四平腔用的最多。
上面所述诸腔,大多来自民间的歌曲或散曲。如西江月腔,宋词、元曲中,都有这个牌子,而花鼓戏的这个腔,显系从词、曲中吸收而来。就各腔命名的意义来说,有的文雅,有的凄凉,总的来说,都是湖北劳动人民的歌声。由于演员中有嗓子不好的,唱出来如同哭声,当然这种演员也不是不想把唱腔唱好,只因嗓子不由主,为了迁就自己的嗓子,一律唱成哀调味儿了。把雅腔给唱得不雅,把四平腔也唱成悲调。这两个腔,偏偏用的最多,再加上社会上一些人盲目捧场,日子久了,这些不正的味儿,影响了下一代演员。在观众中,给花鼓戏造成了不良印象。
在那时,花鼓戏演员,文盲很多,自幼拜师学艺,唱词多系口授,难免以讹传讹,一错再错。有时抄录脚本,传授的人,
故意丢掉其中的正确而紧要的词句,生怕别人夺了他的“看家戏”。有的演员演唱时把较为文雅而又较为费解的词句,改得过于粗俗。为了迎合观众中的庸俗低级趣味,故意涉及淫邪卖弄荒唐,给人以攻击的口实,也是有的。
花鼓戏只有锣鼓伴奏,没有丝弦伴奏,而以帮腔来衬托。花鼓戏的帮腔与川剧的帮腔有所不同,川剧的帮腔,只帮每一小段的最后一句的下句。而花鼓戏的帮腔,对于上下句的末句都要帮。帮腔完了后,就起锣鼓点子,来加以烘托。这时花鼓戏的锣鼓点子还很少,只有长槌、锁槌(这两个点子都有快慢之分)、走槌。后来从京剧、汉剧方面吸收了很多。
社会上有些人向我们提意见,说花鼓戏好是好,就是不沾弦。不沾弦,就不成戏。于是我们想到要进行改革。要改革,只有向汉剧学习,加胡琴伴奏,去掉帮腔。我就请汉剧老师傅严少臣给我们设计音乐,由我开始采用胡琴伴奏上台演唱。我第一次胡琴伴奏演唱的是《白扇记》。
约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前后,我在天仙茶园,采用胡琴伴奏的效果,反映良好。后来其他各家花鼓戏茶园,也都仿效我们加上胡琴伴奏。在加上胡琴伴奏的同时,逐渐添增了月琴、锁呐……等乐器。从此,花鼓戏有了伴奏的曲牌,这些牌子一般都由汉剧中吸收而来。那时的花鼓戏,处处向大戏(汉戏)学,争取社会上承认花鼓戏是一个正式剧种。
为了应付社会上的各种“爷们”(青红帮的大爷、军政界的老爷、工商界的财爷……等),我们加上了“跳加官”这个节目。这样就把花鼓戏无形中自我升格成大戏派头,如遇“爷们”来看戏时,随即将正式节目中断,加上一幕“跳加官”表示欢迎。如遇特别重要的人物,不仅“跳加官”,还放鞭炮,表示隆重欢迎。那些“爷们”见了“跳加官”,很高兴还给以赏钱。我们也乐得受之。
花鼓戏乡班种种
花鼓戏盛行于农村,搭一台子就可以演唱起来,一般称为草台戏。为了适应农村草台戏的需要,花鼓戏的演员就组成乡班来了。一个乡班,只有演员七至九人(包括打锣鼓的在内),每班有一个班头,一般称为头人,也有称老板的,但这个老板没有剥削。头人对内管行头、招呼干活,对外负联系责任。七个人一班的较多,其中三人唱旦角,四人唱外角。这七个人都会唱戏,也都会打锣鼓。一般是三个人搞场面(包括锣鼓),四个人唱。上演的节目,折子戏居多。
由于农村不景气,一台戏唱完了,往往“荒了场”,即没有人继续邀请我们了,无演出的机会,这就影响收入,威胁着生活。为了生活,多求演出机会,增添收入,形成种种“陋习”,乞助于人。
乡班遇上“荒了场”,首先是送戏上门。由于我们演员的行李简单,行动既方便,又迅速,这村不邀请,就跑到别村去找爱好花鼓戏的人,请他领着去拜望地主阶级中的乡绅们,向他们请安问好,诉告艰难,要求在这个村子里上演。得到允许后,
才能请求花鼓戏的爱好者们,带我们去收米。有时一些乡绅,说花鼓戏“诲淫诲盗”,有伤风化,不准上演。如当时的著名演员高月樵在沙市附近跑乡班时,曾经一天连跑四个村子,走了大几十里路,都不准上演。有时逼得无路可走了,就只好直接找花鼓戏爱好者,央求把我们安下,待收了米后,再由花鼓戏爱好者带我们去恳求乡绅们,这样乡绅们看在带路人的面子上,就不好再赶我们走了。
花鼓戏演员跑乡班,都学会了点汉戏,乡班每到一个村子,先演三出汉戏。这叫“半台戏”,这是因为花鼓戏不能公开上演,借汉剧给自己衬场面。三出汉戏唱下地来“接彩”,再正式上演花鼓戏。一般乡班收入,靠点戏进账。每点一出戏给一百文钱,也有给二百文的,最多的也有给三百文。如有人点戏,问题就解决了。如无人点戏,就进行“开门接彩”。“接彩”由一个外角(多是丑角)先上唱一段四平腔。如:“玩了一场又一场,刘秀十二走南阳。岑彭、马武双救驾,二十八宿闹昆阳。…”等彩词。旦角接唱四平腔,后转十姊妹腔。唱些要求点戏的内容。在点戏唱完后,又没有人继续点戏了,就进行“谢彩”。
“谢彩”是旦角上唱十姊妹腔:“彩钱不住往上仰,好比当年赵玄表(即赵匡胤)……”等等向人讨好要钱的内容。“接彩”、“谢彩”的词,都是由演员随口编的。有顺口溜的意味。除了接彩、谢彩之外,还有“打彩”。“打彩”是在演出中进行。每当一个演员,特别是旦角,在备受观众欢迎时,往往结合剧情如在逃水荒、喻老四打瓦、郭丁香赶子、放牛等几出戏中打彩,这几出戏都是跪在街上乞食或乞求盘费的一场中,观众“打彩”。“打彩”的人大都是乡间的小商民、小手工业者等。“打彩”的用意,有两个:一是可怜剧中人物的遭遇,一是藉此机会来捧演员。也有戏弄演员的,把铜板朝向跪在台上演唱的旦角脸上、头上、身上打的。跪在台上演唱的人,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有钱可赚,害怕的是怕闪躲不及,打破头或打瞎眼。如高月樵有次被打破眉棱骨,一直留有个伤疤。
乡班演员不论走到哪个村子里,连私人的房子都不让住,只准住祠堂、寺、观。有时在这个村子里唱了,下了戏后,仍要到原来住的那个村子里去住,来回相距十几里路。吃的问题,演员进了村子,安住了以后,由花鼓戏爱好者带着唱花旦的演员上门去“收米”。与其说是收米,不如说是沿门讨米。柴、米、油、盐、小菜等都收。每次收的,只够这个班子吃一天。如果有给点豆腐的,那就算是打牙祭了。如果有人来邀请去唱,多少还有点戏价。如“荒了场”,送戏上门,那就没有戏价了。一般不在乎戏价,主要是靠点戏赚钱。乡班中,不论是戏价、点戏、打彩得来的钱,统统归全班收后,统一分配。折账的方法是同城市花鼓戏班一样,按股分账。玩乡班有原则,如只会唱,而不会打锣鼓,就不能得整股。但分账又以唱花旦的为主,因为他们到处最受欢迎。如上门去收米,只有唱花旦的去收,才能收到,唱外角的去收,就没人给。折账最多的是整股,最少的是半股,也有九、八、七厘的不等,一般唱生角、旦角的都是整股。吃股的多少,看演员的艺术声望结合资历而定。就是吃整股的演员,收入也少得可怜。
流动在农村演唱的花鼓戏乡班,不仅生活困苦,形同乞丐。
而且,时时刻刻处于紧张警戒之中。每走一村,求得该村乡绅的允准上演,还要躲避官府的追捕。在农村演出,不时可以看到衙役押着满脸胭脂花粉被反绑着双手的花鼓戏演员向县城走去。当台上演唱正精彩的时候,有的演员突然从后台溜走,观众莫明其妙!原来衙役在前面出现了。
花鼓戏进武汉城市以后
在武汉,花鼓戏是严禁上演的。自从汉口有了租界,帝国主义想借用花鼓戏来繁荣租界,敛征税收,利用中国流氓找来花鼓戏班,开始在英租界建立“清桂茶园”演唱花鼓戏,后来逐渐发展,法租界在现在的友益街一带先后建立了共和昇平楼(现入民剧场)、玉壶春(在车站路京汉旅行服务社处)、天声舞台(现民主剧场)、春仙茶园(后改为天仙茶园,座落在现东华浴池)等处也演唱花鼓戏。

沈云陔和梅兰芳
我开始搭班在春仙茶园。当时春仙茶园的前台老板是大流氓范明发,后台老板是杨化民,杨原是花鼓戏的花旦演员。这个班的主要演员中:花旦有陈月仙、小福仙、余翠云、小月红,后来沈云陔也来搭班了。老生有彭月堂、黄炳狗。小生有陶云卿、陶古鹏,花脸有陈月华,丑角有李小安、钱半头(矮子)等。象其他许多演员如小宝宝(江秋屏)、小双红(余文君)、小桂红、小桂仙、灵芝草、小官宝(李百川)、月月红、小桂芬(章炳炎)、张宏奎、王连升、黄黑狗、匡伯林、肖雅臣等分别在共和昇平楼、天声、玉壶春等茶园演唱。这时,四家花鼓戏茶园,共和昇平楼、天声、玉壶春三家均可容观众千余人。春仙最小,也可容纳观众五百入。每值锣鼓起响,尤其是华灯初上,不及三百米范围内的街区,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弦歌之声,飘荡夜空,突出一派畸形繁荣!
正当花鼓戏演员付出高度的艺术劳动,给茶园带来十分繁荣的时候,法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雇用的中国流氓打手,伸出魔爪,对花鼓戏演员敲骨吸髓,恣意侮辱。
仅就春仙茶园而论,全场可容观众五百人,场场客满,生意兴隆。每客一壶茶一百文,戏票二百文,每场平均以每客二百五十文,以四百人计算,一天日夜两场,共收二百串钱。每月实收六千串钱。我们戏班有三十人,每月只给六百串钱的工资,这恰恰占老板收入的十分之一。每人每月工资二十串钱,扣伙食六串钱,每人净得只有十四串钱。如此微薄之数,实难维持一家几口的生活。其他几个茶园的花鼓戏演员也是如此。
这样就逼着演员依靠观众点戏,增加收入,补助家用。由于生活靠点戏,就产生了许多令人伤心的事例。本来花鼓戏就为社会上所歧视,演员的地位是很低的。戏院子里的真正后台是帝国主义,它虽未直接控制演员,却利用流氓来压迫演员。流氓经常来后台管演员,如遇演员稍有不恭顺的表现,流氓开口是骂,动手就打。尤其是天声茶园最历害,流氓硬是拿着鞭子在后台打演员。
每逢旧历初一、十五,戏班的规矩,要拈香烧黄表纸、磕头拜菩萨(拜的是唐明皇和老郎菩萨即二郎神),每逢年节还要做供菜。每逢这些节日拜完了泥菩萨后,还得去拜前台老板这位“活菩萨”,要到他家里给老板作揖,口称“恭喜!恭喜!”“老板发财!”如果演员不去拜老板,轻者挨骂,重者挨打。
更令人发指的是,对演员人格的侮辱。花鼓戏演员中原来没有一个女性,戏院里的老板,对花鼓戏演员,特别对唱旦角的演员,都要取上一个黄色的“艺名”,且含有女性、带歌妓的意味,如小宝宝,小官宝、小桂红、小桂仙等等。用这些手法招徕顾客。
当一个演员唱出了名,大受观众欢迎时,某个资本家如一旦看上了这个演员,就托前台老板,或其他流氓介绍,要演员去拜这个资本家为“干爹”。演员不能拒绝,否则,既得罪了大爷,又得罪了资本家,那就会招致许多麻烦,终致不能上演。认“千儿子”,要举行拜“干爹”仪式。设礼堂,铺红毡,点香烛,放鞭,行大礼,干儿子向于爹干妈磕头。大摆筵席,大宴宾客。表面看,资本家收年轻演员做“干儿子”,要个虚面子,与人谈起来,某某名演员是我的“干儿子”。说穿了,是藉年轻名演员的声誉来抬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扩大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以便更进一步地进行其投机倒把的活动。
资本家为了他的生意经,大流氓为了他的虚面子,时常在请客的时候,叫花鼓戏演员前去陪酒,当时这叫做“出堂”。出堂以唱旦角为主,唱外角的只起陪衬作用。在酒席前,资本家、流氓叫唱两句,就得唱两句。还得看大爷们的脸色行事。资本家、流氓说这是看得起某某演员,其实,这是对演员最大的侮辱。资本家的新店开张时,有时办“堂会”,也请花鼓戏演员去唱堂会戏。不过这样的场合,邀请汉戏的较多,花鼓戏参加的机会较少。这种“玩戏子”的行径,在当时竟成为资本家、流氓大爷们竞相仿效的时髦风气。
花鼓戏来源于民间,生命力是很崛强的,在千难万苦中,还是出现一批奋发图强、有作为的演员:如李百川、江秋屏、沈云咳,章炳炎、袁玉屏、陶古鹏等人,对花鼓戏进行改革,首先去掉帮腔,增胡琴伴奏,继而改折子戏为本子戏,把花鼓戏班改为“进化社”,提出拒绝唱点戏,不再受大爷们玩弄了。李百川有文化,可以自编剧本,自演主角。再如《蜜蜂计》一剧,就是袁玉屏从西安易俗社编的本子移植过来的。
楚剧定名与血花世界
一九二六年春,国共合作开始北伐,国民革命军十月间进驻武汉。武汉市成立了总工会,负责人是向忠发。当时武汉市的工
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组织起来了,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
这时,我们见到游行的队伍中,有下河的工人。在旧社会上对倒马桶的下河工人,视为“下贱”的,难道我们唱戏的,连下河工人也不如吗?他们受人欺负,我们同样也受人欺负。他们组织起来,加入了工会,我们唱戏的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申请加入工会呢?我就和李百川、江秋屏等人商议,一串连大家都同意,把花鼓戏演员组织起来,申请加入工会。当由李百川、江秋屏、陶古鹏等三人出面。请同行朱富全的儿子(忘其名)替我们写了一份申请书,由我们三人出名送呈。
由于花鼓戏长期遭到社会上的歧视,它的名声被反动统治阶级给糟踏臭了,需要给花鼓戏另改个名字,才容易批准。关于另起名字的任务,大家推我承担。我在考虑过程中,想起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李百川、章炳炎在上海演出时,曾用过“楚歌社”那个名字。花鼓戏是湖北的地方戏的一种,而湖北又是春秋、战国时楚国的疆土,就想把花鼓戏改名为“楚剧”。我同李百川等人商量,首先得到他们几个人的同意,再经串连酝酿又得到了全体同行的同意,就把“楚剧”的名字确定下来了。(关于“楚剧”名称,一般认为是傅心一提议的——编者)
我们申请的呈文送上后,很快就得到市总工会的批准。从此以后,我们楚剧界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全体演员光荣地列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
我们既然被批准参加工会,就立即建立组织。这时武汉市楚剧院子共有:天声;天仙和共和昇平楼等三家,演员总共有百十余人。当时大家都很穷,建立组织的没有开办费,还是张玉魂将自己的行头拿出来,交我去当铺当了二十四元银币做开办费。建立组织的第一步就是选举,选举结果,朱富全当选任市楚剧工会主席,王若愚任干事。
不久,又成立了市剧学总会,其中包括汉剧、话剧(文明戏)、楚剧、皮影戏等剧种,并在各剧种成立分会。分会下又设立小组,由汉剧的傅心一任市剧学总会主席。
我们参加工会、剧学总会后,参加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的游行示威运动。只要是工会领导的各种政治活动,我们也都参加了。
同年底,李之龙(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志接任新市场(现民众乐园)主任职务,负全面责任。他到任后即把新市场改为“血花世界”。血花世界是汉口综合性的、最大的一个民众娱乐场所。由于当时没有京戏,只有文明戏(话剧)、汉戏和扬州大鼓一双簧。文明戏最吃香,他们演的是时装戏,演员有刘艺舟、王无恐、章再鸣、红廷廷等。因经营不善;不到三个月,亏了几千元现洋,不得不暂时停业。但象血花世界这样娱乐场所,虽亏了本,也非继续开办不可。李之龙同志因此同游艺股股长何润泉和股员余鉴予商议,因何、余都是湖北沔阳人,都非常了解湖北的风俗、民情,认为花鼓戏最受广大民众的欢迎。也只有上演楚剧最能赚钱。由余鉴予的大力推荐,得到李之龙同志的同意,于是年腊月间,决定吸收楚剧进入血花世界上演。
经黄汉翔的介绍,我同余鉴予协议每月包银一千二百元。从一九二七年旧历正月初一起在血花世界开张演出,在二楼开辟了一个场子上演,日夜两场,场场客满。一个场子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又在四楼给楚剧加辟了一个场子,仍是场场客满。由李百川和陶古鹏排练的《吕蒙正赶斋》一剧上演,这个戏很受观众欢迎,越演越红。其他如访友、送友、告经承、大清官、讨学钱、浪子回头等戏,也是经常上演的主要节目,都很叫座。楚剧在租界里卖三百钱一个座,血花世界五百钱一张门票,看楚剧要另加二百钱,即一张楚剧票要卖七百钱。这样,唱了不到两个月,就扭亏为盈,把原亏的几千元赚回来了,另外,还有盈余。
由于演员的阵容强,能吸引观众,如当时已出名的旦角,就有李百川、张玉魂、余文君、江南容、江秋屏、沈云咳等人。老生有彭玉堂,小生有章炳炎、陶古鹏(兼演老生)等名角。法帝国主义及其控制的一伙流氓,见到楚剧跑出了租界茶园的牢笼,在血花世界大放异彩。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对楚剧展开了各种污蔑,破坏楚剧的声誉。他们在报纸上撰文,还印发大批传单,攻击楚剧“诲淫诲盗”,更有甚者,恶毒攻击李之龙同志,说什么李之龙当上了花鼓戏老板等等。其目的,无非是想把楚剧拖回租界里去,继续为其垄断、剥削而已。
李之龙同志看透了这些阴谋诡计,鼓励我们在血花世界好好演出。他认为楚剧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虽然楚剧中有些剧目,有的有毛病,个别演员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但这都是可以改正的,不能摧残。所以,李之龙同志一方面在报上撰文,为楚剧进行辩护,对诬蔑之词,进行反驳;另一方面,对楚剧进行改进,如为《吕蒙正赶斋》一剧改正一些唱词,把昆曲的《尼姑思凡》一剧移植到楚剧中来。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楚剧的大力支持和培养,楚剧得到了一时的解放。楚剧能到中国地界公开上演了。法帝国主义再也卡不住了。这样一来,武汉地区,除了法租界原有三家楚剧茶园外,在中国地界,一下子发展了十几家楚剧茶园,当时楚剧确是盛极一时。
宁汉合流中楚剧又遭挫折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宁汉分裂。有些学生到血花世界里来贴“打倒蒋介石”的标语和漫画。当时;血花世界的职员,对学生的这一举动,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支持的;一种是反对的。曾一度加以制止。可是学生不管这些,一次就把血花世界的主要墙壁上,贴满了反对蒋介石的标语。次日,李之龙同志来血花世界,见此情景,即向大家指示说不应该制止这一革命行动,更不应该撕毁标语。又过了几天,紧接着一些工人和一些学生都来血花世界开反蒋大会,指责蒋介石叛变革命。会后就上街游行示威。
这年七月,汪精卫叛变,宁汉合流。李之龙同志被蒋帮逼迫而离开了血花世界,国民党派来了黄坚、唐性天等来接管了血花世界。他们见楚剧有利可图,让楚剧继续在血花世界演了两个月,因他们对楚剧抱有偏见,终于把楚剧辞退。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武汉的帝国主义分子又抬了头。共和昇平楼、天声、天仙等茶园都复了业,恢复演出楚剧。共和昇平楼的前台老板是大流氓郑善生。事实上天声、天仙也均为郑善生控制。当然,郑善生又受法帝国主义的操纵。我们这个班离开血花世界后,只得各自回到法租界演唱。从此又陷入了法帝国主义控制的笼牢,又长期陷于受流氓、国民党反动派、报痞子的围攻之中。
这时,有个报痞子叫李齐明,见楚剧又到这个地步,正好藉此机会捞一把,来一个名利双收。于是他就向市教育局献策,开办楚剧演员训练班,进行“改人、改戏”。市教育局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委派他担任这个训练班的校长。他就把全市楚剧演员,不论年老的、少的一齐集拢来,开办了楚剧演员训练班。学费每人每月三元,共有三百多学员,他的收入就很可观了。训练期间,不准上演。训练班的课程有:文化、音乐、军事训练,三民主义教育等等。除此之外,就是整理剧本。
楚剧原来都是口头传授的,根本没有剧本。这次要整理剧本,由五、六个老演员一起,配一个有文化的,根据老演员口述纪录,整理出剧本来。确也整理出了一批剧本。
由于李齐明领导不力,学员中如王若愚之流又在搞撵走李齐明的活动。市教育局怕出乱子,就立即把训练班停办了。停办
后,演员仍各自回各的茶园照常上演。流氓、报痞子等人照常在报上撰写攻击楚剧演员的文章,虽由王若愚去与撰稿人送钱、说项,请其不再撰文攻击。但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共撤走,楚剧就失去了政治上的领导和庇护。又回复到被欺压凌辱的时代。
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市警察局说楚剧演员是由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把李石川、章炳炎和陶古鹏以及王若愚等人,先后抓去,押在总局的拘留所(今民生路后花楼街口),押了一个多月,始终没有讯问。反正我们既没有人说情,又没有钱行贿,只有硬坐牢。他们始终找不出我们的错处,后来只得把我们释放了。
到了同年的八、九月间,市社会局、教育局、警察局三方,为了迫害楚剧,联合出了一个小册子,把楚剧中的几个所谓的坏戏和演员,说得一踏糊涂,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就连爱看楚剧的观众,也被指责为不是好人。还不准楚剧演员在本市逗留,如有发现,当街逮捕。其实,租界上照常演唱楚剧。而这个小册子散播的恶劣影响,使在汉口非租界区的二、三百名楚剧演员失业,无家可归。
当时老圃游艺场(现江汉路老圃正街)的老板朱双云(演文明戏的好手)和京剧演员夏月润、潘月樵等非常同情我们,替我们奔走,向当时的反动当局请求,解决楚剧演员的失业问题,迅速开办训练班,改革剧目和演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开办训练班,由唐怡天负责主持。
唐是国民党派去接管血花世界的负责人之一,是最反对楚剧的。这次办训练班的目的,就是企图把楚剧彻底整垮。规定半年一班,一班四十人,汉口楚剧演员几百人,要都得到受训,才能在汉口立足上演。第一届楚剧演员训练班毕业后,由这批学员组织了“楚剧同学研究会”,毕了业的同学,一律都是会员。待受训的楚剧演员,是非会员,非会员不准上演。
训练班一共办了三届,三批训练,基本上把全市楚剧演员训练到了,从此准许我们在本市非租界地区上演了。在训练班的过程中,我们有两种态度,一是拒绝参加受训,如王若愚、殷殿坤等人。一是委屈求全的态度,参加受训,以陶古鹏等人为首。楚剧演员被训练了一遍,可以到处上演楚剧了。虽不再有被禁演的事,但仍有很多报痞子,还是继续在报上撰文攻击楚剧。其目的仍在向楚剧演员敲竹杠,应付不完,攻击不止。
一九三二年,几位热爱楚剧的朋友,李相武、余鉴予、王觉等,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工作同志,他们都认为楚剧至今还是个浮萍,在社会上没有扎下根,很容易受人歧视和欺侮,应设法在社会上争取一定的地位。我们四人商议,决定出一本《楚剧概言》,由我口述,请李相武执笔。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这本书。叙述了楚剧的起源、发展经过。约有几万字。此书自己出钱印了两千多册,分送各省、市文教部门,为楚剧扩大宣传。
楚剧参加抗日宜传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驻在武汉,郭沫若同志任第三厅厅长。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在汉口工作。当时号召文艺界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楚剧界由王若愚、殷殿坤、陶古鹏负责并与第三厅联系。曾在一次集会上,由楚剧公会邀请周恩来、郭沫若、田汉、洪琛等领导同志莅临大会指导。
周恩来同志给我们作了《加强团结,共同抗日》的指示。会上由我向周恩来同志递送了《楚剧概言》一书三十册,并请随给予批评帮助。
第三厅为了对戏剧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于一九三八年二月间成立了戏剧界人员讲习班。在汉的各个剧种的每个演员都参加
学习。汉剧、楚剧的演员共有三、四百人,白天参加学习,夜晚照常演出。
通过学习,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认识了当时中华民族的危机,大敌当前,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认识提高了,演员的政治思想面貌一新。过去艺人之间,剧团之间,剧种之间,普遍存在一些相互攻击,相互轻视的形态。现在改变为彼此更加关怀和亲密了。
第三厅为了加强抗日宣传救亡工作,在我们讲习班结业后,组织了政治工作宣传队。在汉的各个剧种、剧团都派了大批演员参加,通过戏剧这个形式,加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楚剧成立了三、四个宣传队,有二百多人参加,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至翌年九月间,武汉沦陷前,先在武汉地区演唱。随后服从三厅指挥,跟随三厅到当时大后方的湖南、重庆等处演唱。随楚剧团后方去工作的,名老演员中有:沈云陈、江秋屏、王若愚、张玉魂、徐俗文、黄汉翔、匡伯林、李金和、姚小中,青年演员中有:袁壁玉、熊剑啸、张美玉、陈梅村、冯雅兰、黄楚材等一批强大的队伍。在艰难的岁月里,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功勋。
在武汉沦陷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武汉沦陷,这时楚剧演员都纷纷下乡逃难。如李百川、严兰芳、余文君、江南容、张桂芳、陶古鹏等都下乡了。有的去黄陂、孝感乡间搭班演唱,有的·回阳逻闲住。
同年腊月间,城里的秩序渐趋安全,我回武汉来了。武汉沦陷前,我在新市场演出,此进城后,先到新市场先摸摸情况。原来亚细亚杂技团老板王文明,这时当上了新市场的汉奸老板。王文明见我回来了,立即找王春祥、徐小哈和我商议,要我们赶快组织班子,在新市场上演。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也就演唱起来了。
上演不久,汉奸侦缉队扬言,武汉楚剧演员都是共产党田汉的学生,;他们都参加过抗日宣传队的工作,要捉我们。因此,我们只好躲在院子里演戏,不敢出大门一步。虽然天天演戏,只给大锅饭吃,没有工资。演两个多月以后,才给起薪,但也给不了几文钱。其实所谓要捉拿我们,是王文明耍的花招,我们白白地给王文明唱了两个月的戏。
日寇侵占武汉后,把米和盐都统起来了,按口分配,新市场全体演职员的米和盐,都由亚细亚杂技团管理发放。王文明从中慰扣斤两。如有人反对这种剥削,他们就进行刁难,打耳光,踢一脚,骂几句,这都是极平常的事。后来发展到杂技团的人大打楚剧演员,虽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晚还得演戏。
随着新市场的开放,法租界的天仙舞台、永乐茶园也先后开演了。李百川、章炳炎、李文卿、关啸彬、王砚云等人都到永乐茶园演唱,生意尚好。李百川等人,也同样地受到汉奸侦缉队的迫害,罪名同我们的一样。汉剧演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李百川为了泄愤,在唱词中,经常用指桑骂槐的方法,加些字眼,骂日寇,斥汉奸。
武汉沦陷期间,武汉的楚剧没有公会,各剧院的前台老板,都是日寇的翻译。计难民区有:永乐茶园、满春茶园、美成茶园。法租界有:天仙茶园。华清街有宁汉茶园。大智门有大智舞台。武昌有和平剧场、乃园茶园。震寰纱厂附近有一楚剧场所 (忘其名)。
每个剧院,从卖得的票价中,先抽百分之十的经理费,再抽百分之十的交际费,下剩的三、七分帐,前台老板三成(包括房租水电费),全体演员得七成。实际上,前台老板得五成,全体演员得五成。这时演员的日子很不好过。很多演员分的钱,不能维持生活。如生意不好,生活更难维持。本不想继续唱,但不唱更无办法。
演员不仅受其残酷的剥削,还受其严重的压迫。我因在新市场挨了汉奸老板的打,一气离开了新市场,到满春茶园演唱。这时满春茶园的阵容:唱老生的有涂喜堂、李协成,唱花旦的有彭如玉,唱青衣的有左受梅,唱小生的有我和我的徒弟钟惠然。唱丑角的有徐小哈和钱德生。在这里还是挨汉奸老板的打,受他的气。
那时,钱德生还是个小孩,有一次,被前台汉奸老板先毒打了一顿,打完了,又把他提起来,狠狠地往地下一摔,几乎被摔死。
一九四四年冬,我向前台老板日寇翻译徐维善请假回乡探亲,他不准假。我要求说:“叫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就什么时候回来”。他见我定要请假,就故意找了我个错,说我这话不对。那时我两人对坐,他说完上句话后,拿起茶杯将茶水泼我一脸,接着打我一耳光。我当时实在忍无可忍,我就振臂一呼,几个演员一齐拥上。汉奸见我们要还手了,也就泄了气,不敢那么嚣张!
演员受尽汉奸老板的剥削和压迫,不仅生活艰苦,死后还无钱安葬。花旦名演员江南容,死在满春茶园的后台,不能发丧,还是由演员凑钱给他买棺材埋葬的。名青衣演员张桂芳在美成戏院演唱,贫病交加,住在后台,老板怕他死在那里受牵累,雇人抬回乡去,未至家,死在路上,也是连棺材也没有,随即埋在路旁。
日寇投降到解放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当时我在天声茶园演唱。天声的前台老板是杨寡妇,她丈夫原是汉奸侦缉。虽然抗战胜利了,汉奸在蒋帮庇护下,逍遥法外,汉奸的老婆杨寡妇仍可照常当老板。当时,姚玉春、陶德安、张玉魂、张云霞等人,亦都在这家院子里演唱。杨寡妇为人毒辣,连演员的人身自由,都被这个女流氓控制了。天声对面是天仙,天仙的前台老板是周老九,是个大流氓。周老九想挖陶德安去天仙演唱,陶德安也想离开天声去天仙。为此,陶向扬寡妇磋商,杨寡妇不但不听,开口就骂,举手打了陶两耳光。打了,还是不准走,并且还得继续唱下去。楚剧名青衣演员姚玉春(即灵芝草先唱青衣后改唱小生)也在天声演唱,因分不到几个钱,贫病交加,后来死在后台,杨寡妇不理会,还是由我们演员凑钱埋葬。
为了把楚剧界的演员,团结起来,抵抗国民党官员和流氓的迫害,我同殷殿坤、章炳炎等人建议,恢复楚剧公会,具文呈送当时的汉口市政府,但拖了三、四个月没有下文。后来,章炳炎和彭秀山把我写的《楚剧概言》送去才获批准。恢复后的楚剧公会,设在汉口旧府街大陆里,选出段殿坤为主席,我为副主席。给楚剧演员的联系交往和增进相互了解,作了一些工作;并组织人员,整理了一些剧本。
一九四九年五月武汉解放,二十年前由中国共产党所关心、扶持的楚剧,才真正获得新生,从此进入兴盛繁荣时期。
(1966年4月遗作,市案档馆供稿,汪正本编整))

陶古鹏(1896—1970)湖北新洲(今武汉市新洲区)人,本名陶德金,工小生,1919年进汉口法租界春仙舞台,以《当铺认母》、《董永分别》成名,塑造余成龙、吕蒙正、梁山伯等个性鲜明的角色,首用胡琴伴奏《白扇记》,首演据外国名著改编的楚剧《费公智自杀》、《父之归家》,是楚剧以生行挂头牌的第一人。1927年与李百川率班进“血花世界”公演。述录《楚剧概言》,撰有《楚剧演员生活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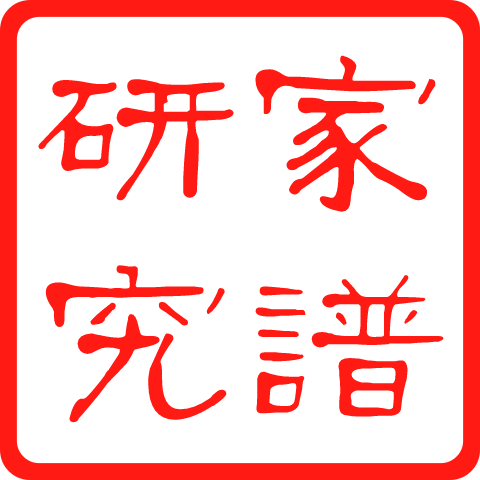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