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陈伯华(汉剧)荣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奖一等奖、主演汉剧《宇宙锋》荣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奖二等奖【人民日报 1952-11-16 第1版 】
1960年秋,周总理备下家宴,邀请参加全国旦角名演员讲习班的陈伯华和袁雪芬、红线女到家中做客。总理对陈伯华说,“汉剧源远流长,对京剧和许多剧种都有过很大的影响。全国13个省有汉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有发展前途的。”
1962年1月,湖北省建立了以陈伯华为院长的武汉汉剧院。武汉汉剧院的建立,使全国汉剧有了一个艺术中心,对促进和推动全国汉剧艺术的发展起了深远影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自题词:“各地名剧种,传人须养成。京昆登大雅,秦越奏清平,尊重吴陈派,宏宣江汉声。根深人群众,生命力藩荣。”这里提到的陈派的创始人就是大家熟悉的陈伯华大师,而吴派的创始人就是“三生大王”吴天保。
1988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陈伯华 “汉剧艺术大师”称号。
1999年,陈伯华80华诞和舞台生活70年,中央以及省、市政府再次为她隆重贺寿,并授予她“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
2004年,陈伯华荣获中国文联荣誉委员金质奖章。
2006年,汉剧被国务院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陈伯华名列文化部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忆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
陈伯华
《穆桂英智破天门阵》陈伯华饰穆桂英(1950年代)
1949年,武汉解放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不断传来。听说梅兰芳、周信芳由上海北上,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听说周总理在北京亲自去访问了程砚秋;又听说文化部找到了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刘喜奎,聘请她担任了戏校的老师,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亲自向她以及参加戏曲工作会议的代表们祝福;听说……这一切就像和煦的春风复苏了我儿乎泯灭了的希望。我再也按捺不住了,便常常独自混迹于观众之中进出汉剧的戏院,确乎着到了汉剧复兴的征兆。旧时的姐妹们也突然都在武汉出现,并活跃在舞台上。她们的演出,不仅一扫过去那种令人难堪和心碎的乌烟瘴气,而且跳动着一种生机盎然的朝气,我依稀回到了少年时代,和大家一样去追回那逝去的青春。
1936年,我17岁结婚,息影舞台。我丈夫刘菊林,又名刘骥,提起他,人们就可以脱口而出说他是“大军阀”、“大资本家”。是的,他早年留学日本,在士官学校毕业后,又进入陆军大学,回国后在冯玉祥手下当参谋长,曾在中原大地指挥过几十万大军作战,他能贴着马肚子双手开枪。后来,他不满蒋军的倾轧,便弃军从商,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办起了商行。他家中有位夫人,终年躺在病床上。他常年在外,奔波于各大城市,操劳商务,虽腰缠万贯,富贵之极,但生活却异常孤寂。
在汉口总商行的一次宴会上,他无意中听到常客刘玉堂和同行在议论“筱牡丹花”(我的艺名)的失恋,当晚就来看我的演出,从此他几乎成了我家的座上客。他比我大31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合适的夫妻。他说:“你是绝对自由的。今后你要是看中了哪个男的,找可以把你当妹妹、当女儿嫁出去。”
婚后,我丈夫带着我漫游了全国著名的大城市,那奢侈的大饭店、豪华的夜总会以及那灯红酒绿的游宴、纸醉金迷的生活,都没有使我感兴趣。相反,有时当我一直处于似乎是无休止的官场应酬中,或是一连几小时站在丈夫身旁与别人握手、微笑,或闲聊、打牌时,我就会因无聊、空虚而缅怀我自己的艺术,甚至痛苦得晚上哭湿枕头。
陈伯华(青年)1937年在上海,与俄国教师合影
后来,我丈夫不再强求我周旋于应酬和玩乐之中。我刻意揣摩了各种地方戏曲,欣赏了文学、美术、民歌、说唱等艺术品种,观摩了大量的西方著名影片,从中受到启发。我爱卓别林的电影,感到他入戏很快,就特别注意学习他的技巧;我看了《魂断蓝桥》,就反复揣摩影片中女主人公那三次准确传神面有层次的眼神运用。另外像《铸情》、《蝴蝶梦》等,每部片子我都看了不下20次。我喜欢赵丹、阮玲玉等人真切自然而有个性特点的表演。同时,我又受丈夫的影响,欣赏了西洋歌剧和歌曲,以及西方油画、雕塑。在家中,我丈夫又为我请了白俄专家教我弹钢琴,学跳俄罗斯芭蕾舞。正是这一时期对中西方艺术的基本了解给了我以后的艺术以极大的帮助和借鉴。
陈伯华与梅兰芳
陈伯华与梅兰芳
更使我高兴的是,我在上海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与他长期切磋艺术。这位“良师益友”庄重华丽、自然大方的唱腔和表演给了我极大的影响。一次梅兰芳在青岛演出,为了能多看一次他的精采表演,我丈夫不惜让我坐火车到上海,又从上海乘飞机至青岛,匆匆“赶场”。我从名家的演出中受到陶醉,也受到感召和启迪。正象一株饱含乳汁的牡丹,含苞欲放。一种有意识的极为强烈的创作欲在心中升腾。开始,我低吟浅唱,手舞足蹈,还有所顾虑,渐渐地就不能自持。为了追求艺术上至善至美的境界,我将楼上楼下的所有镜子集中于卧室,对着镜子练身段表演。有时,我一个人扮演一台戏的全部角色,沉浸在艺术创造的境界之中。有一次,我到梅先生家作客,谈笑间,我即兴演唱了一段京剧《凤还巢》。正好梅先生从外进来,一进厅便兴奋地说:“你这是梅派!”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我是陈派!”梅先生惊异地问:“程派(指程现秋)?”我笑道:“我说我是陈伯华的陈派。”我的话引来一片友好的笑声。虽然这是一时兴之所致的玩笑,但我这时已在锐意追求唱腔中的流畅与华丽的意境,表演上典雅、细腻、纯情的风格。真没想到,新中国刚成立,我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一种创作的欲望情不自禁地社我心中勃发。于是,我请出师兄刘顺娥帮我整理刘本玉师父教授的旧课,又请出了化妆师徐福林,琴师刘志雄等,为自己重返汉剧舞台作了准备。
1950年,军代表接见汉剧演员陈伯华、王晓楼。
正巧1951年武汉为抗美援朝举行义演,我在旧时姐妹们的热情推操下也参加了演出。记得当时我演了《断桥》、《打花鼓》和《四郎探母》等剧目,没想到竟得到了中南行政区的领导李先念、王任重、陈荒煤等同志以及群众的赏识。嗣后,有人劝我参加汉剧团,又有人劝我弃汉从京。他们好心地说:“汉剧太古老了,已经走向没落,京剧还是时兴的,具有巨大的影响,要是你改弦易辙去演京剧的话,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甚至还有人建议我到北京去拜在王瑶卿的门下。
他们认为,凭着我幼时的功底和现在的艺术修养,如果再冠上“瑶卿弟子”的头衔,是不难在京剧舞台上震响一声春雷,并以一颗新星的姿态而涌现出来的。的确,我喜爱京剧,也熟悉京剧,去演京剧也许会获得一定成功。但是我更爱汉剧,我的全部感情早已注入和溶化在汉剧里了,简直有点不能自拔。当然,刘菊林当时的一席话也深深影响了我。他说:“你去演京剧,纵然拜在王瑶卿门下(这是有可能的),一时也难与京剧‘四大名旦”并驾并驱,势必要落在他们之后,而演汉剧,除了董瑶阶这些老前辈以外,凭着你的资历和水平还可以独占鳖头,有望扛起汉剧复兴这面大旗的。汉剧之首总比京剧之末要有影响。”刘菊林的这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也确有远见。
就这样,我参加了当时的汉剧一团,其前身为汉剧抗敌流动宣传队一队,团长是吴天保。我们除了演些《玉堂春》、《四郎探母》之外,还排演过《牛郎织女》这一类新戏,但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直到1952年夏天,中南区举行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崔鬼同志担任了我主演的《宇宙锋》的导演,我才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也才认识到“推陈出新”这个方针对于戏曲革新的重要性,懂得了一个好演员应该怎样去创造角色,体会到一个演员的根本任务是演人物而不只是演戏的许多道理。
为了准备参加中南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我曾排了《打花鼓》和《宇宙锋》。《打花鼓》是和李罗克同志合演的,《宇宙锋》则由张春堂、王子林、万仙霞和我合演。帮助导演的入很多。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同志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后,果断地作出决定:由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兼中南文艺学院院长崔鬼同志担任导演,让我集中排演《宇宙锋》;《打花鼓》由李罗克和玲牡丹合演;汉剧的吴天保和楚剧的李雅樵合演《战樊城》。
戏曲界过去虽没有导演这个名称,但我认为它还是有导演的。传统剧目经过老师逐字逐句的传授,对每个场面、身段、动作做出有一定尺寸的指点,事实上这些便是导演作业。不过这种作业不光出自老师一人,它首先是继承了前人的创作成果,又经过长期的扬弃和积聚才慢慢地形成的。这就是我们习惯叫做“说戏”的那种方式。当然这是比较粗糙的,也不够完善,特别是这种方式缺乏对演员的启发和诱导,不能指引他们去创造角色。大凡有成就的演员,由于他们能大胆突破而有所创新,因此以往虽没有导演,确也演出过不少好戏,这是事实。但是要在20世纪中实现对古老戏曲的革新,那种传统的“说戏”方式就不能再适应了,必须相应地建立科学的导演制度。
崔嵬同志是50年代初期为戏曲导演制的开创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一位新文艺工作者,也是我平生接触到的第一位正规的导演,同时还是帮助我走上创作之路的良师益友。
最初,我以为崔嵬虽是话剧名家,但对戏曲可能不太了解。后来才发现他不仅热爱戏曲,而且还相当熟悉。我曾听说,在话剧界导演要求演员都写角色自传,演员则要求导演讲解剧本的主题思想。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鲜事物,准备从头学起。不料崔见下排练场以后,连一点“新”措施都没有,只是要我按全剧再走一遍台,他象个普通观众那样趣味盎然地看得十分入神。看完后,他就逐段逐节、逐字逐句地和我们讨论。例如〔引子〕中的“暗悲啼”三字,唱词中的“烈女传”一词,他都认为不妥。他说,既然是暗自悲伤,必然有不敢让人知道的苦衷,那就不能用表示放声大哭的“啼”字,而只能用饮泣吞声或泣不成声的“泣”字;他又指出,《烈女传》是汉朝人写的,秦代的妇女不可能读到。这可以说都是对传统剧目中存在的疑难杂症的“诊断”。我们文化水平和历史知识都贫乏的戏曲演员,当然欢迎这种“治疗”。接着他又和我谈起了民国初年汉剧在北京演出时,很受行家们的重视和欢迎,但是有人对《金殿装疯》这折戏却提出了批评,认为把赵女演得和真疯一样,那就不是装了。我和他交换意见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父亲和皇帝,赵女应该演得象个真疯子,切不能让他们看出你丝毫破绽;但面对乳娘则还是个正常的人,这样才能告诉观众,她是在装疯。老崔非常欣赏我的见解,然而他又不客气地指出:这种正常人的精神状态,在我的演出中虽和乳娘有过交流,但只是偶尔一闪现,并没有让它贯穿于全剧的始终,因而还是自然主义的表现方法,并没有进入艺术创造。这几句话击中了我的要害,使我感到导演的作用和权威性。
使我最为心折的是金殿装疯后老崔安排的最后一节戏。当秦二世说“赶了下去”时,危险虽已过去,赵艳容亦气尽力微,然而还没有真正脱险,她还得挣扎着保持疯癫的状态,踉踉跄跄地走下御阶。这时乳娘迎面走来,赵艳容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声哀号,全身扑过去,几乎瘫倒在她身上,再由乳娘搀扶下场。仅仅这一个动作,就能赢得观众鼻子发酸。这要导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才能产生这样的舞台艺术魅力。崔嵬没有要求我写角色自传,也没有专门讲主题思想,但这些问题我却在创作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弄明白了。
陈伯华
《宇宙锋》是汉剧正旦的看家戏,是由刘本玉老师的得意弟子、我的师兄刘顺娥帮助我恢复的。排练不等于导演,他只是按照当年师傅传授给他的路子如实地重复一遍,基本上还是李彩云老师的路子,我也只是对汉剧〔反二黄〕的唱腔在琴师刘志雄的协助下作了点翻的尝试,至多可以说是对传统的补充,谈不上什么创造。而在崔鬼导演下,我的排演却是个创造。凡是看过我演出的人,都觉得这出戏既不同于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又有别于李彩云先生的《宇宙锋》,有着自己的风格和个性。而这风格和个性却是崔嵬同志所给予我的。
正是由于这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中南区代表团选派的剧目中就有汉剧《宇宙锋》。汉剧《宇宙锋》和桂剧尹羲演出的《拾玉镯》在赴京前曾引起过一番议论。有人认为京剧《宇宙锋》是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而《拾玉镯》是小花旦的开蒙戏,中南区的两位知名演员这么两个剧目,岂非班门弄斧?其实中南区代表团挑选剧目的工作是够慎重的,之所以选了这两出戏,正是为了展示我们对于戏曲“推陈出新”方针的理解和为此而所做出的成绩。
会演结束时,这两出戏都获得了表演一等奖。我记得那是1952年10月的一天,我们在北京演出,台下坐着评委,其中有德高望重的京剧“通天教主”王瑶卿和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四大名旦”,我心中感到少有的胆怯。但崔嵬同志很沉着,他不断地鼓励我,并显得信心十足。戏果然打响了,是热烈的掌声使我惊醒,我谢完幕刚回后台,便看见梅先生满脸含笑地匆匆走来,亲切地祝贺我演出成功,并说:“你是陈派。”没想到当年在他家一时的玩笑话,他还牢记在心,并热情地给予肯定和鼓励。他还说王瑶卿老先生是轻易不夸奖人的,尤其对京剧的代表剧目《宇宙锋》,他从未对梅一人以外的人给予任何青睐。然而这次他也首肯了,认为汉剧的确有特色,有许多长处。梅先生还真诚而谦虚地说:“我要向你学习。”这无异于给我最高的奖赏和鼓励。
《宇宙锋》演出的成功,给中南区代表团带来了欢乐和荣誉。我们接着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汇报演出,刘副主席、周总理、陈老总、贺老总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周总理还特地和我们合影留念,并亲自到代表团驻地看望我们。对周总理的平易近人我早有所闻,而真正
认识并感受到他的关怀,则是从《宇宙锋》在京演出开始的。当时天很冷,周总理叫政务院的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棉大衣,并亲切地对我说:“你是汉剧的后起之秀,要一代超过一代。”
全国会演闭幕后,大会决定崔嵬同志仍以中南戏曲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带领我们在华北、华东、中南诸大城市作巡回演出,以扩大影响,直到1953年春天巡回演出才结束。
作者系武汉市政协第五居、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黄靖、邓家琪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 总第四十九、五十辑
陈伯华(1919.3-2015.1.30),艺名筱牡丹花,女,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大师,湖北武汉人。8岁入汉剧新化女科班,工四旦和八贴,曾用艺名新化钗、小牡丹花。由于陈伯华在汉剧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她的名字已经和汉剧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她主演的《二度梅》、《宇宙锋》和《柜中缘》早已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她在表演上突破了正旦与贴旦的界限,首创新的角色行当。她着力钻研京剧的梅派、程派表演艺术,广泛借鉴其他艺术形式,终于形成自己华美清新、细腻醇厚的陈派表演和唱腔艺术。在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以一出《宇宙锋》艺惊四座。她在继承先辈艺术家李彩云的表演技巧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梅兰芳先生扮演赵艳蓉的人物基调,经过融化,塑造了一个既有别于李彩云,又有别于梅先生所创造的赵艳蓉的典型形象。她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剧情所规定的艺术境界融为一体:表演层层递进,张力适度,规范娴熟,极富个性。艺术大师梅兰芳说:“祝贺你,也谢谢你为我们带来了好戏,您是陈派,陈伯华的陈派!您的《宇宙锋》有特色,演得好,是汉剧的东西。”
陈伯华的演唱华丽婉转,细腻精致,无论是叙事与抒情总善于以浓抹手法精雕细刻,有如工笔重彩,给人以勾勒纤细、色泽鲜艳的感觉。此外,她在表演中对手和眼的运用别具一格,自成系统。
她师从刘本玉,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13岁独立演出,并以甜润柔美的歌喉,优美清新的表演,娇美动人的扮相脱颖而出,倾倒无数观众。她广为涉猎中外名著,广采博收,集众家专长于一身。她向俄籍教师学音乐,唱咏叹调,她学芭蕾舞、学弹钢琴、听西洋歌剧、欣赏世界名画,古典文学和西方艺术样式的熏陶,使陈伯华得到了多种营养。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她意识到手和眼对刻画人物、表现剧情、展示形象的独特性。经过数十年的苦练,她终于练就了一双柔弱无骨、变化多端的手,在表现人物的心态时,传神达意,准确生动。《二度梅》是陈派艺术重要的代表剧目之一,无论表演还是唱腔,都有很大的革新创造,标志着陈派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她在表演上融进了繁重的刀马旦应工的身段,舞蹈华丽典雅,唱腔细腻深沉。陈伯华代表剧目有:《柜中缘》、《状元媒》、《贵妃醉酒》、《秦香莲》、《三请樊梨花》、《断桥》、《二度梅》、《穆桂英智破天门阵》、《写状》、《宇宙锋》等。她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剧协理事、武汉政协副主席、剧协湖北分会顾问、武汉汉剧院名誉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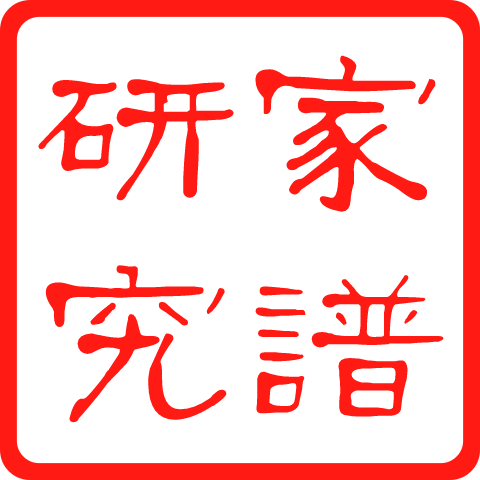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