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佛陀波利来到五台山 莫高窟第217窟·盛唐
唐代开始,多流传文殊化现老人之事。简称文殊老人,其中经典的例子就是佛陀波利唐高宗仪凤二年年在五台山南思阳岭遇到文殊为口吐“婆罗门语”的老人样貌呈现。内容大致说,北印度有一位佛陀波利,不远万里到五台山礼拜文殊道场,在途中遇到了文殊菩萨化身的老人,最终得到文殊菩萨的开示。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中记载: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者。婆罗门僧佛陀波利,仪凤元年从西国来至此汉土,到五台山次,遂五体投地向山顶礼曰……礼已举首,忽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遂作婆罗门语谓僧曰……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生一切恶业,未知法师颇将此经来不。僧报言曰,贫道直来礼谒不将经来。老人言,既不将经来空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得识,师可却向西国取此经,将来流传汉土……举头之顷忽不见老人。其僧惊愕,倍更虔心,系念倾诚,回还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文殊所化应的老人,即称文殊老人。在艺术表现上,则体现在所谓的新样文殊的模式中。
莫高窟第220窟同光三年(925)文殊图像题名有“敬画新样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一躯并侍从”字样,故被学者称新样文殊。学者对文殊尊像图式有一个界定:“三尊像”有文殊菩萨、于阗王和善财童子。“四尊像”在其基础上加入文殊老人,“五尊像”又加入佛陀波利。也就是说,在新样文殊的图式中,四尊像的模式中有了一个老叟形象文殊老人,五尊像中有了两个老叟形象,一个文殊老人,也叫圣老人,一个则是中土形象化了的梵僧佛陀波利。
此种图式可追溯到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主持修建的功德窟第61窟五台山化现图,图中出现了文殊化老人故事,故事分别在图中表现的西台和北台的右面,代表佛陀波利两次登山。两个画面旁边均有榜题:“佛陀波利从罽宾国来寻台峰,遂见文殊化老人身,路问其由”,“佛陀波利见文殊化老人身,问西国之梵”
《宋高僧传》载云,窥基曾“行至太原传法,三车自随。前乘经论箱帙,中乘自御,后乘家妓女仆食馔。于路间遇一老父,问乘何人。对曰:家属。父曰:知法甚精,携家属偕,恐不称教。基闻之,顿悔前非,翛然独往。老父则文殊菩萨也”。《广清凉传》中,雁门驽僧牛云遍巡台顶祈聪明事中,牛云在东台和北台顶两次见到文殊化现老人。
《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中对文殊化现的描绘就是:文殊大菩萨,不舍大悲愿。变身为童真,或冠或露体。或处小儿丛,游戏邑聚落。或作贫穷人,衰形为老状。亦现饥寒苦,巡行坊市尘。



见贾子萱文章插图
榆林窟第19窟西壁南侧的文殊变,右上角画出一白衣老人拄杖而行,前有一僧人合十礼拜,内容与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一致。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佛陀波利遇文殊老人莫高窟第217窟·盛唐


由此,从文殊新样开端的范式中,多存在两个老叟的图形,一个是文殊老人,一个是佛陀波利。一个是宣法者,一个是问道者。
在下图所示敦煌藏经洞白描画中,文殊画样出现了两个老人,右侧风帽持杖者,乃文殊化身的文殊老人,左侧合掌露顶的持杖老叟,则是佛陀波利。此即新样问殊图形中所谓的双老人的五尊式。文殊老人图像中两个持杖老人的要素的特点,也使得水神庙“千里行径图”壁画中两个持杖老人要素,似乎有了某种着落。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白描画稿现藏法国图书馆

本画中分别画有骑狮的文殊菩萨、驭狮人于阗国王、善财童子、佛陀波利和圣老人。画面左侧上部,文殊像前略上方画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佛陀波利作老年胡僧形,长眉,身着紧身短袍衫衣,裹腿,作远行状,右肩挂一斗笠,腰间拴一瓶子,胸前一拐杖,屈臂,双手合十,面对文殊老人作礼谒问询状。文殊老人戴风帽,身着长袍衫,长须,端立,屈臂,右手作姿,左手执一拐杖,作与佛陀波利讲话状。


见贾子萱文章插图

西夏《文殊变》壁画中的文殊老人
文殊老人与祈雨
假设我们大胆猜测水神庙中所谓《千里行径图》中的双持杖老翁可能是文殊老人,那么,文殊老人与水神庙壁画的重大主题祈雨要素是否有关呢?
既然我们假设水神庙中的壁画,多为祈雨的系统,都遵循交感媒介的功能,那么,假设本画面中可能为文殊老人,第一、这与祈雨又有什么关系呢?第二,文殊道场就在同为山西的五台山,这里是霍山,两者有什么关联呢?第三,对面壁画上画着西方三圣,这里假设是文殊,会如何协同?

一、文殊与祈雨
文殊菩萨道场是五台山,而龙神是五台山神圣空间中常见的显圣者,最初多以“毒龙”的形式出现,后来被文殊降伏,南朝梁法云所撰《法华经义记》中阐述“文殊则是往古诸佛龙种如来”。
隋时舍那掘多和笈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的《见宝塔品》和《安乐行品》中,也有文殊师利由龙宫中来,在龙宫中说法,以及龙女闻法得道的情节。
唐代大历七年,唐代宗回复不空请求在全国寺内均设置文殊院的诏书中说:“大圣文殊久登正觉,拯生人于三界,镇毒龙于五峰,慈悲道深,弘济功远”。
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介绍,五台山北台顶“南头有龙堂,堂内有池,其水深黑,满堂澄潭。分其一堂为三隔,中间是龙王宫。临池水上置龙王像,池上造桥,过至龙王座前。此乃五台五百毒龙之王,每台各有一百毒龙,皆以此龙王为君主。此龙王及民,被文殊降伏归依,不敢行恶。”
《太平御览》也说五台山北台是文殊镇压毒龙之所。五台山流传的众多龙神传说也聚焦了这一点。而大家知道,毒龙不仅有佛法上的抽象象征含义,比如僧肇《注维摩诘经》卷二就曾经对“毒龙”解释为“毒龙,恶道也”。但是,龙神本身又无疑是呼风唤雨的降雨主尊。
据唐初慧祥所撰《古清凉传》记载,总章二年四月,慧祥与河北僧尼道俗六十余人奉舍利石函像塑等往北台安置。其中有一尼僧在中台太华池中见有大龙围绕太华池中大树。圆仁在巡礼五台山时也记录了中台北台“龙池”与“龙堂”的供养情况,五代时期所造敦煌61窟“五台山图”中多有“大毒龙二百五十云”及龙王图像。见下图所示:

宋乾符四年(877)栖复所撰《法华经玄赞要集》对窥基法师的《法华玄赞》做了注解,其中提到文殊在五台山神迹说,文殊菩萨为“三世诸佛第一辅臣”,专居五台山的原因有两个:“一降伏毒龙,谓彼山中多有毒龙,恼害众生,由是世尊遣来作镇。二者,缘此界众生爱乐大乘,于此密化四众,常说大乘,实久成佛,示为菩萨”。
八世纪中期李邕所撰的《清凉寺碑》中就多次化用“文殊镇压毒龙”的典故。碑中记述道:“上尊王演正法,降毒龙,在清凉之山“,碑文末尾作者作歌曰“天作五山兮实曰五台,台上出泉兮有龙为灾,大圣煦妪兮戢毒徘徊,西南其刹兮赫赫枚枚,翠微之上兮崒崫崔嵬,金容月满兮宝座莲开,祈我圣皇兮其至矣哉,以感以通兮为祉为福,前际后际兮无去无来”。
五台山有毒龙,文殊则是往古诸佛龙种如来,专治恶龙,驾驭了毒龙,自然就能按时遵序降雨,风调雨顺。怪不得唐代段成式在所撰《寂照和尚碑》中说,“清凉山曼殊大士是司鳞长,游之不诚,必有疾雷烈风”。也就是说,文殊是龙神统领,驾驭毒龙产生疾雷烈风,既然有了疾雷烈风,那么,丰沛的降雨也就是一种必然的值得期待的水到渠成的成果了。
唐代佚名笔记小说《大唐传载》中载有一则毒龙故事:
五台山北台下有青龙池,约二亩已来,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每至盛午,昏雾暂开。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观。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电风雨当时大作,如近池必为毒气所吸,逡巡而没。
这个记载非常有意思,他是说五台山的青龙池中有五百毒龙,和尚与有道居士可以观看,所谓的可以观看,就是看了没事,看了也很平静,但是假如尼姑或者妇女靠近,那么青龙池就会雷电交加,风雨大作。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上次我们阐述的古代祈雨仪式中,女性作为阴物的特征,去引导作为极阳之物的龙王,从而交感产生阴阳和合,从而下雨的逻辑路径,从这个角度,五台山的龙王,龙池,正是降雨的总控机关。


敦煌《五台山赞》中多次提及文殊菩萨,甲类S5573(底本)中记载:
佛子道场屈请暂时间,志心听赞五台山。毒龙雨降为大海,文殊镇压不能翻。佛子清凉寺里遍山崖,千重楼阁万重开。文殊菩萨声赞叹,恰似云中化出来。
《五台山赞》中的:“毒龙雨降为大海,文殊镇压不能翻”、“毒龙雨降为大海,大圣文殊镇五台”、“狮子一吼三千界,五百毒龙心胆摧”。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敦煌文献中还有诸如:“北台顶上有龙宫,雷声曲震裂山林。娑伽罗龙王宫里坐,小龙护法使雷风。五百神龙朝月殿,十千菩萨住灵台”的资料。
要知道,五台山(即清凉山)是文殊菩萨道场,和华严宗有密切关系。《大方广佛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第三十二记载:
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
而清凉山的清凉两字,也被中土社会加以运用阐发。在中土观念中,既然山岳神灵的主要功能是求雨和祈福禳灾,那么五台山又岂能例外。传说中就有古代五台山气候异常恶劣寸草不生,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在此传教的文殊菩萨得知此事后,到龙王那里借来了歇龙石安置于此,五台山立刻变成一个清凉无比的地方的传说。这条山谷命名为清凉谷,北魏年间在此建了一座寺院,取名叫清凉寺。以后,文殊菩萨经常在石头上讲经说法。
《古清凉传》就记载了唐龙朔年中,频勅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行圣迹的时候遇见的圣雨奇迹。赜等祇奉明诏,星驰顶谒,并将五台县吕玄览画师张公荣等十余人,共往中台之上。未至台百步,遥见佛像……后欲向西台,遥见西北,一僧着黑衣乘白马奔就,皆共立待相……又往大孚寺东堂,修文殊故像,焚燎傍草,飞飙及远,烧爇花园,烟焰将盛。其园去水四十五步,遣人往汲。未及至间,堂后立起黑云举高五丈。寻便雨下,骤灭无余,云亦当处消散,莫知其由。便行至于饭仙山,内侍张行弘,复闻异香之气。……皆亲顶礼。赜等既承国命,目睹佳祥,具已奏闻,深称圣旨。

更直接的例证是,据《广清凉传》记载,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代州都督薛徽曾登台顶向文殊菩萨祈雨。
”开元十八年,代州都督薛徽,以岁属亢陽,久愆时雨,草木焦枯,种植俱废,都督谓众曰:吾闻台山文殊菩萨极多灵异,有无缘慈,必哀祈请。遂登台顶,竭诚祷雨,倏见华严寺上有群飞白鹤,凡二十一只,徘徊翱翔,集于台上,须臾即散。俄顷黑云叆叇,驶雨洪澍,五县霑足也。民至二十六日,方兴耒耜。是秋大丰,耒耜小穀皆孰,粟斗三钱,百姓饶乐。若非至诚感神,曷能致此“。
文殊菩萨作为山神担当的求雨职能不仅施与忻州、代州等周边地区,甚至还波及整个山西的核心太原地区。
在五台山祈雨掌故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北宋宰相张商英。张商英(1043~1121),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属四川)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元符元年(1098),为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崇宁初,为翰林学士,拜尚书右丞转左丞。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赠少保。
张商英原本任开封府推官,有一日梦游五台山金刚窟。五个月后,张商英被朝廷调到河东路当提点刑狱公事,八月他到任后朝圣五台山巡礼金刚窟,所见竟然皆与梦中一样。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张商英因公务正式入五台山,听清凉主僧说南台出现过金桥圆光,张商英便于傍晚抵达金阁寺,燃香礼拜后,见到了金桥和金色相轮,轮内为深绀青色。七月初一,张商英携家眷、僧人辩与台主在北台见到红炬圣灯。七月初三,张商英同保甲司勾当陈聿、兴善监镇曹谞晚登梵仙山,商英要为他们请五色祥云,礼拜默祷后又现。商英认为紫气祥云之下当有圣贤出现。良久,宫殿楼阁和诸菩萨化现。阵聿与曹谞连连赞叹:“圣哉,圣哉”。由此他对文殊感通事迹“由疑生信”到“笃信弘传”,以士大夫身份撰写《续清凉传》。
大观四年(1110年)六月,久旱不雨,张商英受命祈雨,他三次入山祈雨,三祈三应。并州大旱时,张商英以"文殊眷属"身份几上五台山祈雨,元祐四年六月为祈雨至五台山罗睺殿礼拜圣迹。
张就任之时,也久旱甘霖,徽宗大喜,钦赐“商霖”二字。商霖,典出《尚书》卷十〈商书·说命上〉。 商王武丁任用傅说为相时,命之曰:“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 后遂以“商霖”称誉济世之佐。
宋代祈雨是非常频繁的。比如仁宗祈雨非常勤快,《宋史》多次记载他自己亲临祈雨。“庆历三年五月庚辰,祈雨于相国寺、会灵观……戊子,雨。己丑,谢雨。”“皇祐二年三月甲午,遣官祈雨。”宋代官方祈雨,地点多设在寺庙和道观。
神宗分别在治平四年、熙宁元年、熙宁二年三次“命宰臣祷雨”,主持仪式的官员都是宰相级别。南宋孝宗的时候还专门制定了一套祈雨的方案,名为画龙祈雨法。
张商英作为宋代宰相,其服饰打扮与水神庙所谓《千里行径图》中的展脚幞头的宋代高官完全一致。当然,我们并非在此想去比附《千里行径图》中的官员角色就是张商英,那就太浅薄了,而是说,壁画中的这个角色,第一绝非唐太宗,第二,是宋代高官打扮,所以,这个角色大致就是朝廷派遣的官方的祈雨钦差的角色,一如北宋的张商英的身份与祈雨使命一样。

这种朝廷重臣祈祷神灵的布局与打扮,也出现在玄天上帝启圣录系列图像中,这次祈祷者是北宋重臣吕大防,祈祷的对象则是玄天上帝。

同样,这类朝廷重臣祷拜神灵的布局也出现在南宋梁楷《道君降临图》中,这次祈祷的对象是元始天尊。见下图所示:


由此可见,五台山既有毒龙,而文殊则是制龙大圣,一旦驾驭毒龙,则风调雨顺,所以,官府也去五台山向文殊祈雨。所以,作为制龙圣人文殊菩萨化应的文殊老人,也自然与祈雨可以发生有效的逻辑关联。

二、文殊化应中的金桥与楼阁
顺便说一嘴,张商英作为宋代宰相,赴五台祈雨,而见文殊,见亭台楼阁,是不是与水神庙壁画中的千里行径图中,宋代贵官打扮者朝圣祈雨、文殊化应圣老人在云端化现,旁有亭台楼阁的情景有三分神似呢?水神庙壁画中的千里行径图不必是具体的张商英个案,但是可以是类的比照。
《敦煌遗书》《五台山赞》中都有文殊降毒龙、圣鸟点灯、文殊化老人、云中金桥等化应故事要素,《五台山》曲子写本也有“大圣堂,非常地,左右龙盘,为有台相倚”的叙述。五代敦煌五台山图中,文殊菩萨、金桥、金龙要素一应俱全。这与水神庙壁画千里行径图中的桥、持杖老人以及楼台、降龙的含意也有某种奇妙的关联性。

《广清凉传》载(释道义禅师)唐开元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游至台山访寻文殊所在:“举目见一金桥,义即随登,乃金阁寺。……遂入寺庭……义曰: 和尚寺舍尤广,触目皆是黄金所成……道义遂辞老僧。出寺百步,回顾已失所在,但空山乔木而已。方知化寺,遂回长安”。此传说为后世《化现图》提供了更多元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金阁寺和化金桥。
同样,唐代法照称受到文殊菩萨点化,大历五年到五台山。法照作《五台山赞》,从传记赞文中,法照所见化现有:五色云、化寺、佛光、金桥、文殊侍从、文殊普贤、圣灯、佛陀波利等。
金桥元素也出现在莫高窟361窟《化现图》中,壁画中标识了“圣金桥”。
“后唐庄宗时来华的天竺普化大师,在《普化大师行记》中有载云:(普化大师)昨四月十九日平[旦]达华严寺,寻礼真容。……二十二日游王子寺,上罗汉堂,礼降龙大师真[容]……巡礼未周,五色云现。……晚际有化金桥,久而方灭。……礼佛之次,忽有祥云之中,化菩萨三尊,举众皆礼敬”。

三、五台山与霍山
关于文殊老人是否可能在水神庙壁画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文殊道场在山西的五台山,五台山位于忻州市,而山西的水神庙在洪洞县,两者相距三百七十多公里,两者又能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在文殊信仰以及其他佛教信仰中,化应是跨地域的。是不拘泥地域的。化应只是一种觉悟的手段。佛经中本有“法身遍一切处”的概念。在《华严经》中说“一念于一切处为一切众生示成正觉是菩萨园林,法身周遍尽虚空一切世界故“,既然法身遍一切处,则佛陀圣地也就自然不拘泥于某处。
据《宋高僧传》载,“法相宗”开宗窥基曾于唐高宗咸亨二年登临五台山。窥基“行至太原传法,三车自随。前乘经论箱帙,中乘自御,后乘家妓女仆食馔。于路间遇一老父,问乘何人。对曰:家属。父曰:知法甚精,携家属偕,恐不称教。基闻之,顿悔前非,翛然独往。老父则文殊菩萨也”。
可见,这次“文殊化现”的地方,并非文殊道场的五台山,而是太原。而太原离五台山大约两百公里之遥。
唐代高僧义净《西行求法行记》中就曾经提到:“西方赞云:曼殊室利现在并州, 人皆有福,理应钦赞。其文既广,此不繁录。”而古之并州,大约当今之山西。由此,既然文殊化应不拘泥于五台山,则至少山西境内的文殊化应,也是理所应当的,而水神庙所在洪洞县正是在山西境内,符合文殊并州化应的范畴。
其实,文殊化应的区域不仅超越了五台山,也超越了古并州,据《宋高僧传·灵坦传》载,大历八年,太原文水僧人灵坦游方扬州,感应到文殊在空中为其开示,见文殊菩萨化现并以掌按其项,为其授记。在此,文殊化现之地已到江苏扬州之地。灵坦经文殊授记后,项上有“四指赤痕”,他到达润州金山,竟然也留下了降服毒龙的传说。在《宋高僧传·道潜传》中,钱塘永明寺道潜到五台山礼佛时曾“躬覩文殊圣容”,后到如今浙江衢州地区,在衢州古寺览阅藏经时又见文殊化现。在此,文殊化现已到浙江衢州之地。
以五台山为信仰中心的文殊信仰广为流传。因路途遥远或者其他因素,所以在各地也出现了诸多的“小五台山”。五代的福建、西夏、辽代等都出现过取名五台山的地方,西夏的五台山在贺兰山,辽国的五台山在河北蔚州,各地效仿五台山在本地营建“文殊院”和“文殊堂”就更所在尤多不胜枚举。自唐宋开始, 五台山文殊信仰就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尼泊尔以及泰国等地。唐贞观十七年朝鲜慈藏法师仰慕中国五台山,在五台山得到一颗佛祖顶骨舍利及一件袈裟,回国后他将自己修行之地改名五台山,日僧裔然朝礼五台山,归国时携带回了宋版大藏经、十六罗汉画像等珍贵文物,他上奏天皇请求将京都西部的爱宕山改为五台山,并在山中建立清凉寺,安放释迦旃檀瑞像和佛经等。可见,文殊道场本身的五台圣地,不仅延展到了西夏、辽国,也拓展到了朝鲜半岛与东瀛。
所以,既然文殊菩萨的化应地不局限在五台,也不拘泥并州,那么作为同在并州的洪洞县的水神庙壁画上出现文殊化应,也是完全合理的。况且,前述《广清凉传》载,唐开元十八年代州都督薛徽曾登台顶向文殊菩萨祈雨。之后宋代张商英也曾奉命向文殊菩萨祈雨,其实,文殊菩萨的求雨法力、雨露恩泽不仅施与忻州、代州等周边地区,甚至还波及整个山西的核心太原地区。所以,水神庙壁画上存在文殊老人符合逻辑。
在俗称的水神庙《千里行径图》的左上,绘有玉渊亭,建于霍泉侧畔。亭为四角攒尖顶式样,壁画上亭檐下"玉渊亭"三字仍清晰可辨,亭内坐着一位僧人,一位文人,文人持扇,西边泉岸有一老翁垂钓,小沙弥端盘杯。

这样的亭台,与两三人物聚饮闲谈的情状,也与西夏《文殊变》壁画中,波涛中的亭台人物,有着惊人的神似,见下图所示:


福州有一座定光寺,俗称“白塔寺”,是闽王王审知为其父母祈福,于唐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所建之白塔。建寺两年后,为祝贺朱温即位,曾改名为“万岁寺”。其中有座殿宇叫做法雨堂,门口两根盘龙柱,檐下悬挂蓝底金字匾,上书“法雨堂”。相传五代后梁贞明元年(公元915年),福州大旱,有云游僧义收到白塔寺祈雨,他在寺前木柴堆塔,自己坐塔上诵经祈祷;随火焰升起,大雨骤降。法雨堂就是为纪念义僧义收舍身求雨事迹而创建。
而这个纪念祈雨的佛殿内供奉着的就是卧佛、西方三圣、文殊、普贤等诸多佛像。由此,假设洪洞县水神庙壁画中,一边存在西方三圣,一边又有文殊化应,看来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也许有人要说了,水神庙明应王殿的壁画,怎么会与佛教有关呢?有专家还说水神庙是风俗小庙,其实,大家看一下下图中壁画上空的这组景象就可以明白壁画是否与佛教有关了,至于其中到底是如何的关联路径,我们下回详细分解。

综上所述,也许文殊老人也未必一定是水神庙壁画中《千里行径图》的本意,但是我们在此就是为了开拓思路,因为千里行径图至少在诠释唐王故事上,存在着不完备的要素。而存在其它的可能性,同时,鉴于我们设想的,所有的整体壁画都在为祈雨服务,都聚焦于祈雨,而且可能本身就是阴阳合顺的交感触媒,更深的探索,有待继续研究。







原创版权,违者必究
有关于水神庙壁画的历史文化与艺术图像的探索,请继续关注下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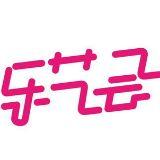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