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曹旭


一
儿子长大了,不愿听我指教,要他如何如何的话被反感了,而且不再愿我和他的母亲陪着睡了。儿子的成长是向着理想的那个地方奔吗?他在什么时候遇到了叫做理想的那个东西?在理想的王国里又会选择哪个公主?当他豢养的鸡仔夭折,他的梦中小鸡会复活吗?他在与理想相遇之时,看到之前,所有的想象是梦幻吗?就这样,我悄悄的站在他的身后,望着已逾他1米30的身高,不知所措,也许根本的原因,是我忙于工作,繁于应酬,又华于自娱的自私吧。
办公楼另院楼外,有一棵原不起眼的树,我抬头去望局长是否在屋时,不料有一束鲜花在春天里开放,是我熟悉的花,叫做白玉兰的。她不仅让我惊喜,而且一下子让我回到了那诗情词意之中,那我苦苦追索的理想之域。与我有知遇之恩的,你推开窗子,放进春风的时候,可否发现这一树的灿烂?你孜孜求之的学校和整个区的教育工作,可否就是你的理想?
同一层楼,同一院的春光,同一袭春风的另一个窗口,窗也悄悄地打开,有一盆新绿的花草被搬出,那室内是两个行政工作人员,搬花于高台,沐春至三月,她的理想又会是什么?她仅仅是对自然的感悟,仅仅是与天地的呼吸相通?仅仅感叹享受着生活的甜美和宁静吗?草根逢春萌绿,草根年年在季节的轮回中生生不息,在生生不息中一树一盆的萌芽或绽开鲜花。
我的儿子,我不过急于你的困惑之际,你的聪明和父母的呵护,还有天地的神灵,将护送你健康成长,听到花开,看到春来。


二
女儿是如花的,我却自卑如粪土的吧;花在粪土上茁壮成长的,但花常常不屑于粪土的臭味。幸如一个女人对你说,40岁的男人一朵花,你不是粪土,你是粪土上的一朵花。
说这话的女人已是经朝露夜霜数月的鲜花,她美丽的容颜在岁月中冷笑的雕塑,那么温柔却又无情地把她雕刻,在她的眉间而不是额头。她是容易皱眉的嘛,她的极喜乐极痛苦的眉间频皱,黯然闪烁。她的皮肤是洁白的,她青春的脸庞与手臂,闪烁着古人所谓凝脂一样的色泽,也怎么仅是凝脂?是可观看不可手触,那肌肤是必有弹性的。因为正是大学的年龄,世事的沧桑,无法言喻的痛楚,还有那正襟危坐的师言贤论,是如何让她痛苦,受到煎熬,在苦涩的风中摇曳,在远处高大树木的阴霾里那么卑微。
我却以为她是美的,正如我知道这春夜的静谧和那春花灿烂中的卑浅。冲她笑笑,她并不知道我的深意;我冲她说几句真心的话,她并不知道我的情痴。她说我的花,我却不明言,我只是微微的赞叹,然后看她一点点的萎缩,一瓣瓣地凋零,化作我树下的泥土,在我的身上复活。
女人是如花的,最后却成为一杯泥土和粪壤。树在花壤上茁壮成长,深深记得花儿的幽情和纯洁,也告诉女儿们,40岁的男人是一棵树,正成长的树,不是一朵嫩弱的花。只是想到黛玉的葬花,盛开的花之葬,埋葬着青春和声象。

☆ 本文作者简介:曹旭,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教师进修学校干部,笔名陈草旭变,近年来有数百篇散文、小说见散文在线、红袖添香、古榕树下、凯迪社区等文学网站,合著有人物传记《那年的烛光》。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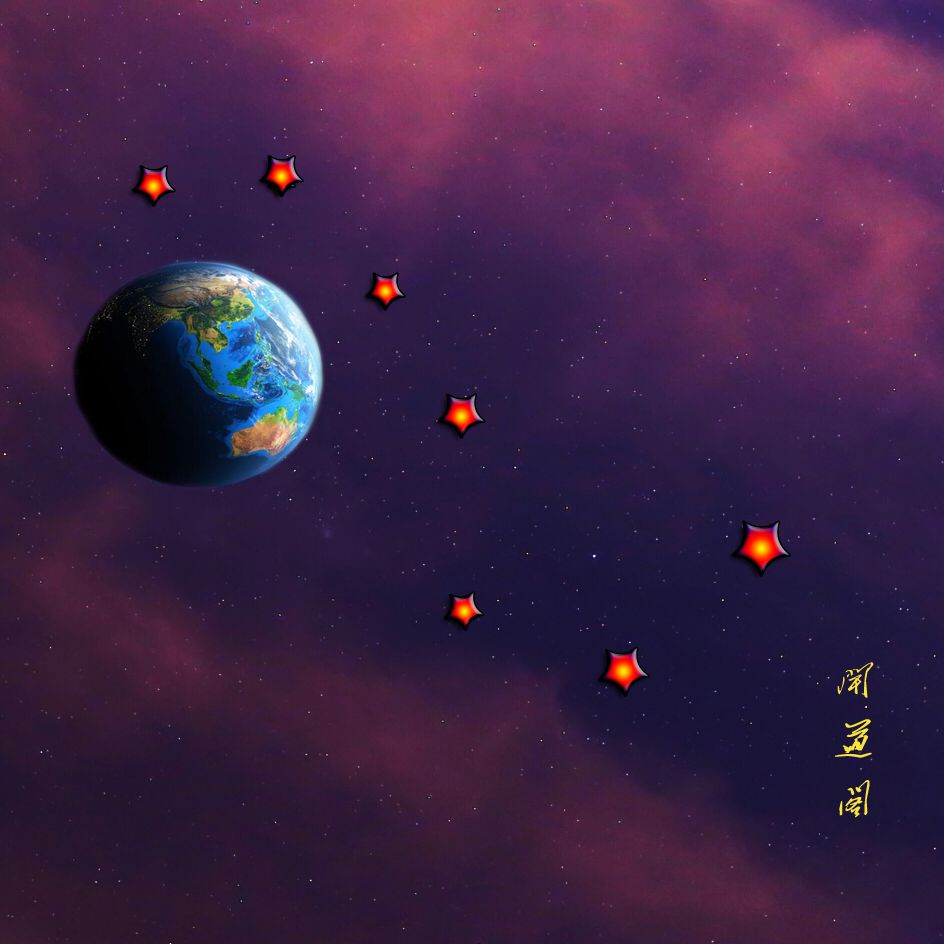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