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水牛城66》是文森特·加洛导演的第一部长片,这部电影几乎是他的独角戏。他似乎不相信任何人,他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主演,甚至还是作曲、剪辑和制作人——这个习惯在他之后的《棕兔》、《写在水中的承诺》《间谍》中一直延续着。
从《水牛城66》开始,在他自己导演的电影里,他从未与他人分享过光荣或失意,所有鲜花和砖头统统涌向他一个人。因为在他看来,他的电影就是他一个人的电影,是“加洛出品”。他说:“我只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因为害怕什么东西而被经纪人和企划人员精心保护起来,现在这样我才觉得舒服自在。”
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时代,文森特·加洛依然恪守新浪潮“作者电影”的信条,并且由于他性格中天生的桀骜不驯和卓尔不群,他做得比那些60年代的前辈们更加决绝。
影片讲述了一个刚刚出狱的男人比利如何在24小时内,从一个满嘴谎言、暴躁易怒的“失败者”,蜕变为一个终于敢直面自己软弱的普通人。
这部电影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英雄的壮举,有的只是一个被生活反复蹂躏的小人物,如何在最绝望的时刻,被一个陌生女孩的温柔轻轻托住。
比利的故事从监狱门口开始。他刚刚服完五年刑期,却不是因为什么惊天罪行,而是因为一场荒诞的赌局——他替人下注,赌水牛城比尔队赢球,结果球队输掉比赛,他被迫背债入狱。
出狱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自由,而是疯狂地寻找厕所——这个看似滑稽的开场,精准地勾勒出比利的生存状态:他被生活逼到角落,连最基本的尊严都难以维系。
比利的困境不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他虚构了一个完美的世界给父母——在谎言里,他是成功的商人,有体面的女友,而不是那个蹲了五年监狱的“失败者”。为了圆谎,他绑架了偶然遇见的女孩蕾拉,强迫她扮演自己的未婚妻。
蕾拉,这个穿着湖绿色袜裤、眼神清澈如小鹿的女孩,本该是被胁迫的受害者,却在比利歇斯底里的表演中,看穿了他脆弱的内核。她安静地配合他的谎言,甚至在比利的父母面前即兴发挥,让这场荒诞剧意外地有了温度。
电影最令人心碎的段落,是比利回到父母家的那场戏。他的父亲沉迷于电视里的橄榄球比赛,对儿子的归来漠不关心;母亲则絮絮叨叨地抱怨,甚至直言“如果有得选,我宁愿没生下你”。
这个家庭像一座冰窖,比利的童年创伤在此刻赤裸裸地摊开——他从未被真正爱过,所以他也学不会爱自己。而蕾拉的存在,成了这场家庭悲剧里唯一的光。
她在保龄球馆里旁若无人地跳舞,哼着Moonchild的《Lonely Boy》,那一刻,比利愣住了。这个女孩不需要他的谎言,她看见的恰恰是他拼命掩饰的破碎,却依然选择靠近。
影片的魔力在于,它用荒诞消解了痛苦。比利的世界充满黑色幽默:他复仇的目标是个早已金盆洗手的黑帮老头;他幻想中的英雄主义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甚至他精心策划的“完美见家长”也变成了一场滑稽戏。
但正是这些荒诞,让电影没有沦为苦情剧。加洛的镜头下,痛苦与幽默如影随形——当比利终于找到厕所却发现需要投币时,当他在餐厅里对着蕾拉咆哮却被服务员无视时,观众在笑,但笑里带着酸楚。
而蕾拉,这个看似被动的女孩,实则是整部电影的救赎核心。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使型”角色,她有她的古怪与固执。但她拥有比利最缺乏的东西——接纳真实的勇气。
电影的结尾,比利放弃了复仇,带着蕾拉回到那家霓虹灯闪烁的汽车旅馆。在粉色灯光下,两人相拥而眠,像两个终于找到归宿的流浪儿。这个结局没有宏大宣言,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它给出了比救赎更珍贵的东西——和解。
《水牛城66》上映二十多年,它的后劲却随着时间愈发强烈。在这个崇尚成功、贩卖焦虑的时代,比利这样的“失败者”反而成了最真实的镜像。我们或许没有坐过牢,但我们都曾被某种无形的牢笼禁锢——社会的期待、家庭的创伤、自我厌恶的循环。
而电影给出的解药简单得近乎奢侈:也许救赎不在远方的英雄梦里,就在当下,在一个愿意陪你吃馅饼的人眼里,在一首跑调的《Lonely Boy》里,在终于敢对自己说“这样活着也可以”的瞬间里。
《水牛城66》1998
导演:文森特·加洛
编剧: 文森特·加洛 / 艾莉森·巴格纳尔
主演: 文森特·加洛 / 克里斯蒂娜·里奇
豆瓣8.4IMDb7.4
前往
好消息:为感谢影迷长期以来的支持,特推出千余种商品,几百种精选图书,粉丝超惠选择,不妨逛一逛吧!件件亲测,七天无理由退货!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点个“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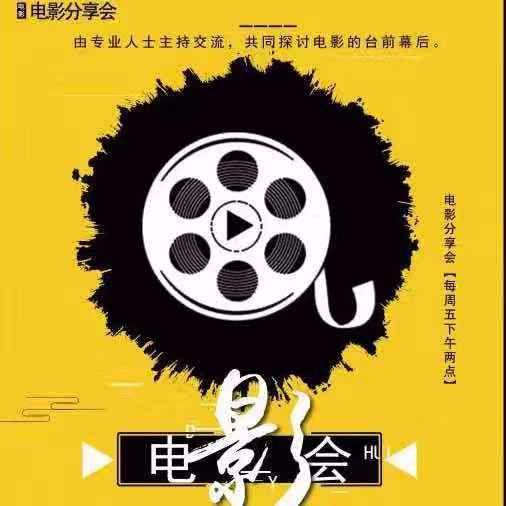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