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夏天,热浪炙烤着训练场,我攥着军校毕业证书的手心全是汗。作为从地方高中直接考入军校的"学生官",此刻站在全排战士面前,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带着刺的目光。特别是三班长老王,那个当了八年兵的"老炮儿",正用似笑非笑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
"排长,单杠二练习能拉多少个?"队列里突然响起的声音让空气瞬间凝固。说话的是炮班的老兵张大山,人送外号"张大炮",臂围比我大腿还粗。没等我回答,他又补了一句:"要不您给兄弟们打个样?"全排顿时响起此起彼伏的起哄声,三班长甚至吹了个响亮的口哨。
汗水顺着钢盔带流进眼睛,火辣辣的疼。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请教——这是下马威。器械场上的单杠在烈日下泛着冷光,就像张大炮嘴角那抹挑衅的笑。接过战士递来的镁粉袋时,我瞥见指导员站在树荫下,手里的笔记本已经翻开新的一页。
当我的作训服后背完全湿透时,单杠已经晃动了二十七下。落地瞬间,炮班几个兵的表情像见了鬼——这个戴着眼镜的"学生官",居然比他们班长还多拉了五个。但真正的考验在晚饭后降临,三班长带着几个老兵堵住了我回宿舍的路:"排长,夜间射击有兴趣比划比划吗?"
那晚的靶场月光惨白。当报靶员喊出"48环"时,我听见身后有钢盔掉在地上的脆响。这个成绩比三班长还高出3环,但我知道,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熄灯号响过后,我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要让他们服气,光靠军事素质还不够。"
第二天早操,我特意提前二十分钟站在了队列前。当三班长揉着眼睛出现时,看见的是已经跑完五公里的我,作训服上结着白花花的盐霜。接下来的一周,我每晚泡在班排里帮战士写家信,周末自掏腰包给家庭困难的战士寄津贴。直到某个深夜查铺时,听见上铺的新兵小声说:"咱排长...好像不太一样。"
转折发生在秋季战术演练。旅里突然改变预案,要求我们排担任穿插分队。沙盘前,三班长提出的方案遭到连长否决,我在地图上画的那条迂回路线却让参谋长眼前一亮。当全排踩着齐腰深的河水完成侧翼包抄时,炮班战士主动把最后干爽的袜子塞给了我。
那年冬天特别冷,但排里的气氛却像烧旺的炉子。张大炮开始叫我"眼镜排长",这个外号后来传遍了全营。春节会餐时,三班长端着白酒过来碰我的可乐:"排长,我敬你是条汉子。"他仰脖喝尽的不仅是酒,还有那些不服气的日日夜夜。
1999年开春,我们排被选中参加军区比武。在武装泅渡科目中,新兵小李突然抽筋,是我扛着他游完了最后三百米。当裁判组宣布我们以0.3秒优势夺冠时,全排把我抛向空中的力度差点让我撞上礼堂吊灯。庆功宴上,旅长拍着我肩膀说:"早知道该让你当连长。"而三班长醉醺醺地搂着张大炮说:"咱排长...嗝...是块带兵的料!"
二十年后的战友聚会上,已经成为某训练基地教官的张大山端着酒杯找我碰杯:"当年要不是您那27个单杠..."话没说完就被三班长打断:"少往脸上贴金!是排长半夜给咱们盖被子的那双手..."我看着这些鬓角泛白的老兵,忽然想起那个月光如水的靶场。带兵就像种树,你永远不知道浇灌的哪滴水,会让种子突然破土而出。
(经历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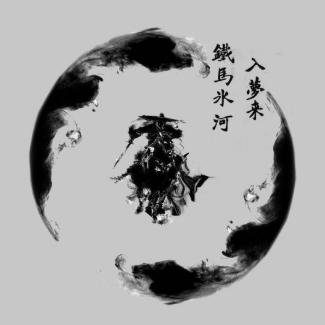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