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西安的道北地区,居民们的“官方”语言,就是河南话。为什么?河南人多呗。
解放前,逃荒的河南人坐火车来到西安,就在火车站附近落下脚、扎下根,道北一带河南人最为集中。许多年过去了,尽管道北人一张嘴,也能说字正腔圆的西安话、普通话,可那是出门办事儿才说的。回到家门口,仍是一口河南话。只是因离开本土年代久了,这河南话稍稍有些变异,河南省任何一个地方的口音,听起来都和这里的不完全一样。不过,对于河南以外的人来说,只要是河南话,就全是一个味儿。
小个儿丁浩就说河南话,正宗的河南话。也就是说,一听口音,就让人知道他是在河南长大的。至于丁浩是哪个地县的,道北的闲人们没人向他打听过。总之,说河南话,大伙儿就接受他,认同他。更何况,这丁浩身高不足一米六,偶尔从街道上出溜过来、出溜过去,并不引人注意。
丁浩眼睛不大,一说话就成了个笑模样,看上去是个好脾气。有人眼尖,发现这小个儿的左手没有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好像也少一截儿。
“让电锯给划了!”丁浩每每这般解释。
丁浩来道北有一年多了。早先,他来这里找建。建在这一带有些名气,是个资格比较老的闲人。建二十岁左右时,是个打架的好手,以心狠手黑出名。往后,建被人引上了道儿,吸上了“毒品”。等丁浩被人引荐到建跟前时,建已经成了一个毒品方面的“权威人士”。
从丁浩拿来的那二斤“白粉”中,建抠出指甲盖大小,放进嘴里一尝,马上又“呸、呸”地吐出来:“假的,你让人耍了!”
原来,丁浩提心吊胆从广州弄到西安的这一大包“海洛因”,其实只是一些“料子”,也就是毒贩往海洛因里混、用来压秤的白色粉状物。
丁浩从建这儿得到的收获,是一年后继承了建的媳妇——花。
花年轻时候真的像花一样迷人。花上初中时候,学校外面就常有小流氓等着截她。花起初很害怕,后来,和其中一个好上以后,花就不害怕了,只是她再也没心思念书了。草草地混到初中毕业,花就进了纺织厂。
当花挺着大肚子嫁给建以后,再也没去上过班。建吸毒后,花哭过,闹过,寻死觅活过;可很快,建开始贩毒,花又过上了衣食无忧却又提心吊胆的日子。
一些吸毒人员没钱的时候,就会把形形色色的东西弄到建这儿换毒品。花可以从容地选出她喜欢的东西,比如戒指、项链,甚至洗发精之类。当然,这期间建也时常会被警察抓去。建吸毒已经吸成了一把骨头,对那事儿早就没兴趣了。而花虽说也早已邋遢得没了当年的花容,可毕竟才三十多岁,怎么能耐得住寂寞呢?丁浩来得次数多了,俩人的眼光相遇时,擦出了火花。
不久,建因吸毒丧了命,丁浩与花也就不再遮遮掩掩,自然而然地住到了一起。
花和丁浩搅到一起,还因为这个小个儿对自己的儿子不错。其实,丁浩心里最清楚,他自己的儿子也应该有这么大了,只可惜自己关于儿子的记忆全是孩子三岁以前的。
建一死,那些吸毒的就开始来骚扰花了,谁让她这会儿成了孤儿寡母?有人来到花家里,吵吵闹闹,说建欠了他的钱,临走时会随手抄走个家什。最可恨的是那个叫大军的,跑到家里,二话不说,关了花的儿子正在看的电视机,口口声声说这电视是临时让建保管的,不由分说就往外搬。花上去阻拦,大军居然狠狠给了她一个耳光,把花的半边脸都打肿了。花哭着打电话叫回了丁浩。
2002年春节前几天,丁浩从一个人手里花八百元买了一把猎枪。大年三十,趁爆竹声响成一片之际,丁浩朝天上放过一枪,那一声巨响震得丁浩耳朵嗡嗡了半个月。他知道他这杆枪不是摆设。
这会儿,花和儿子哭成一团,丁浩的血顿时冲上了脑门。他从床下摸出那杆枪,打开保险压上顶膛火,拦下一辆出租车就去追大军。可这会儿,哪儿还寻得见大军的半点人影儿?花的半边脸火辣辣地疼着,恨不得亲手宰了大军。她拉着丁浩去崇明路找烟民领,因为领也不是好东西,几天前也欺负过她;更重要的,是领绝对知道大军的下落。
领是一个十分张狂的家伙。领当然不把死了丈夫的花放在眼里。一见花对他出言不逊,立刻就想抽花的脸。可是,他的巴掌还没抡起来,一只猎枪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的脑门上。他竟没注意,花的身后居然还有一个比花还矮的男人。
领被丁浩的枪震住了。等他睁开眼,发觉枪并没有响的时候,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给花说好话。他嫂子长嫂子短地亲切称呼着、辩解着,不时拿眼角余光扫一扫丁浩的枪和丁浩的脸。
领住的是临街的平房,转眼间就围了一群人,大家兴致勃勃地看热闹。这时,丁浩想起了山东那个被他杀掉的出租车司机。此时花正揪着领的衣服,滔滔不绝地大骂。丁浩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极其可恶,她已经把他扯进了一个烂泥潭,让他没法收场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不能在正占上风时突然撒腿跑了吧?
警察就在这个时候赶到了这里。由于有一把猎枪,这就不是一起普通的打架斗殴了。在前往太华路派出所的警车里,丁浩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把“丁浩”的简历背了一遍。“丁浩”,河南登封人,从小在哪儿上学,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已经有许多年,没人再称呼他陈永亮了。他被人们张三、李四地叫着,丁浩只是他在西安期间用的一个化名。当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一口河南话的小个子,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小兴安岭南侧有个叫北安的小城市,这里一入冬,就经常白雪飘飘,呼出一口气,就如口吐长龙。
陈永亮的家就在北安市的通北镇,这里离哈尔滨还有近千公里远。陈永亮的父亲在镇上的林业局工作,家里有七个孩子,陈永亮排行老四,被人们称作陈四儿。本来,陈四儿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小时候学习不错。由于他个子矮,打架斗殴之类的事儿本不该有他的份儿。可是这孩子有股狠劲儿,受不得半点气。这一点,在他用刀子一口气儿捅倒好几个膀大腰圆的大孩子之后,得到了证实。赶上一九八三年“严打”,陈四儿以流氓罪被判刑十二年,这一年,他才十六岁。
在监狱里,陈四儿对自己的一时冲动悔恨不已。在漫长的时光里,他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回报:通过自学,他取得了建筑装饰这样一个热门专业的大专文凭,这在当时成为报纸、电视上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北岗监狱里的良好表现,让陈四儿一再赢得了减刑的机会。1990年,他提前刑满释放。
陈四儿的巧手不是吹出来的。干活时每逢别人亮出绝活儿,陈四儿就反反复复地跟人家学,直到完全掌握其中的技巧。陈四儿会木雕,也会在木板上用烙铁烙出各种装饰图案。后来,他在深圳的一次大型活动中制作过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在这条龙前面,他还和一位市长合过影。
1990年底,陈四儿到哈尔滨看冰灯时,给人家露了一手。结果,人家盛情相邀,请他留下来搞创作。从这一年到一九九四年,陈四儿的作品年年在冰雕节上向游人亮相。
在此期间,陈四儿有了妻子,也有了孩子。冰雕只能在冬天做一做,陈四儿得谋生挣钱。可通北镇乃至北安市毕竟太小了,陈四儿没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一九九五年,经人推荐,陈四儿到秦皇岛的一家小广告公司谋了个职。陈四儿聪明,手上又有点绝活儿,老板很欣赏他,给他开的工资不少,还委以副总经理的头衔。可陈四儿眼高心大,等他摸熟门道后,便脱离老板自立门户,把老板原来的客户、生意全拉走了。
老板是个人高马大的汉子,哪肯忍下这口气。他找上门去,准备揪住忘恩负义的陈四儿揍一顿。可没想到,陈四儿身后站着一个黑铁塔似的大汉,他故意让对方看到自己身上的刺青和拍在桌子上的刀子,警告小老板不许再来生事儿。老板吓得面色如土,立即转身跑了出去。
黑大汉名叫李继刚,是陈四儿在北岗监狱时的“难友”。此人是个争勇斗狠、打架玩命的主儿。陈四儿以每月一千二百元的工资雇下他给自己看摊儿。可没多久,陈四儿有一笔生意做砸了,眼看要赔个底儿掉。陈四儿一不做、二不休,卷了别人买房时交付的一万多元的订金,和李继刚一起坐上火车,一口气儿跑到了江苏的连云港。
接下来,二人信马由缰一路逛到了山东。游泰山时,他们的盘缠已所剩不多。正好有个女青年一个人下山,与他们二人结伴而行。陈四儿便让李继刚把安眠药倒在了一瓶可乐里,让那个女子喝下,然后,抢了人家身上的六百块钱。
坏事儿开了头,就收不了手,那区区六百块钱很快就花光了。在济南市区,他们坐出租车时,碰到一个十分热情的司机。他边开车边和两个东北人聊天,临分手,居然还递给他们一人一张名片,说日后要用车可以呼他。
陈四儿的坏水儿立刻又冒了出来:把这辆桑塔纳车弄到外地,能赚一大笔钱,干脆把他的车骗出来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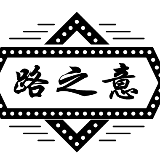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