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戛纳又开始了,了解一下现场信息,《狂野时代》与《风火林山》分别入围了戛纳入围“午夜展映”单元,入围主竞赛单元。让人更加惊喜的是,现场重映了杨德昌先生的《一一》。
电影《一一》剧照
文:秦戬
编辑:杨雁婷
责编:朱学振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2000年,杨德昌先生凭借《一一》获得了第53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且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2007年病逝后为了缅怀杨德昌先生,该片于2009年在台湾正式上映。一部影片,横跨近十年,其中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贯穿电影的始终,令人动容。
影片以台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各自故事为框架,通过对不同年龄段人物的生命体验的记录,揭示了人类在爱、失落、成长与自我认知中存在的困境与感悟。这篇始于婚礼,终于葬礼的环形叙事的诗歌,恰似一首戛然而止的爵士即兴曲,钢琴的黑白键交替叩击着现实的迷雾与觉醒的微光。
在不到三个小时的影片里,提到了但不限于职场的声色犬马、家庭的琐碎支离、孩子的孤独成长、青春的放荡迷惘,大到生老病死,小到绿豆芝麻。涵盖了夫妻、家庭、亲情、青春、成长、爱情、亲友、邻里、职场、教育等现代社会所有的主题关系,几乎无所不包,有着讽刺的外衣,悬疑的色彩,以及感人的内核。所以,这部电影从观看角度来说,不仅适合于成年人,适合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还适合于小孩子。
电影《一一》剧照
整部电影叙写的是杨德昌先生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但很多人却从电影里看到了自己,这就如同影片中父女两人相似的轨迹一样,在茫茫人海中,生命如重重叠浪,循着前面的泡沫,不断寻找命运的口岸。
摄影机如同穿行在时间血管里的红细胞,在简家三代人的生命图谱中巡回:婚礼现场飘落的气球与葬礼上焚化的纸钱形成首尾咬合的莫比乌斯环;百叶窗上流转的夜色倒影着NJ(南俊)眼角的皱纹;汽车玻璃里变形的摩天大楼映照着中年人的迷惘。这些看似随意的镜像镜头,实则是精心布置的时空虫洞。
台北与东京、青春与中年在某个黄昏悄然重叠,在NJ与初恋阿瑞漫步东京街头,霓虹灯管在雨幕中晕染到三十年前,南俊说:"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这句话像钉子楔入记忆的年轮里,让所有关于"如果"的假设都成为想象的涟漪。而婷婷与胖子在影院门口的错身,墙上褪色的海报却是父亲年轻时错过的爱情电影,这种蒙太奇式的时空折叠,将生命不同阶段的困顿编织成交错的锦缎,每个针脚都暗藏命运的谶语。
简家的客厅宛若巨大的水族箱,每个家庭成员都是困在透明壁障后的热带鱼。敏敏每日重复的"早上做什么,下午做什么......"的自白,在婆婆昏迷的床前化作空转的磁带,这种叩问,恰似鱼缸里永不停歇的气泡,在抵达水面时破碎成虚无的禅意。
在影片中,成年人的经历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挣扎,更映射出一种普遍的中年困境:当生活的重复性逐渐侵蚀内心的热情,个体如何在遗憾与妥协中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而洋洋举起相机拍摄后脑勺的姿态,宛如孩童版的普罗米修斯,试图盗取成人世界背面的火种,点亮这个昏暗的世界。
电影《一一》剧照
雨水在本片中成为最诚实的叙事者——它平等地淋湿婚礼的彩带与医院的走廊,模糊了新生与死亡的界限,最动人的雨落在洋洋的校服上,当他跃入泳池克服恐惧的刹那,飞溅的水花在镜头中化作液态的星辰。
当洋洋在婆婆灵前朗读那封未寄出的信,孩童稚嫩的声音与城市的脉搏形成奇妙的和弦:"我觉得我也老了。"这句话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从1999年的胶片一直荡漾到现在。杨德昌导演用这个充满神性的结尾,将私人记忆升华为集体生命的传奇。
《一一》的英文名"A One and a Two",取自爵士乐即兴前的节奏轻点,这个细节泄露了导演的心思:生命本就是没有预设乐谱的即兴演奏,而那些看似重复的日常小节,在时光指挥棒的挥舞下,终将在某个时刻显现出隐藏的和声,就像简家阳台上永远晾晒的衣物,在季节更迭中默默完成着关于存在与消逝的永恒对话。
电影《一一》剧照
暮色中的台北街道,路灯次第亮起如同文明重启,杨德昌导演用这部遗作,在银幕上浇筑出一座关于东方家庭的记忆博物馆。
当我们跟随镜头穿越这些发光的生命标本,或许会突然懂得:所谓成长,不过是学会在时光的褶皱里,与自己的倒影温柔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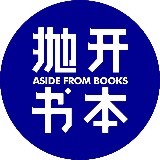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