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马小官
1978年的冬天,内蒙古的寒风刀子似的刮在脸上。我裹着单薄的棉衣,站在营房门口,望着几个城里来的战友背着背包,兴高采烈地登上那辆送他们去火车站的解放牌大卡车。两年,仅仅两年,他们的服役期就满了,回去就能端上“铁饭碗”。卡车卷起一阵呛人的尘土开远了,我嘴里发苦,心里却空落落的像被挖走了一块——在我们这个步兵师,农村来的兵,谁心里不揣着本明白账?两年?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三年是起码,四年五年寻常事,连那些挂着六个年头“光荣”服役期的老班长,也大有人在。
我们农村兵私下里早就嚼烂了这苦涩的“规矩”:想熬成志愿兵,想提干,想跳出农门换个活法,除了拼命干、死命熬,别无他途。那“两年义务兵”的说法,更像是一块看得见却永远够不着的糖。至于探亲假?更是天边的云彩。明文规定,义务兵,除非家里塌了天、死了人,否则根本没资格想!熬到第三年头上,才终于有资格申请那张薄薄的通行证——连上来回路程,抠抠搜搜一共21天。
连队里那些服役四五年、胡子拉碴的老兵油子,是我们这群新兵蛋子偷偷仰望的对象。记得刚下连不久,一次晚饭后,我跟着班长去服务社买烟,昏暗的灯光下,看见一个黑黢黢的老兵,正捏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凑在灯泡底下使劲地瞧。照片上是个两三岁的娃娃,咧着嘴傻笑。班长捅捅我,低声说:“瞧见没?四班长,当兵第五个年头了,儿子出生到现在,还没抱过一回。”那老兵似有所觉,慌忙把照片揣进里兜,动作快得像被火烫着。那瞬间他脸上闪过的窘迫和深不见底的思念,像根冰冷的针,狠狠扎进了我心里。我默默攥紧了口袋里那个记着离家天数的烟盒纸片,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正”字,像一张巨大的、无声的网。
日子在枯燥的队列、冰冷的枪械、无休止的战术演练中,一天天被拉长、碾碎。终于,日历撕到了我入伍的第三个年头。一个训练归来的傍晚,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他手里捏着一张纸,表情有点复杂:“你的探亲报告,批了。”他顿了一下,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路上…抓紧点时间。”那眼神里似乎藏着点别的什么,沉甸甸的。然而被狂喜冲昏头脑的我,哪还顾得上细想?只记得心脏擂鼓般狂跳,耳朵里嗡嗡作响,指导员后面的话都成了模糊的背景音。批了!整整三年啊!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回排房,胡乱往那个磨破了边角的黄挎包里塞着东西,手抖得几次拉不上拉链。当晚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家里那低矮的土坯房、灶膛里跳动的火光,还有母亲在昏暗油灯下纳鞋底时微微佝偻的身影。
回家!这两个字像滚烫的烙铁,灼烧着每一根神经。
通往家乡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摇晃着,慢得令人心焦。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汗味、劣质烟草味、还有不知谁带的咸鱼干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我蜷在过道里,背靠着冰冷的车厢壁,眼睛死死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光秃秃的北方原野。时间像凝固的铅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煎熬中缓慢爬行。离家越近,心里那份积压了三年的思念,反而像野草一样疯长、缠绕,勒得人喘不过气。邻座一位好心的大娘,看我嘴唇干裂,递过来一个熟鸡蛋:“娃,饿了吧?看你这兵当的,遭罪啊。”我勉强挤出个笑,摇摇头,喉咙堵得厉害,什么也吃不下。家,就在前方了,可这最后一段路,却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火车在傍晚时分,终于喘着粗气停靠在一个简陋的、连站台都没有的乡村小站。我几乎是第一个跳下车厢,脚踩在故乡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来不及掸去满身的煤灰,我迈开大步,沿着那条熟悉又似乎有些陌生了的乡间土路,朝着那个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小村庄狂奔。暮色四合,炊烟在远处稀稀拉拉地升起,空气里弥漫着柴草燃烧的、让人鼻子发酸的熟悉气味。近了,更近了!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模糊的轮廓在望,我家那低矮的院墙也隐隐可见了!我几乎是撞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院门,激动地大喊了一声:“娘!爹!我回来了!”
院子里很静。灶房透出昏黄的光亮。一个瘦小的身影闻声,慢慢地从灶房里挪了出来,手里还攥着一把烧火棍。是我娘!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和哽咽:“娘!是我啊!儿回来了!”
昏暗中,母亲抬起浑浊的眼睛,努力地看向我。那目光,带着一种令我瞬间全身冰凉的陌生和茫然。她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像刀刻上去的一样。她眯着眼,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这个穿着军装、满身尘土、比她记忆中高大了许多的身影,嘴唇哆嗦着,张了又合,合了又张,似乎在努力辨认,又似乎完全无法将眼前这个高大的军人,与三年前那个离家时还带着几分稚气的儿子重叠在一起。过了好半晌,一个微弱、迟疑、带着巨大不确定的声音才从那干瘪的唇间艰难地挤出来,像一根针,猛地扎穿了我那颗滚烫的心:
“你…你是…哪个啊?”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灶膛里柴火“噼啪”爆裂的声音格外刺耳。我像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原地,浑身的血似乎都冲到了头顶,又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千山万水的跋涉,一千多个日夜蚀骨的思念,无数遍在心底排练的重逢场景…所有的期待和狂喜,都在母亲这句陌生而茫然的询问里,被击得粉碎。那瞬间,巨大的委屈和心酸排山倒海般涌上来,喉咙里堵得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眼眶瞬间滚烫。
这三年,究竟有多长?长得足以让母亲忘记她日思夜想的儿子的模样!
后来才断断续续知道,自我离家后,母亲的眼睛就一日不如一日。地里的活儿、家里的担子、还有那份望眼欲穿却迟迟不见儿归的焦灼,无声无息地磨损着她的身体和记忆。她常常坐在门槛上,对着村口的方向,一坐就是大半天。她念叨我的小名,翻看我仅有的几张穿着肥大新军装的照片,却越来越难以将照片上那个模糊的影子,和远方那个活生生的儿子联系起来。那份深沉的思念,最终竟成了阻隔她认出儿子的厚厚屏障。
那21天的探亲假,短暂得像指缝里漏下的沙。我在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陪伴,笨拙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家务,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大声和她说话,试图将那些丢失的时光重新刻进她的记忆里。临归队的前夜,母亲摸索着,把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几个煮鸡蛋,还有一小包炒得喷香的花生米,硬塞进我的黄挎包。昏黄的油灯下,她枯瘦的手紧紧攥着我的手,那双浑浊的眼睛似乎清明了一瞬,她终于清晰地、带着无限不舍地唤出了我的小名:“儿啊…路上…吃…下回…早些回…”那一刻,我强忍了多日的泪水,终于汹涌而出。
火车再次“哐当哐当”地驶向寒冷的北方军营。我靠着冰冷的车窗,怀里紧紧抱着那个尚有母亲体温的小布包。窗外是无边无际的沉沉黑夜。我摩挲着挎包里那几颗坚硬的鸡蛋和花生米,它们沉甸甸的,像无数颗无法归家的心。探亲假结束了,但服役的路,还远没有尽头。我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更多的三年、四年,甚至更久。如同千千万万沉默扎根在边关哨所、塞外荒原的农村兵一样,我们的根扎在贫瘠的乡土里,我们的脊梁却要撑起这万里山河的界碑。那些被制度碾碎的青春,那些被距离模糊的亲情,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思念,都化作了边关冷月下无声的忠诚。
(经历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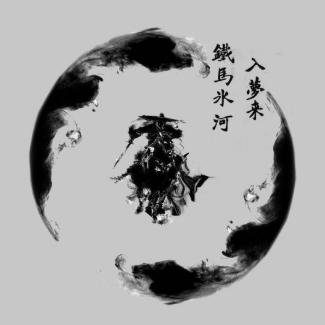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