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洗一条狗都要半小时,早干嘛去了?”
贵妇不耐地扯着牵引绳,指着我鼻子骂得难听,洗宠区里的人全都看着我。
“这手,原来可是拿手术刀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
我默默攥紧拳头,却一句话都没回。
三个月前,新院长一句“岗位年轻化”,让我从主刀兽医生变成了护理小工,徒弟升官,我刷澡。
可短短3月,三起术中事故接连爆出,北极狐、长臂猿、金刚鹦鹉相继死亡,媒体一篇篇逼问:“谁来为这些国家动物负责?”
那晚,院领导们站在洗宠区门口,对我低头哈腰:“老沈,只能靠你了……”
我冷笑一声:“你们当初怎么踩我,现在就得怎么跪着请我回来。”

01
我在这家兽医院干了二十年,二十年里,从小手术做到大手术,从家猫狗看到国家级保护动物。
哪一场疑难会诊不是我顶上的?哪一例术中抢救不是我亲自扛过来的?
可那天,站在台上念决定的,是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
那是一次所谓的“现代化转型说明会”,说是全院大会,其实就是一场权力更替的仪式。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空气闷得发沉,墙上的投影打着“新时期兽医院发展战略改革”的大标题,
我坐在靠后的位置,一杯没怎么碰的清茶摆在手边,手心却莫名沁出汗来。
“为了推进人才结构的年轻化、扁平化,从今天起,沈怀远医师调任宠物美容科,
协助完成宠物护理、洗护相关工作,不再承担一线手术任务与珍稀动物诊疗。”
那一刻,我脑袋里嗡地一下。
全场一片静默,我没说话,只是看了他一眼。
那个站在讲台上的徒弟,穿着剪裁得体的白大褂,胸牌金光闪闪,脸上写满了“革新”和“执行力”。
而他,避开了我的眼神。
同事们都低着头,连个咳嗽都没敢发出来。
没人愿意在这种场合多看我一眼,也没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有人握紧了笔,有人悄悄把椅子往后挪了一下,仿佛和我坐得太近,自己也会被“优化”掉。
会议结束,我收拾了自己桌上的东西。
那本厚厚的《濒危动物临床手术记录》我没带走,扔在了抽屉里,
盖上那一刻,我心里像有什么被彻底合上了。
接下来的两天,我就像从空中摔下来的大鸟,直接被砸进了另一个世界。
宠物美容科在最角落,临近仓库,墙上贴着卡通狗狗猫咪的贴纸,房间里弥漫着洗毛液和香波的味道。
洗澡池边放着一排吹风机,嘶嘶响着。
我换上了蓝色的工作服,胸前那枚“首席专家”的徽章早就摘了。
我曾为藏狐接骨,也为斑鳖缝合皮瓣,如今我只能给一只博美打结毛发、剪指甲。
儿子问我:“爸,他们就这么处理你,你真忍了?”
我没回头:“不忍能怎么样?你的妈妈还等着做复查,贷款还没还完。”
我知道他心里气,可我更清楚,现在这口气不能硬顶上去,我得等。

02
一次,一位女客户看我洗得慢了些,直接撂下一句:
“你这是手抖还是脑子慢?我们家这猫是明星猫,有代言的,你洗不好我投诉你!”
我愣了三秒,只说了句:“下次别选我。”
我能忍,但不代表我不知道羞辱。
那天晚上,我回家晚了。
儿子等我吃饭,桌上是媳妇做的番茄炖牛腩,锅底还冒着热气。
没人说话,只有电视里放着财经新闻。
我刚坐下,媳妇就夹了一筷子菜:“你……能不能,不用每天都这么晚回来?”
我笑了笑,没答话。
她没问我今天洗了几只狗,也没问有没有被人骂,因为她懂,我脸上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习惯了洗澡剪毛的节奏,习惯了员工群里没有我名字的手术排班表。
习惯了中午吃饭没人跟我打招呼,习惯了被人绕着走的感觉。
直到那天晚上,一个熟悉的号码打到了我手机上。
是急诊科的老同事,语气紧张:“老沈,麻烦你赶紧上线看下术前记录,那只藏狐出大事了。”
“谁主刀?”
“是那个你……带过的小伙子。他说术前评估没问题,结果一开胸发现内出血失控,抢救失败。”
我沉默了几秒:“是国家送来的那只?”
“对,已经被媒体盯上了。”
我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着天边的雾灯,听着对面楼顶的风扇咔哒作响。
这个行业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如果连命都救不好,那吹得再响的“数字化”也不过是空壳。
电话那头,老同事压低了声音说:“再这么下去,咱们医院迟早出大事。”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这不是第一次动物死在术台上,却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些不是错误,而是无知和骄傲。
我把手机收起来,站起身,拉上阳台的窗帘。
厨房里,媳妇正在热饭,儿子在房间里背古诗,家里还是那个家,像是跟我这些年的职业毫无关系。
可我心里知道,我不能再等太久了。

03
我一直以为,自己彻底沉下去之后,风波就离我远了。
没想到,真出事了,第一个来敲门的,还是那群把我推到台下的人。
事情是从那只白颊长臂猿开始的。
那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原本只是做个膝关节内固定手术,按我的经验,两小时内能搞定,恢复期一周。
但这回主刀的是那位“优秀青年兽医”,手术做了四个小时,术中多次出血,
术后不到十二小时,猿猝死,死亡报告上写着“凝血机制异常、术中出血未控”。
第二天,网上就炸了。
“珍稀动物死在术台上,责任谁来扛?”
“高薪聘请的专家,到底值不值?”标题一个比一个刺眼。
我在洗宠区,一边剪着一只比熊的脚毛,一边听着旁边几个实习生低声议论:
“那只猿好像是原生态保护中心送来的,说要给它装个活动芯片。没想到……真死了。”
“听说院里开始排查了,好几个组被约谈了。”
我没插话。
吹风机的风很响,我只是专注地修着毛线,装作什么也没听见。
可没过几天,第二起又来了。
这次是北极狐,误诊成了犬瘟热,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等查出来是肝细胞炎,动物已经休克。
抢救了三个小时,还是没能救回来。
这下连保育站的人都怒了,说我们“技术不过关、还自称旗舰机构”,要求出具书面解释。
医院的脸面,差不多丢了一地。
可最严重的,是第三起。
那是一只金刚鹦鹉,全球极度濒危,当地动物园斥资送来我们这边治疗声带息肉,结果术中出现麻醉并发反应,气道堵塞,直接休克死亡。
消息一出,连电视台都来了,站在大门口连拍两天,说“全国唯一拥有高等级珍禽手术认证的医院,竟然三月内死了三例国保级动物”。
我坐在员工休息室,看着墙上的大电视,冷眼旁观这些热闹。
护士小姑娘在旁边低声说:“这事闹大了,听说上头让管理层重新做人员评估了。”
我心里冷笑。
三个月前他们开会决策,把我一个手术量全院第一的老兽医调去洗狗,还大言不惭地说“时代需要新血液”。
现在呢?三只动物一命没保住,才想起来要“评估”?这叫技术失误,我看是人心出了问题。
当天下午,洗宠区的门忽然被轻轻推开。
我回头一看,是行政办的主任,平时一副端着的样子,这会儿却满脸堆笑:“老沈,您这儿……忙不忙?”
我“嗯”了一声,没抬头,继续给一只英短修脚趾毛。
他站了一会儿,见我不接话,只好自己开口:
“是这样,院里那边想请您过去看看一份会诊方案。就是……您当年做过类似的那种疑难案子。新来的几个专家,说实话,不太有底……”
我头也没抬,只说了句:“我现在的职责是护理和洗澡。”
空气顿时安静了下来。
那主任脸上的笑僵了一下,眼珠子转了几圈,又凑上来:
“您也别生气……大家都知道,您水平没的说。这次要不是实在没人,我们也不敢麻烦您啊……”
我终于放下剪刀,看着他:“你是来让我出手的,还是来让我兜底的?”
他嘴巴张了张,最后干笑两声:“哎呀,老沈,咱都这么多年老同事了……”
我打断他:“我现在是宠物护理岗位,手术方案归你们专家小组。我插手,算不算越权?”
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转身接下一只待洗的狗,把水龙头打开,热水哗啦啦地流下来,那人只好讪讪地退出去了。
等门关上,我手里的动作停了一秒。
不是我无情,也不是我真就不想救。
但这些年,我早学会了,真正值钱的,不是你干多少,而是你什么时候说“不了”。
我若轻易出手,这班人明天还得踩着我往上爬。
那天晚上回家,儿子见我难得提前回来,问:“爸,你最近怎么老不开心?”
我摇摇头,没答。
媳妇看了我一眼:“医院那边……是不是又有人来找你?”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她叹了口气:“人啊,有时候不摔个大跟头,是不长记性的。”
我点了根烟,看着窗外夜色。医院那些人,摔得还不够疼。
可惜,这代价不是他们一个人扛,而是几条命。
我不知道,他们还想让我当多久的“临时补丁”。
但我知道,我的尊严,一分都不再便宜出卖了。

04
那天傍晚,我刚给一只萨摩耶洗完澡,身上湿透半边,蹲在角落拧毛巾。
蒸汽屋里湿气弥漫,脚底下还有刚洗完的一摊水,几个实习生正吭哧吭哧地给猫剪指甲,谁也没想到,会有领导来这儿。
门“咔哒”一声被推开,几个穿西装的男人踩着我身后的积水,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前头那个,我认得,是行政副院长,平时走哪都挺胸抬头,现在却跟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似的,脸上的笑勉强得很。
“老沈……您还没下班啊?”他搓了搓手,语气客气得让我觉得陌生。
我没应声,只是把湿毛巾搭在脖子上,低头换了条干净围裙。
后头的主任一看我不搭话,硬着头皮往前凑一步,眼睛里有点红,
说:“真对不起,打扰了。是这样,有紧急任务……”
我依旧不说话。
旁边那个实习生不明所以,站起来准备让位,却被主任挥手止住,脸色都白了。
“老沈,这次真不是一般的活,是外交任务。”
副院长说着,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资料图递给我,
“一头麋鹿,是上个月从北欧送回来的国家级礼赠动物,今晚凌晨就要送去首都展示。可下午运送途中摔了跤,怀疑是股骨断裂,伴随内出血。”
“他们本来想送去动物总院,但专家不在。现在各大媒体正赶往咱们医院,说是现场跟拍‘中国兽医抢救国家动物’。要是出了问题……”
他话没说完,但我听懂了。
这事,是炸锅的节奏。
“你们不是有专家组吗?”我头都没抬,语气冷得像隔夜的水,
“就那几个站在台上放卫星的,喊着‘要革新、要创新’的年轻人。”
副院长脸上抽了一下:“他们……试了。实在做不了。麻醉的药不敢下,位置也判断不清楚。”
我缓缓地站起来,把毛巾往椅背上一搭,望着他们几张脸。
那些人,三个月前坐在会议室里拍桌子喊着“老专家理念落后”,现在却像小学生挨训一样站在我面前,低眉顺眼。
“你们当初怎么踩我,现在就该怎么跪着请我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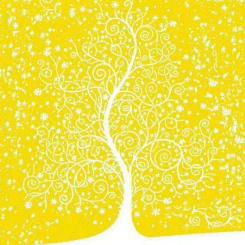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