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末,一位台湾老兵辗转归乡,刚踏上大陆国土,便被带进海关小屋。他本以为等待自己的是盘问与审查,却没想到工作人员的一句话令他热泪盈眶。三十多年的思念,一封家书,一段曲折归途,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情与坚持?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36年初春,姜思章出生在浙江舟山群岛的一座偏远渔村中。这个被海风吹拂的小村落,日复一日地在潮起潮落中度过平静的岁月。村民以打鱼为生,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安稳。而作为家中长孙,姜思章自小被长辈视为希望所在,衣食无忧,书读得比其他孩子更早。
每逢节庆,他总是站在祖父膝前,听老人讲那些关于忠义、家国的古老故事。长辈们望着他的眼神里,藏着无数未尽的寄托。可这样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战火早已在远方燃烧,国家的局势也逐渐影响到了这个海边的宁静角落。
1950年5月,村口茶馆传来风声:国民党残军要穿过东南沿海,路上征兵,连镇上的私塾也临时停课。先生淡淡一句“为了安全”,却让村民心里泛起了不安的涟漪。
但姜思章和伙伴们并未放在心上。他们才十几岁,还以为兵役这种事离自己很远。5月15日下午放学,他们三人沿着熟悉的田埂走在回家路上。卡车突然从岔路冲出来,挡在他们面前。几名军人跳下车,二话不说就将他们推上了车。三人挣扎、哭喊,有人起了恻隐之心准备放人,但话还没说完,又一辆军车拦住去路——这一次,他们没再逃掉。
车厢内挤满了和他们一样大的孩子,有的还穿着校服,有的脸上还残留着墨迹。空气闷热,夹杂着汗味、恐惧,还有不安的沉默。
途中,车队不断停靠、转移,在临时营地中短暂停留。每一次停靠,都有人试图逃跑,也有人永远没能回来。有一个喊着“我要回家”的男孩,被当场带走,枪声响起,姜思章第一次亲眼看到生命在面前消逝。他没有哭,只是紧紧攥着同伴的手,指尖早已发冷。
几天后,他们被送到港口。一艘巨舰停在码头,甲板高耸如墙,像巨兽张口等待吞噬。少年们被赶上船,有人趁乱跳海,子弹随即追上,海面顿时染上血色。姜思章脸色发白,胃里翻涌,却强忍住呕吐。
他被发了一套军装,显然不属于他:袖子盖住手指,裤腿在地上拖着。他看着那身不合身的衣服,沉默地接受了现实,从此他不再是学生,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兵,一个被抓来的“兵”。
天亮时船靠岸,他踏上异乡土地,身边是陌生的命令和旗帜,没有亲人,没有归路。站在队伍中,他忽然意识到,他的人生,已经彻底被改写。入台后,姜思章被分到国民党陆军十八师。每天清晨出操,稍慢一步就挨打挨骂。没人关心他的情绪,也没人记得他不是自愿来的。夜里他常和同样被抓来的王岳清对躺发呆。说话少,想家多。
一次偶然,两人遇上同乡朱彪。朱是自愿从军的,待遇明显好得多。姜思章俩人请他帮忙调离部队。还没来得及递申请,消息就走漏,三人被连长当众痛骂,朱彪还挨了一耳光。
事没成他们没死心,朱彪提议:趁外出洗澡,直接逃。他们跑了,投靠另一支部队,由浙江老乡黄云波带兵。为避追查,黄让他们全改了名字。新部队没那么苦。没人再打他们,饭菜也好点。但广播响起《思乡曲》时,姜思章还是会默默掉泪。
他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他失踪那天,母亲怀着孕,在码头痛哭;祖母听到他被抓的消息后郁病去世。他全都不知道。直到那天,他无意间翻起一张旧党报,准备随便看看打发时间。可当他扫到副刊左下角,一则寻人启事让他僵住了:
“寻子姜文标,浙江岱山人。”姜文标是他的原名。家人还在找他。他记下联系人王先生的地址,用尽办法托人传信回家。几周后,他收到了回信。母亲还活着,父亲也在。家人找了他两年,靠登报才试图找到一点回音。
但他不敢再回信了,台湾开始严查通信,谁和大陆联系,谁就是“通共”。牵连他人是死罪。他知道王先生若被盯上,可能丢命。他咬牙断了信。他活着,但不敢再说“我是谁”。他有名字,却不能用;有亲人却不能见,他只能等。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岛内的国民党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期。但他们并未因此松懈,反而将精力集中在军队内部,开始收紧对基层士兵,特别是那些从大陆被带来的老兵的控制。
新一轮的“整肃”在部队中悄然铺开,“以军作家”的政治宣传运动、“自愿留营”的登记表看似民主,却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强制表演。所谓“自愿”,不过是摆在士兵面前的单选题,不签字就等于自绝出路。
不过姜思章从未真正接受这个“被带到”的身份。他心里清楚:自己从未选择过留下,心始终在故乡。思念如潮水,不断冲刷他对现实的忍耐。他是连队里唯一一个明确表示不愿继续服役的人。他不是为了出风头,只是想回家。
这种“反常”立刻引起了上级的警觉。领导没有立刻发难,却很快“找到了理由”对他下手。一次饭点他和几个老兵在食堂闲聊,说着说着,就有人大声敲着饭桶喊了几句:“没饭了!”本是军营中常见的牢骚话,却被无限上纲,说成是“扰乱军心,煽动兵变”。姜思章首当其冲,被当场关入禁闭室。
也正是从当时开始姜思章开始策划,他偷偷把计划透露给隔壁床铺的士兵,说自己“就是想跑”,还让对方记住这些话,他希望留下一个“证人”,万一成功,也能有人为他说话。年轻的他还抱着一丝幻想,想让“坏人”得到报应。
几天后他真的趁夜翻墙逃走,他一路狂奔,甚至看到不远处车站的灯光时,心跳都快要冲破胸口。但他刚到车站边,就被士兵拦住,当场抓回。对此上级迅速给他安上了“倒卖军用品”的罪名。原因?他身上带着几个气门芯和火花塞,这些都是司机必备的小配件,却在上级嘴里成了他“贩卖军资”的铁证。
他试图辩解,没人听。他试图申诉,毫无回应。几天后罪名坐实,他被送进监狱,刑期三年。监狱是另一个世界,铁栏后是剥夺尊严的地方。但也就是在那里,姜思章遇到了任先生,一位因“思想问题”被关押的中年人。他们在同一个牢房里度过了三个月。
任先生与众不同,说话温和有理,目光透着沉稳。他从不抱怨,只是每天都坚持写信给远在台湾的兄嫂。那是他最后的希望。他说他还有话要交代,还有一个心结未解,只是他不知道还能等来多少时间。
三个月后任先生病倒,没多久便在牢中去世。他最终没等来兄嫂的只言片语。姜思章亲眼看着他咽气时还盯着门口,像在等谁推门进来。任先生的死,像一记重锤砸在姜思章心上。
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在那个时代命运的齿轮不会为任何人停转。他曾幻想过反抗能带来改变,却在现实中看见无力与荒凉。三年刑期,他咬牙熬过。心中的怒火冷却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埋心底的等待,他不再轻举妄动,也不再相信奇迹,只默默等一个能回家的机会。
出狱后姜思章下定决心改变命运。他想进军校当军官,可没正规学历,于是冒险搞了一张假的上海高中毕业证。为了考上,他几乎不眠不休地学,拼尽全力,最后真的考了进去。
军校毕业后,他顺利当上了军官,日子总算安稳了下来,军旅生涯也算平平稳稳地过完了。
退役后他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音乐老师。日子比以前轻松多了,生活也有了着落。条件是有了,他也早就想回家,但那个能让他回去的机会,却一直没等到。
1982年8月11日,姜思章抵达香港。他此行的目的是回大陆,见亲人。中午下机后,他住进陈女士家。第二天在陈女士丈夫陪同下,她前往办理回乡探亲的旅行签证。手续办得意外顺利。签证一拿到他便匆匆搭船去澳门,再转巴士北上广州。
车到珠海拱北口岸时,姜思章心里打鼓。他担心会像在台湾那样,因身份而遭盘查。但令他意外的是,他被请进“台胞接待室”后,一切出奇地顺畅。没有盘问,没有为难。
当工作人员核验完身份,贴上一张“台湾同胞旅行证”时,还低声提醒他一句:“回到香港后可以撕掉,免得回台湾麻烦。”这句话像一股暖流,击中姜思章心底。他从未想过,回家的第一步,竟有人替他考虑得这么周到。
过关后,他一路转乘,风尘仆仆抵达宁波,家终于近了。他先拨通了大妹的电话。不久,二弟也赶来码头。兄妹三人隔着人群认出彼此,一把抱住,抱头痛哭,仿佛要把几十年的眼泪一次流尽。
再乘船去沈家门,母亲已在码头等候。船刚靠岸,他便跳了下去,冲向那瘦小却熟悉的身影,扑通一声跪下:“阿妈,我回来了!”母亲全身一震,扶住他,声音颤抖:“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最后一站,是岱山,他曾在这里被掳走,如今回来,是为了见父亲。那一刻,他走进家门,父亲已经白发苍苍。两人对望无言,姜思章冲过去抱住父亲,泣不成声。三十年,苦尽甘来。
他回来了。消息在村里炸开。那些年一起被抓走的,还有不少人。许多村民上门打听亲人消息。姜思章讲述着当年真相,那些被掩盖、被遗忘、被误解的过往,才终于被重新拼凑出来。
1987年5月,姜思章写下一张传单:《我们已沉默了40年》。开头一句——“难道我们没有父母?他们是生是死,我们不知道。”像一把刀,刺破沉默。30万份传单,5月10日飘满台北街头。十几名老兵举着横幅:“捉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警察冲上前,冲突爆发,媒体哗然。
姜思章没停,又写了一张传单:《想家了,怎么办?》简单六个字,却刺穿所有老兵的心。6月28日,五万老兵挤满大礼堂。当《母亲你在何方》响起,全场跟唱,无人不哭。
两个月后,台湾当局终于松口,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台北红十字会门口排起长队,老兵抱着遗像、拿着老照片,只求一个“回家”。当年他们离开时是青年,再回来,已满头白发。但那一天,他们终于成了“儿子”。
姜思章一次次返乡,陪父母到老送别。他把余生用在一件事上:帮更多人回家。后来他说:“我再也不会做想家的梦了,因为,我已经回来了。”这条回家的路,他走了40年,也为无数人走通了。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没完。家可以回了,国家还没团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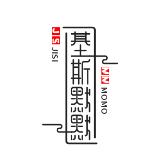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