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6日凌晨,王近山放下望远镜,轻声嘟囔:“活的,一定要活的。”
数小时后,满身油烟的康泽被拖进六纵司令部,他的右臂还濡着黄磷的余温,脸上却看不出决绝,只有惶惑。许多官兵认得这个名字,他们在苏区曾躲过“别动队”的追捕,对这张面孔恨得牙痒。
电报自襄阳飞往西柏坡,毛泽东仅看了两遍便提笔批示:不能杀,送来。十个字,把军委值班员惊得直吸凉气——主席早年言“康泽罪不可恕”,这回却留了活路。
为什么?得倒着解。康泽1904年生于四川安岳,幼时父丧,靠母亲纺线度日。寒窗苦读的少年,踏着泥路考进黄埔三期,碰巧被校长蒋介石翻了翻笔记本,从此列入“重点培养”名单。
二十年代的黄埔左联右合,一边是周恩来筹学生自治,一边是蒋介石圈队伍。康泽选择了后者,还加入“孙文主义学会”,对“反共”三字深以为然。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已是蒋介石的私人参谋。
九一八事变,蒋氏忧心的不是东北,而是南京政权的椅子。他召集十余名亲信密谈,提出要搞“中国版格柏乌”。康泽举手赞成,力推“复兴社”名称。会后,他领到一支番号:别动队。
这支不足三千人的武装特务,被分成几十个小分队往赣闽边界渗透,打着剿共旗号烧庄稼、建“无人区”。兴国、连城的男人一夜间少得惊人,许多老人至死没找到儿子的尸骨,血仇由此结下。
毛泽东回忆苏区失守时叹道:一个蒋介石,一个康泽。这句重话刻在他心里。可到了1948年,他仍决定留下康泽。这不仅是“以德报怨”的姿态,更是一盘统战大棋——战场上赢了枪,场外要赢人心。
押往晋察冀途中,康泽极度紧张,随身只带一本《曾胡治兵语录》。他问押送干部:“我会被游街吗?”对方回:“照政策办,先治伤再谈其他。”这种反差令他愣住——多年鼓吹的“赤匪嗜血”并不存在。
功德林的改造生活并不好受:天天写交代,隔三岔五学习文件,还要劳动。康泽求生欲强,读完《新民主主义论》便写万余字自省稿,称自己“如梦方醒”。真假几分?没人急着下结论,可他坚持写了三年,态度慢慢被认可。
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毛泽东点名康泽和宣统皇帝作例:不杀他们,不是罪不够,而是杀了不利。短短一句,定下宽严相济的国策,也让海内外看清新政权气度。不得不说,这招很管用。
1963年特赦令下达,康泽在狱中几乎跑着去签字。他对来访的沈醉说:“旧日兄弟里,我第一个出去,像做梦。”随后被安置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每月写回忆,不再握枪,却留下几十万字口供,为研究国民党特务史提供原始材料。
有人评价,康泽后半生的笔,比前半生的枪更有价值。确实,那些资料揭开复兴社、别动队的作案细节,让无数隐匿罪行浮出水面,也成了反面教科书。倘若当年一枪了结,这部分史料怕是永远失传。
1967年春,康泽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噩耗传出时,台湾《中央日报》先讶异,继而改口称其为“叛将”。两岸对同一人的标签截然相反,这恰是时代剧变的缩影。
从黄埔学员到“别动队”头子,再到功德林学员,康泽的人生翻了三次面。打仗时,他用铁血手段维护旧政权;败局已定,他又在新制度下延续生命。历史不乏这种极端对比,而决定权往往握在胜利者手中。
毛泽东那句“不能杀”,有人说是政治智慧,有人说是人道情怀。在我看来,更像对未来的投资:若连曾经的刽子手都有出路,普通人自然有活路。这样的心理感召,穿透力远胜枪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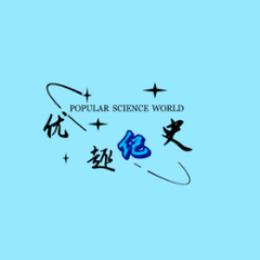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