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同学聚会上,当上科长的情敌赵云锋,当着我暗恋多年的白月光李越的面,把酒杯磕在桌上。
“陈风,没个铁饭碗,你这种南下闯荡的倒爷就是时代的垃圾!”
他以为我是在深圳混不下去的穷光蛋,不仅炫耀着他分房分电视的福利,
更是酒后吐真言,得意地泄露了自己计划。
这引以为傲的“能耐”,也是他能保住自己“铁饭碗”的手段。
我平静地看着他,心里早已有了盘算。
我正准备开口,包厢厚重的木门,被人“砰”的一声,猛地推开。
县长的秘书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目光扫过全场,直直地朝我走来。
秘书对我的一番言语后,赵云锋直接傻眼了...

01
我叫陈风,三十六岁。
1996年的秋天,我坐在一列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上,车厢里的烟味、汗味和方便面混合在一起的、独属于这个年代的躁动气息。
我身上半旧的“的确良”夹克衫,还是三年前离开家时穿的那件。
与我对面那个揣着“大砖头”大哥大、生怕别人看不见的“大老板”相比,我确实显得寒酸。
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深圳那个被无数人称为“小渔村”的地方,
我用五年时间,从一个兜里只剩五十块钱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电子厂、银行户头里趴着七位数的“百万富翁”。
这个词,在老家丰林县,恐怕还只存在于报纸和传说里。
五年前,我爸,拖拉机厂的老车间主任,几乎是拍着桌子让我去厂里“接班”。
那是我们县里无数人挤破头都想得到的铁饭碗。
但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想去南方看看。
他气得半天没说出话,只骂我“鬼迷心窍”。
我妈偷偷抹着眼泪,给我煮了十个鸡蛋。
只有李越,我们厂里最漂亮的女孩,也是我从小的“白月光”,
在送我的时候,往我手里塞了一张手帕,轻声说:“陈风,我相信你。”
她的眼神,支撑了我无数个在深圳睡桥洞、啃冷馒头的夜晚。
这次回来,一是看望父母,二是考察。
我的“风越电子厂”是取我和李越名字里的各一个字,已经到了扩张的时候。
如果能把生产线搬回内地,成本能降一大截。
而我们县那个曾经辉煌、如今却风雨飘摇的拖拉机厂,就是我的首要目标。
“小风?是陈风吧?”
刚下长途汽车,一个熟悉的声音拉住了我。
是住我家隔壁的王婶,她拎着一个菜篮子,正上下打量着我。
“哎哟,真是你!可算回来了,在外面不容易吧?看你都瘦脱相了。”
我笑了笑:“还行,王婶,您身体还好吧?”
“好着呢!”王婶拉着我,压低了声音,开启了她最擅长的信息播报模式,
“跟你说啊,我们大院的骄傲,李越那丫头,现在可是县广播站的台柱子!声音甜得嘞!就是……对象的事还没个着落。
那个赵云锋,你记得吧?当年就跟你不对付的那个,他爸现在是副厂长,他自己在厂里也是个采购科科长,威风得很!
天天开着厂里那辆吉普车,往广播站跑,送的东西都堆成山了!”
我的心,被攥了一下。
赵云锋……我当然记得。
王婶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唉,说起拖拉机厂,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听说都好几个月没发全工资了。
也就是赵云锋他们家,靠着权力,滋润得很。
你们这些同学,现在差距可拉开喽!”
我沉默地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回到家,闻到母亲炖的鸡汤味,我五年来的奔波与疲惫在此时才真正落了地。
父亲看着我,嘴上依旧板着脸,眼神却柔和了不少:
“回来就好,外面不好混,就别出去了。我再去找找老关系,看能不能在厂里给你寻个临时工的差事。”

02
我正想说点什么,家里那台电话机,突然“铃铃铃”地响了起来。
是老同学,刘斌,外号“大嘴巴”。
“喂!陈风?是你小子吗?我靠,你可算回来了!”
电话那头是的咋呼声,“听王婶说你下午到的。别废话,明天晚上,红星饭店二楼包间,老同学聚聚!你可一定要来!”
我犹豫了一下。
“都谁啊?”
“能来的都来!赵科长请客!对了,李越也来!”
刘斌特意加重了语气,“你可得来啊,当年你俩……”
听到李越的名字,我心里那点犹豫瞬间就没了。
我想亲眼看看,她现在好不好。
“好,我去。”
第二天傍晚,我独自走向红星饭店。
这是我们丰林县唯一一家有三层楼的饭店,门口挂着两盏大红灯笼,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气派。
我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混杂着酒香、菜香和人声的热浪扑面而来。
大堂里人声鼎沸,服务员端着盘子穿梭其间。
刘斌早就在二楼楼梯口等着了,一见我,就捶了我一拳:
“你小子,总算来了!快快快,就等你了!”
他领着我推开最里间“牡丹厅”的包厢门。
门开的那刹,我的目光越过满屋子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落在了靠窗的位置。
李越就坐在那里。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没有化妆,如一束清雅的月光。
她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头看来,四目相对的瞬间,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一丝复杂。
她对我轻轻点了点头,嘴角动了动,却没说话。
因为她身边的那个男人,已经站了起来。
赵云锋。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深灰色毛料中山装,胸口的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手腕上那块锃亮的上海牌手表在灯光下闪亮。
他脸上挂着笑容,大步向我走来。
“哟,这不是陈风嘛!”
他声音洪亮道:“我还以为你小子在深圳发了大财,不认我们这些穷同学了呢!怎么,这是混不下去了,跑回来了?”
他上下打量着我那件半旧的夹克衫,眼神里的轻蔑毫不掩饰。
我平静地看着他:“回来看看。”
“看看好,看看好啊!”赵云锋一把揽住我的肩膀,力道大得像是在宣示主权,
“家里总比外面强。你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没关系,同学一场,有困难跟我说!
我在拖拉机厂,大小也是个科长,给你安排个活儿干,还是没问题的。”
他的话引来桌上一些同学的附和:“就是啊陈风,听赵科长的,别在外面瞎折腾了。”
“现在个体户不好干,还是得靠国家,靠单位!”
我不动声色地从他的手臂下挣脱出来,找了个空位坐下。
李越看了我一眼,她端起面前的杯喝了口水,避开了赵云锋投来的得意目光。

03
酒过三巡,赵云锋彻底成了饭桌的中心。
他高谈阔论,唾沫横飞:“不是我吹牛,”
他端着酒杯,站起身来,用筷子指点着桌上的菜,
“在咱们丰林县,就没有我赵云锋办不成的事!上个月,厂里分房子,我第一个挑了套三室一厅的向阳房!
前两天,刚从后勤搞了张处理品条子,一台14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一百块就拿下了!”
“哇,赵科长你太牛了!”
“云锋现在可是我们同学里混得最好的了!”
在一片恭维声中,赵云锋的目光再次锁定了我。
他喝了口酒,脸颊泛红,带着几分醉意教训道:
“陈风,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当年就是太犟,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非要去搞什么投机倒把。
你看看你现在,有什么?户口是临时的吧?档案没地方放吧?以后养老怎么办?看病谁给你报销?”
他顿了顿,声音更大了:“我们这种人,才叫国家的基石!稳定!懂吗?稳定才是一切!
你们这种,就是那水上的浮萍,风雨里的野草,政策的风向稍微变一变,第一个被割掉的就是你们!到时候,哭都找不到地方!”
我夹了一口菜,没有理他。
但我的沉默,似乎更助长了他的气焰。
他转向李越,举起酒杯:“李越,来,我敬你一杯!你是我们县广播站的门面,我呢,是拖拉机厂的中坚力量。我们俩,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
李越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赵云锋,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赵云锋不以为然,反而借势坐到了李越旁边的空位上,
“我说的都是实话!李越,你别听陈风这种人花言巧语。
他今天能在深圳,明天就能去别的地方。他能给你什么?他连自己的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指着我:“陈风,你拿什么跟我比?”
他脸上的醉意更浓,得意地打了个酒嗝,将杯中剩下的白酒一饮而尽。
接着将目光转向了全桌的同学,发表着演说。
“同学们,不是我赵云锋爱说教。”
“我是真心为陈风这样的同学感到惋惜!你们知道吗?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认清形势!”
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用力地挥舞着:
“什么是形势?形势就是,国家还是国家的,单位还是单位的!我们拖拉机厂,是国家的亲儿子!
而他陈风呢?他是个体户,是‘倒爷’!说白了,就是国家的野生儿子!
平时没人管,一刮风下雨,第一个淋死的就是他!”
这番粗俗的比喻引来大家一阵哄笑,几个想巴结他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

04
李越的脸色愈发难看,她放在桌下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
赵云锋很满意地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你们啊,只看到我们厂现在效益不好,人心惶惶。
但你们看不到里面的机遇!这叫什么?这就叫‘改革阵痛’!这就叫‘减员增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他压低了声音,身体前倾道:“不怕跟你们说实话,我们厂里那几条从德国进口的生产线,早就过时了!
效率低,耗电大,还老出毛病。厂里几个老领导早就想处理了,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
为什么?因为直接报废,那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他得意地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但是,我有办法。”
他端起酒壶,给自己又满上一杯,那双因酒精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贪婪:
“我跟南边来的一个大老板已经谈好了。我们先这样,再那样……”
他含糊地比划了几个手势,“让那几条生产线,在一次‘生产事故’里,彻底瘫痪掉。
到时候,再请专家来鉴定,结论就是‘没有维修价值’。这不就合情合理了吗?”
“到时候,几百万买来的德国机器,当废铁卖,十万块钱就能出手!这中间的差价,有多大,你们自己算算!”
整个包间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赵云锋粗重的呼吸声。
所有人都被他这番话震惊了。
我握着酒杯的手,指节已嘎嘎响。
我父亲,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老工人,一辈子都扑在那几条生产线上,把那机器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
而在赵云锋嘴里,它们只是可以用来中饱私囊的废铁。
赵云锋完全没意识到众人神色的变化,他以为大家是被他的“手腕”和“魄力”镇住了,更加肆无忌惮。
他突然扭头,死死地盯着李越:“李越,我知道你爸,李师傅,是咱们厂里最好的老钳工。他所在的那个车间,就是这次‘改革’的重点。
可惜啊,老师傅思想跟不上形势,第一个就要被‘优化’掉。
到时候,提前退休,一个月拿十几块钱的退休金,滋味不好受啊?”
这番话,让李越的脸瞬间血色尽失,嘴唇微微颤抖。
“赵云锋,你……”
“我什么?”赵云锋的笑容变得狰狞而油腻,他甚至伸出手,去拍李越的肩膀,
“不过呢,你放心。只要你跟了我,我一句话的事,就能让你爸从‘被优化’的名单上下来,
调到我们采购科,当个清闲的顾问。怎么样?我够意思吧?”
这已不是暗示,而是赤裸裸的威胁和交易。
用一个老工人一辈子的饭碗,来逼迫他的女儿。
此时我将手中的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正当我准备站起身来,
“砰!”
包厢的红木门,被人从外面猛地一把推开。
一个穿着干部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正扶着门框,气喘吁吁地朝里面张望,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是县长办公室的王秘书。

05
王秘书的突然闯入,整个包间的所有人目光都聚焦他身上。
赵云锋的反应最快。
他脸上的狰狞和醉意在半秒钟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近乎谄媚的、谦卑的笑容。
他赶忙从座位上站起来,抢先一步迎了上去。
“王秘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他一边说,一边熟练地从口袋里掏出“大前门”香烟,恭敬地递上去,
“您来吃饭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安排!是不是王县长有什么指示?”
然而,王秘书只是礼貌性地摆了摆手,拒绝了他的烟。
他甚至没有正眼看赵云锋,只是焦急地扫视着全场,
目光掠过一张张错愕的脸,最终,定格在了我的身上。
在全场人,尤其是赵云锋那难以置信的注视下,王秘书绕过他伸出的手,快步走到了我的面前。
他微微躬着身子,语气里带着十二分的恭敬和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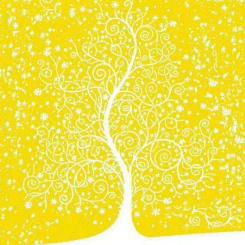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