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血腥气散了,但紫宸殿里的空气依旧是凝滞的。
安史之乱平定,大唐续命。
郭子仪,这个名字的分量,已经重得让龙椅上的唐代宗有些喘不过气。
皇帝对郭子仪的这个称呼,一半是依赖,一半是枷锁。
郭子仪垂手立在殿下,仿佛没听出那声“尚父”背后的忌惮。
他知道,平定叛乱的功劳是他的护身符,也是他的催命符。
这份诡异的平衡,被一个宦官打碎了。
大宦官鱼朝恩,皇帝身边最贴心的“家奴”,最擅长的便是揣摩圣意。
他不需要圣旨,只需要皇帝一个不耐烦的眼神。
消息传到郭府时,郭子仪正在擦拭他那把跟随多年的战刀。
“尚父!”管家连滚带爬地进来,声音都劈了叉:“出事了!咱家……咱家在邠州的祖坟,被人……被人给刨了!”
擦刀的手停住了。
管家哭嚎道:“是鱼朝恩!就是那个阉竖!他派人干的!满长安都传遍了!”
“哐当”一声,战刀落地。
长安城炸了锅。
功臣的祖坟被刨,这是不死不休的血仇。
满朝文武,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汾阳郡王府。
他们都在等,等那个手握重兵、威震天下的郭子仪,会怎样让长安再流一次血。
“郭子仪必反!”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连鱼朝恩自己,也缩在皇宫深处,一边得意于自己的“杰作”,一边又惊恐地等着郭子仪的雷霆一击。
代宗更是彻夜难眠。
他既怕郭子仪反,又隐隐“期待”郭子仪反。
只要他一反,“猜忌”就成了“事实”,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回一切。
三日后,早朝。
郭子仪来了。
他没有披甲,没有带刀,甚至没有穿他那身紫袍的郡王常服。
他穿了一身素白孝服,一步一步,走进了大殿。
鱼朝恩的脸色瞬间惨白。
郭子仪走到大殿中央,没有看鱼朝恩,更没有看皇帝。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重重叩首。
“臣,郭子仪,有罪!请陛下……降罪!”
皇帝愣住了:“尚父……何罪之有?朕……已知你家祖坟之事,朕必为你做主!”
郭子仪抬起头,老泪纵横,声音却洪亮如钟:
“陛下!臣之罪,不在祖坟,在治军!”
他颤抖着指向自己:“是臣领兵在外,杀伐太重,纵容部下。
想必是臣的兵士,曾经刨了别人的祖坟,如今……报应来了!天谴!”
他再次叩首,额头砸在金砖上砰砰作响:“祖坟被掘,非人祸,乃天意!是上天在惩罚臣治军不严!
臣……无颜面对陛下,无颜面对郭家列祖列宗!恳请陛下,削臣官爵,收臣兵权,让臣回乡守陵,日夜忏悔!”
大殿内死一样的寂静。
唐代宗震惊地看着地上那个痛哭流涕的老将。
他想过郭子仪会提刀上殿,想过他会陈兵阙下,甚至想过他会据兵自重,但他唯独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不是“人祸”,是“天谴”?
这句“自领天谴”,把皇帝和鱼朝恩从这件事里摘得干干净净。
他非但没有造反,反而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到了自己头上。
皇帝的猜忌、杀意、和试探,在这一刻,全被郭子仪的“忠诚”和“忍耐”堵了回去。
“尚父……”皇帝走下御座,亲手扶起郭子仪,声音里带着一丝愧疚和后怕,“……是朕,是朕对不住你。”
鱼朝恩瘫在自己的位置上,冷汗湿透了背心。
郭子仪以一种近乎耻辱的“自污”,赢得了这场“掘墓之恨”的胜利,化解了郭氏满门的第一次灭门之祸。
退朝后,郭子仪换下孝服,在王府后院继续擦拭那把战刀。
皇帝的“愧疚”是短暂的,但“猜忌”是永恒的。
“掘墓”风波刚过,一道圣旨便追了下来。
郭子仪“尚父”的尊号未动,“汾阳郡王”的富贵未减,但他手中的兵权,却被“明升暗降”,以“体恤老臣”为由,一点点收了回去。
郭子仪没有半分怨言,交出兵符的那天,他甚至还“病”了一场,以示自己“年老体衰,不堪军旅”。
一代战神,自此赋闲在家。
他脱下了那身浸透了血与火的铠甲,换上了粗布麻衣。
长安城外的汾阳王府别院,他真的开始“种田”了。
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手,如今握住了锄头。
他每日侍弄着那些瓜果蔬菜,仿佛真的成了一个安享晚年的田舍翁。
长安城里的风波诡谲、尔虞我诈,似乎都与他无关了。
他越是“安分”,皇帝就越是“放心”。
郭子仪可以忍,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忍。
“郭令公能忍,我仆固怀恩不能忍!”
仆固怀恩,郭子仪麾下第一悍将,也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
他不像郭子仪那样以退为进,他只知道自己流血拼命,却要受鱼朝恩那等阉人的鸟气。
“阉竖欺我太甚!”

在一场庆功宴上,鱼朝恩的党羽再次当众羞辱仆固怀恩,嘲讽他“有反骨”。
常年积压的愤懑,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仆固怀恩拔刀而起,杀了那名宦官,一不做二不休,反了!
“反”一个功臣,朝廷尚可镇压。
但“逼”反一个功臣,后果是灾难性的。
仆固怀恩在军中威望极高,他这一反,竟裹挟了朔方军的精锐。
更可怕的是,他知道大唐的命门在哪里。
他北上,联络了当年郭子仪的“盟友”——回纥。
他西进,引诱了对长安垂涎已久的“仇敌”——吐蕃。
“我们合兵一处,攻破长安,共享富贵!”
这一次,不再是“内乱”,而是“外患”!
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二十万联军,如山崩海啸般席卷而来。
大唐刚刚从安史之乱中喘过一口气,根本无力抵抗。
京师震动!长安失守!
唐代宗在宦官的簇拥下,继他祖父唐玄宗之后,再一次仓皇逃离了自己都城。
这是大唐立国以来,第二次被外敌攻破首都。
皇帝如丧家之犬,一路逃往陕州。
长安城内,吐蕃人烧杀抢掠,皇室的宗庙被焚毁,宫女妃嫔尽遭凌辱。
在逃亡的土路上,马车颠簸,代宗羞愤欲绝。
他想不通,为什么他倚重的鱼朝恩,在敌军面前不堪一击?为什么他信任的新贵,个个都是酒囊饭袋?
就在这最狼狈、最绝望的时刻,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被他夺了兵权,一个被他默许“刨了祖坟”的老将。
“郭子仪……”皇帝喃喃自语,羞愧、悔恨、恐惧,五味杂陈。
“快!快!”皇帝抓住身边的小宦官,声音嘶哑:“拟旨!拟旨!命郭子仪……不,是‘尚父’!命尚父即刻‘勤王’!朕……朕把兵权还给他!”
圣旨火速送出。
使者快马加鞭,冲到长安城外的别院时,看到的景象让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汾阳郡王郭子仪,那个名震天下的“尚父”,此刻正穿着一身粗布短打,挽着裤腿,满脚是泥,在田垄里……种菜。
“尚父!尚父!长安……长安失守了!”使者滚下马背,带着哭腔喊道。
郭子仪直起腰,接过那份被雨水和汗水打湿的圣旨。
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波澜,只是淡淡地抹去了手上的泥。
“备马,”他对管家说。
“老爷,”管家颤声问,“备……备几匹马?”
“那……兵呢?”
郭子仪抬头,看了一眼长安的方向,那里火光冲天。
“没有兵。”他平静地开口,“陛下只叫我‘勤王’,没给兵。
传我将令,命府中家丁、马夫、伙夫,但凡拿得动刀的,都跟我走。”
他知道,皇帝在逃亡路上,已经无兵可调。
这道圣旨,不是“命令”,而是“哀求”。
他要勤王的,也不是“王”,而是这个摇摇欲坠的江山。
郭子仪没有带任何辎重,只有一袭布衣,一匹老马,以及七八个从王府里凑出来的家丁。
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勤王军”,连千人都不到。
他们星夜兼程,赶到了泾阳。
泾阳,是长安西北的门户,也是吐蕃和回纥联军的必经之路。
当郭子仪登上城墙时,看到的是让他这位征战沙场半生的老将,都感到心寒的景象。
城外,黑压压一片。
吐蕃和回纥的联军加起来,号称二十万。
战旗蔽日,马蹄声如闷雷滚滚,仿佛连空气都被压得凝固了。
而城内,守军不过区区数千残兵,军心涣散,士气低落。
他们不是害怕敌人,是害怕自己被抛弃。
“尚父,”一位年轻的将领声音发颤,“我们……我们真的要守在这里吗?”
郭子仪没有回答,他只是眯着眼,望向远方那如铁桶一般的敌营。
硬守,是死路一条。这数千残兵,连半日都撑不过去。
他必须打破眼前的“必死”之局。
吐蕃人是豺狼,只认利益和鲜血。
但回纥人不一样。
回纥可汗药葛罗,当年曾与郭子仪并肩作战,一同平定安史之乱。
两家曾有“香火情”,甚至唐朝的公主也嫁给了回纥可汗为妻。
“来人,”郭子仪转过身,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压倒一切的决然,“为我取一套,当年在回纥大营中所穿的,无甲常服。”
将领们错愕:“尚父,您要做什么?”
“我自去回纥大营。”

“不可啊尚父!”“二十万大军!单骑入营,必死无疑!”
“若守,则满城皆死;若去,至少……有万一的生机。”郭子仪没有解释,他脱去了象征身份的紫袍,换上了那套略显陈旧的素色衣袍。
他牵出自己的老马,没有带任何随从,只身一人,打开城门。
城门“吱呀”一声,在这片肃杀的平原上显得无比刺耳。
郭子仪策马,缓缓走向回纥大营。
他抵达营前时,被一队回纥骑兵拦住。他
们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衣着朴素的老人,面露疑惑。
“我是郭子仪。”
这四个字,比二十万大军的怒吼更具震撼力。
回纥骑兵立刻将消息传了进去。
片刻后,回纥可汗药葛罗亲自出营迎接,脸上带着复杂的神色。
“尚父!”药葛罗跳下马来,行了一个半生不熟的唐朝大礼,但语气中却透着一丝尴尬和警惕。
郭子仪没有还礼,他直接下了马,步入大营,如同走进自己的家门。
他看到营帐内堆满了从长安城里抢来的金银布帛,以及被掳掠的女子。
郭子仪心中怒火中烧,但他面上不动声色。
他扫视了药葛罗一眼,没有寒暄,直接爆发了。
“药葛罗!你这匹夫!你可知羞耻二字怎么写?”
药葛罗被骂得一愣。
“当年安史作乱,是老夫力排众议,引你回纥入关,平定乱局!我们是盟友,是兄弟!”郭子仪指着他,“你可还记得你当年是怎么对老夫保证的?不烧不杀,秋毫无犯!”
“如今呢?”郭子仪声震屋宇,他指着外面那片吐蕃的营地:
“你竟与吐蕃这等豺狼为伍?你可知吐蕃是大唐的世仇,是你的仇敌!你引狼入室,助仇攻亲!”
“你的王妃,是大唐的公主!你把你的妻子,放在何地?你的誓言,放在何地?”
药葛罗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
他知道郭子仪说的都是事实,回纥之所以与吐蕃联手,不过是觊觎长安的财富,而且是被仆固怀恩哄骗而来。
“尚父,”药葛罗试图解释,“是仆固怀恩说,说你们唐朝皇帝已经……”
“仆固怀恩不过是朝廷的叛逆!他被朝廷逼迫,老夫深知他的苦楚,但你不能助他为恶!”郭子仪打断了他,语气忽然放缓,带着一丝痛心:“你与吐蕃联手,就算得了长安,你猜吐蕃人会不会分你一分好处?”
“不!他们会趁你回纥疲惫之际,反戈一击!你得了大唐的财物,却失了你的信义,更失了你回纥的国运!”
这番话,句句诛心,直击药葛罗的内心。
吐蕃人向来反复无常,他早就对这次联军感到不安。
药葛罗猛地抬头,盯着郭子仪:“尚父,你……你只身前来,难道不怕我杀了你,向吐蕃邀功?”
郭子仪冷笑一声,脱下了身上的袍子,露出里面干瘦的身体。
“你若杀我,你的信义便荡然无存!老夫不过一具尸体,但你回纥却要背负千古骂名!”
他缓缓套上袍子,再次看向药葛罗:“我此来,不是求你。
我来,是问你一句:你是选择信义,还是选择与豺狼共舞,最终被豺狼反噬?”
药葛罗沉默了许久,终于重重一跺脚。
“尚父!药葛罗惭愧!我愿与尚父重续旧盟!”
顷刻间,回纥大营战旗变色。
郭子仪单骑入营,成功策反回纥!
当回纥的大旗转向,猛然杀向吐蕃大营时,城外的二十万联军瞬间炸营。
吐蕃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盟友会在战场上倒戈一击。
郭子仪抓住时机,立刻下令:“全军出击!与回纥夹击吐蕃!”
数千残兵,在老将的指挥下,爆发出了惊人的士气。
吐蕃军被两面夹击,彻底大败,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长安之围,就此解除!
郭子仪再次拯救了大唐。
他以一人之智,换来了数十万将士的性命,换来了大唐的江山社稷。
吐蕃大败,回纥退兵。
大唐的江山社稷,再次被郭子仪从鬼门关前硬生生拉了回来。
唐代宗返回长安,那座被蛮族洗劫过的都城,处处是疮痍,但因为郭子仪,它至少还属于李唐。
在重建的紫宸殿上,皇帝拉着郭子仪的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尚父!朕江山,赖公复存!朕……朕该如何酬你!”

皇帝是真的想赏,但郭子仪已经是:太尉、中书令、汾阳郡王、尚父。
赏钱?郭府富可敌国,金银珠宝堆满了库房。
赏地?他的封地已无可再加,再赏便是裂土分茅,如同藩王。
赏官?他已是文武第一人,再升便是……皇帝。
皇帝在朝堂上陷入了巨大的“赏无可赏”的尴尬。
每多一个赏赐,皇帝心中的猜忌就多一分。
郭子仪也心如明镜。
他功劳越大,皇帝的睡梦中就越是惊雷滚滚。
他谦卑地请求:“臣老迈无用,陛下能让臣安享晚年,便已是最大的恩赐。”
这句“安享晚年”,本是老臣的表态,听在皇帝耳中,却又多了一层深意:“他安享晚年,是否就是想让朕不安享晚年?”
代宗的疑心,如寒冰下的暗流,开始涌动。
郭子仪知道,光凭“掘墓自污”赢得的愧疚已经用光了。
下一次危机,将是致命的。
郭家的权势,也达到了巅峰。
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娶了皇帝最宠爱的女儿昇平公主,被封为驸马都尉。
郭家是臣,李家是君,但通过联姻,两家成了亲家。
正是这份亲近,引来了滔天大祸。
一日,驸马府内,郭暧与昇平公主因琐事争吵。
公主贵为天子之女,言语自然飞扬跋扈:“你一个区区驸马,敢对我大呼小叫?我父是天子,你敢动我一根汗毛?”
郭暧本就年轻气盛,又喝了几杯闷酒,被公主的傲慢激怒,瞬间失去了理智。
他猛地一巴掌扇了过去!
这一声脆响,不仅打在了昇平公主的脸上,更打在了整个大唐的江山上。
公主捂着脸,惊怒交加,尖声哭喊:“你……你竟敢殴打天子之女!我要奏明父皇,诛你九族!”
郭暧此刻酒意上头,被压抑的傲气彻底爆发。
他指着公主,口出狂言,句句如惊雷炸响:
“你以为你父亲是天子?告诉你!我父薄天子不为!”——我爹根本不稀罕当皇帝!
“你!你!”昇平公主瘫倒在地,她不是被丈夫打的,是被这句话吓到了。
这四个字,是彻头彻尾的“谋反”之言!
公主连夜跑回皇宫,哭着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代宗皇帝。
当宫内禁卫军出动,奔向汾阳王府的时候,郭子仪正从外面回来。
他不是去处理军务,也不是去密谋,他只是在长安郊外的戏楼,听了一段新编的曲子。
郭暧酒醒后,惊恐地等着父王处置。
当管家颤颤巍巍地将郭暧那句“薄天子不为”禀报给郭子仪时,郭子仪手里的茶杯瞬间落地,摔得粉碎。
他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丝毫愤怒,只有无边的恐惧。
“蠢材!逆子!”郭子仪一脚将郭暧踹倒在地,不是因为他打了公主,而是因为他说了那句要命的话。
“来人!将逆子五花大绑,立刻押入囚车!”
郭子仪换上朝服,亲自带人押着郭暧,直奔宫门。
夜色中,老将军须发皆白,跪倒在宫门外,重重叩首,声音里带着决绝的悲怆:
“臣郭子仪,教子无方,逆子郭暧,口出狂言,大逆不道,欲行谋反!臣不敢以亲情蔽罪,恳请陛下……处死逆子!并抄没郭氏满门,以谢天下!”
他把自己的儿子推出来,让皇帝杀。
唐代宗闻讯,连夜赶到宫门。他看着跪在地上的郭子仪,看着囚车里瑟瑟发抖的郭暧,心中五味杂陈。
他知道,如果他今天杀了郭暧,就等于承认郭家有反心。
他不仅要失去这个女婿,更要失去天下人对他这位“仁德之君”的尊敬,同时也会让郭子仪的部曲寒心,天下再也无人敢为他卖命。
可如果不杀,天子的威严何在?
代宗沉默了很久,最终,他走到郭子仪面前,亲自扶起了老将军。
“尚父,”代宗叹了口气,眼中尽是疲惫,“俗话说得好,‘不痴不聋,不做家翁’
他摇了摇头,语气和缓下来:“这是小儿女之间的私事,是家事,不是国事。
朕知道尚父的忠心,此言,休要再提!”
郭子仪抬头,看着皇帝眼中那份混合着疲惫、信任、与无奈的眼神,知道自己又过了一关。
皇帝用“家事”的名义,将这桩滔天的“国事”强行压了下去。
郭子仪虽然再次过关,但他知道,代宗的“仁慈”是有限的。
自己以“请死”为代价换来的忠心,终有一天会耗尽。
代宗驾崩,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
新皇甫一即位,就展现出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铁腕和多疑。
他开始大力铲除宦官和旧臣的势力,试图建立一个“清明”的朝堂。
在他眼中,郭子仪这个汾阳王,是旧朝最大的遗留问题。他功高盖世,却又没有实际反叛的证据。
德宗决定,必须在气势上,彻底压倒这个老头子。
贞元初年,德宗设下盛大宴席,召集了所有功勋老臣,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宴席,名为“酬谢”,实为“鸿门”。
郭子仪身着朝服,步入大殿。

他已经八十高龄,走起路来,脚步有些蹒跚,但眼神依旧清明。
德宗皇帝亲自起身迎接,言语间尽是隆重:“尚父!先皇在位时,你两次匡扶社稷,朕今日继承大统,当厚加酬谢!”
宴席过半,气氛也推到了顶点。德宗饮下一杯酒,醉眼迷蒙地看着郭子仪,语气却锋利如刀:
“尚父,天下已定,朕今日为你设宴,酬谢你的定国之功。朕能给的,几乎都已经给了。”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在大殿内回响:“但朕知道,赏赐绝不能辜负功臣的血汗。尚父,你功高盖世,朕……实在不知该如何酬你。你……你可还有什么想要的?”
满朝文武,特别是德宗的新宠、面貌丑陋而心狠手辣的宰相卢杞,都竖起了耳朵。
要钱,皇帝会鄙视他“贪财”。
要地,皇帝会怀疑他“图谋割据”。
要兵符,皇帝会立刻认定他“谋反”。
郭子仪如果说“臣什么都不要”,皇帝反而会更警惕:你想要什么,难道是朕的江山吗?
郭子仪知道,自己的回答,将决定郭氏一族是否能在这位新皇帝手下活下去。
老将军叩首,良久,才颤巍巍地开口。
要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东西,却是皇帝最想听的答案。
“陛下……臣……”他以一种难以启齿又带着“老不正经”的语气,颤颤巍巍地回答:
“陛下……臣……臣年事已高,沙场征战,杀伐太重,气血两亏。”
他停顿,全场都屏息等待。
“臣不要兵符,不要良田,只……只求陛下赏赐。”
皇帝:“哦?尚父想要何物?”
郭子仪脸一红:“只求陛下……赏几房江南来的、美貌能歌善舞的姬妾,为臣……调理阴阳,安度晚年。”
郭子仪的话音刚落,整个紫宸殿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皇帝德宗,脸上的表情经历了一次精彩的变幻。
起初是错愕,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一代战神,再造社稷的元勋,求的竟是女色?
接着是鄙夷,一个贪恋美色的老头子,真是庸俗!
最后,是狂喜!
“准!准!准!”德宗皇帝爆发出一阵震天的狂笑,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
这笑声中,有如释重负,有嘲讽鄙夷,但最核心的是安全。
一个功高震主,却只爱美色和享乐的臣子,对皇帝来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臣子。
“尚父!朕即刻为你遍寻江南!要最美的,最能歌善舞的!朕要让你安享晚年,调理阴阳!”德宗大声宣布,语气中的“恩典”掩盖不住那份轻松。
在场所有人都明白了。
郭子仪要的是“安全”。
阴险的宰相卢杞,原本紧绷的嘴角也放松了,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他本以为能看到郭子仪死在自己要兵权的上奏中,没想到他竟然选择了用美色为自己铺设棺椁。
郭子仪不是说说而已。
皇帝赏赐的姬妾一到,郭府立刻变成了另一番景象。
他要的不是三五房,而是数十房。
这些姬妾,大多是江南选来的美人,能歌善舞,莺莺燕燕。
汾阳王府内,终日歌舞升平,丝竹之声不绝。
郭子仪将这份“荒唐”执行到了极致。
他深知,德宗皇帝的猜忌不会因为一场朝堂对话就消失,皇帝还需要“证据”来证明他真的老了,真的“无英雄之气”了。
德宗皇帝派来的“眼线”混入郭府,扮演着家丁、仆役甚至侍卫的角色。
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收集情报,确认郭子仪是否真的“沉沦”。
眼线们看到的,正是皇帝最想看到的景象:
郭子仪半卧在雕刻精美的软榻上,任由姬妾们嬉闹喂食。
偶尔有公文送来,他也只是心不在焉地瞄一眼,随手扔在一旁,继续听曲。
郭子仪对钱财的贪婪似乎也达到了顶峰。
各路节度使送来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他来者不拒,甚至主动索要。
金银珠宝堆在走廊上,堆满了库房,他示人以“贪财”,让皇帝知道他所有的心力都用在了积累财富上。
郭子仪身边永远不缺美人,他似乎在极力弥补多年沙场征战的“损失”。
他与姬妾们嬉戏打闹,言语轻浮,完全是一副荒淫无度的模样。
眼线将这些密报源源不断地送入宫中。
“郭令公正在王府内,和新来的姬妾在后花园蹴鞠嬉闹,根本不理会朝中风云。”
“郭令公收下了河东节度使送来的三箱夜明珠,正指挥家丁清点。”
“郭令公沉迷享乐,已无英雄之气,只求调理阴阳,安心度过晚年。”
德宗皇帝听着这些密报,终于彻底放松了警惕。
“郭子仪,不过如此。”德宗冷笑一声,将奏折扔在桌上。
在他眼中,郭子仪不再是那个能单骑退回纥的战神,而是一个“好色”、“贪财”、“昏聩”的荒唐老臣。

一个追求享乐的人,是不会想要江山的。
郭子仪,这位被天下敬仰的尚父,以自己最高的荣耀和最后的尊严为赌注,赢得了郭氏满门的绝对安全。
他用荒唐的晚年,换取了皇帝的放心。
郭子仪的“自污”妙计虽然为郭家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但家族内部的危机并未完全解除。
郭府终日歌舞升平,但郭子仪每日听曲饮酒,却如饮鸩止渴,心中始终悬着一把刀。
这把刀,再次从家里落了下来。
这一次,仍旧是他的儿子,驸马郭暧,与昇平公主。
自上次“醉打金枝”之后,郭暧对自己的岳父心有余悸,对父王的教诲铭记在心,再也不敢口出狂言。
昇平公主毕竟是天子之女,虽然上次被皇帝按下了“国事”的定性,但骨子里的骄纵并未完全磨平。
又一次争吵发生。起因微不足道,无非是驸马府的用度或奴婢的管教。
公主再次拿出她无往不利的武器——身份。
“郭暧!你别忘了,你不过是臣子之子,我是天子之女!你我之间,永远隔着君臣之别!”
郭暧被刺激得脸色铁青。他忍耐着,但公主却步步紧逼,言语极其刻薄,直刺郭暧的痛处。
“你父郭子仪,功高震主,如今不过是靠着姬妾和装疯卖傻苟延残喘,若非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你郭家早就……”
“够了!”郭暧怒吼一声。
他没有再动手,而是红着眼睛,指着公主:“你知道我父有多难吗?他一生忠君报国,如今却要靠装作一个老色鬼才能保全我们!”
“你以为你爹是天子就能为所欲为?你以为我父真的只是贪图女色吗?那是因为……”
郭暧及时收住了嘴。他意识到自己差点说出更致命的话,但愤怒的火焰已无法熄灭。
他摔门而出,直奔城外王府,去向父王请罪。
当郭暧冲入王府别院时,看到的景象是:
郭子仪正半倚在榻上,听着新来的两位姬妾弹唱琵琶。他闭着眼睛,表情慵懒而满足,面前摆着一盘刚送来的荔枝。
郭暧跪倒在地,声音哽咽:“父亲!儿臣……儿臣这次虽然没有动手,但又与公主有了争执,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郭子仪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没有理会郭暧说了什么,他只知道:又有冲突了。
他那副荒淫、松弛的伪装,瞬间被击得粉碎。
他猛地推开身边的姬妾,老迈的身体带着一股不符合年龄的迅捷,冲到郭暧面前。
“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他揪着郭暧的衣领,双目圆睁,仿佛下一秒就要将这个儿子撕碎。
郭暧惶恐地将争吵的细节说了一遍,唯独隐去了公主提到“装疯卖傻”的那部分。
郭子仪听完,脸色由青转白,再转为铁青。
他知道,哪怕只是普通的争执,在德宗皇帝的眼中,都会被放大成对皇权的藐视。
他立刻再次下令,将郭暧五花大绑。
这一次,他没有等公主去告状,没有等皇帝下旨。
他亲自驾着囚车,带着捆得结结实实的儿子,连夜奔赴宫门。
他再次跪倒在宫门外,如上次一样,请罪求死。
这一次,前来迎接他的不是代宗,而是更加冷酷的德宗。
德宗皇帝看到这一幕,内心是极其复杂的。
他看到那个“沉迷女色”的老头子,竟然为了儿子的“家事”,再次亲自来宫门外“请死”。
“尚父,”德宗的声音有些沙哑,他扶起郭子仪,“何至于此?不过是小儿女的争吵。”

“陛下!”郭子仪老泪纵横,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来表演自己的“忠诚”和“卑微”。
“家国一体!老臣教子无方,酿成大祸!陛下可以对老臣不忍,但不能对朝纲不忍!”他表现得比皇帝还要维护李唐的威严。
德宗凝视着郭子仪,看着他脸上那份真实的恐惧和决绝。
他知道,如果郭子仪真有谋反之心,绝不会如此卑躬屈膝地请杀自己的儿子。
皇帝的心中,那份针对郭子仪的最后一点疑虑,彻底烟消云散。
他叹了口气,重复了父亲当年的话,但语气中却带着一丝无奈和钦佩:
“罢了!尚父请起!*不痴不聋,不做家翁。朕恕郭暧无罪,尚父不必再提!”
郭子仪叩首谢恩,如蒙大赦。
他带着被释放的儿子,离开了宫门。
德宗站在宫墙上,看着郭子仪远去的背影。
他知道,自己又被这个老头子“表演”了一次。
但他也知道,郭子仪是真心忠于李唐的江山,而非李唐的皇帝。
郭子仪以近乎自残的方式,彻底封死了德宗皇帝对郭家的杀心。
贞元年代,汾阳王府成了长安城一道奇景。
它并非奇在奢华,而是奇在敞开。
自从郭子仪在朝堂上“乞求姬妾”之后,他便将“自污”推向了最高境界。
他索性下令:王府四门大开,不设门卫,任凭人出入。
这在权贵之家是匪夷所思的。
哪家公侯没有几分见不得人的秘密?
可郭子仪就是要让皇帝的眼线、宦官的党羽,甚至贩夫走卒,都亲眼看看:郭府内,除了歌舞和脂粉气,没有任何谋反的迹象。
皇帝派来的眼线大摇大摆地在王府内走动,他们看到的,是尚父拥着美人,醉眼朦胧,甚至在批阅奏章时,也让姬妾替他磨墨、揉肩。
“郭令公真的老了,他沉迷在温柔乡里,再也无心江山了。”这是每一个眼线送回的报告中的核心结论。
郭子仪的“昏聩”表演得如此成功,以至于他的儿孙们都开始信以为真。
他们私下议论,老将军真的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消磨了心智。
这份荒唐而安全的生活,在一天下午被一道拜帖打破。
“尚父,宰相卢杞求见。”
郭子仪正躺在榻上,听着新来的姬妾弹奏一曲哀怨的胡笳。
他眯着眼睛,仿佛即将入睡。
但听到“卢杞”二字,他那双老迈的眼睛,骤然睁开,射出两道寒光!
他猛地坐起身,将手中的玉如意摔在地上,发出了刺耳的碎裂声。
“快!快!立刻将府内所有姬妾、乐师,全部藏起来!一个不留!”郭子仪厉声喝道,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恐慌。
姬妾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花容失色,侍奉的家丁更是摸不着头脑。
“尚父!您……您这是做什么?”管家惊愕不已,“连皇帝的眼线都能进来,为何独独要躲避卢宰相?”
“不必多问!快!”
郭子仪以最快的速度,让整个王府瞬间“清场”。
歌舞声戛然而止,脂粉气被迅速驱散。
他换上了最朴素的朝服,坐姿端正,如同临大敌。
当卢杞被引入大殿时,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清净、肃穆,甚至有些简朴的王府,以及一个眼神清亮、气度沉稳的郭子仪。
卢杞此人,不仅心狠手辣,貌相更是丑陋。
他身体矮小,面容猥琐,一看便非善类。
郭子仪对卢杞的接待,达到了空前的礼遇。
他亲自相迎,言语毕恭毕敬,甚至对卢杞的任何一个提问,都回答得滴水不漏,毫无错漏。
他谈论的,都是些边疆军情和国政要事,仿佛之前那个沉迷女色的人根本不存在。
卢杞带着满腹的疑团离去。
他本想借着郭子仪的荒唐做文章,却发现这个老头子,比朝堂上的任何人都清醒。
卢杞走后,被藏在后院的姬妾们和管家才敢出来。
姬妾们纷纷抱怨,不知道为什么独独要躲着那个“丑陋”的宰相。
郭子仪叹了口气,挥退了其他所有人,只留下了自己的儿子和贴身管家。
他缓缓坐下,喝了一口凉茶,疲惫的眼神中,透露出彻骨的清醒。
“你们以为,我郭子仪是真的贪图那几房姬妾?”

“你们以为,我郭子仪是真的老到昏聩,不知道那卢杞的来意?”
郭暧和管家面面相觑,不敢吱声。
“那卢杞,相貌丑陋,心胸却狭隘至极,睚眦必报。”郭子仪的声音低沉而充满警告,“你们想想,若是方才,府内的姬妾见他貌陋,忍不住窃笑一声,或是露出了半点鄙夷之色……”
郭子仪停顿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杀气:“他日,卢杞若得势,他不会来针对我郭子仪的功劳,他只会记住那一笑的羞辱!”
“他会以姬妾失礼、教导无方为由,诬我为老不尊,进而诬蔑我郭家蔑视朝廷,藐视宰相。
他灭我郭氏满门,只需要一个‘姬妾的轻笑’,就足够了!”
郭子仪指了指那些姬妾,语气沉重:
“我乞求姬妾,让天下人以为我好色,是自污,是我的保命符。
但我让她们时刻侍奉左右,却是在告诉皇帝:我的心力,都在女人身上。”
“可若是让那心胸险恶的卢杞见到了她们……”郭子仪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血光之灾,“你们是我用来‘保命’的,不是用来‘送命’的!”
所有人都彻底明白了。
在德宗皇帝“放心”的眼光中,郭子仪继续着他荒唐的晚年生活,直到八十五岁高龄,安然寿终正寝。
临终前,郭子仪的精神忽然变得无比清明。
他叫来所有的儿子,交代了最后的遗言。
他没有分配金银珠宝,他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他吩咐儿孙们,要善待府内所有姬妾。
她们不是物件,是郭家安享富贵的功臣。
第二,他命管家取出府中所有的“兵符”、“诏书”,包括当年代宗皇帝赏赐的空头兵权、德宗皇帝赏赐姬妾的诏书、以及历代皇帝的恩旨。
“这些东西,不能留。”
他颤巍巍地嘱咐:“待我死后,尔等立刻将其全部上交朝廷,一丝不留!”
“功劳”可以入史册,“兵符”和“诏书”却可能成为“罪证”。
他要让皇帝看到,郭子仪连死,都将忠心刻在了骨子里。
郭子仪八十五岁寿终,这在唐朝,几乎是罕见的“富贵寿考”的圆满结局。
德宗皇帝闻讯,悲痛得几乎不能自已。
他为郭子仪废朝五日,亲临哭祭,谥号忠武。
这是天子对臣子能给予的最高规格的哀荣。
与他同时代的英雄,命运却凄惨无比:
李光弼是与郭子仪齐名的名将,却终生被猜忌,郁郁而终,死后留下遗言,连棺木都不敢用皇家的制式,生怕被皇帝追究。
仆固怀恩是个不懂政治的武夫,被宦官羞辱,最终被逼造反,落得身死族灭。
宰相卢杞最终因触怒德宗,被贬斥至死,结局凄凉。
唯有郭子仪。
这位在世人眼中“贪财好色”、“沉迷姬妾”的“荒唐”老臣,却是这血色棋局中,唯一活到最后、笑到最后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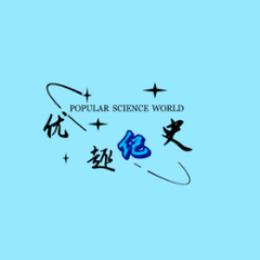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