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城的龙椅是用尸骨堆出来的,坐上去的人都觉得烫。
朱全昱把那枚决定生死的骰子砸了个粉碎,只想在必死的棋局里给全家求个活路。
世人都道他是憨傻的农夫,殊不知,他只是他想让所有人看到的。
开平元年的汴梁城,空气里似乎都飘着一股子新漆和陈血混合的味道。
刚落成的大梁皇宫金祥殿外,文武百官按照品阶,像被墨线弹过一样,排得整整齐齐。
每个人的腰都躬成了一张绷紧的弓,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惊扰了殿内那位即将登基的新皇。
偏偏在这肃穆的死寂中,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叫嚷声。
“慢点!慢点!这可是咱家那头老叫驴拉的,弄坏了轮子,回头种地用啥?”
宫门口的禁军侍卫面面相觑,手里的长戟不知道该不该架起来。
只见一辆只有乡下运粪才用的破板车,吱吱呀呀地停在了汉白玉铺就的御道前。
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半老头子,头发花白,胡乱挽了个髻,插着根不知哪儿折来的荆条。
身上那件灰布棉袄,袖口磨得发亮,上面还沾着几点没干透的黄泥印子。
跟在后面的年轻人却是一脸窘迫,他是朱全昱的长子朱友谅。
此刻他正拼命扯着身上那件并不合身的新锦袍,压低声音抱怨道:“爹!这是皇宫!三叔……不,陛下的登基大典!

您怎么穿这身就来了?快把那件紫蟒袍换上啊,那是宫里特意送来的!”
“穿个屁!”朱全昱回身就在驴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那是他平时赶牲口的习惯动作,在这皇宫门口显得格外滑稽,
“那蟒袍穿着跟裹尸布似的,勒得慌。
再说了,咱是来走亲戚的,又不是来唱戏的。”
“爹!这是朝廷,不是走亲戚!”朱友谅急得直跺脚,脸涨成猪肝色,甚至不敢看周围那些官员投来的鄙夷目光。
“啥朝廷?那是朱三!”朱全昱瞪了儿子一眼,那眼神浑浊且固执,像极了村口那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他就是穿上龙皮,那也是我看着光屁股长大的朱三!”
此时,吉时已到。
沉闷的钟鼓声从城楼上传来,震得人心头发颤。
殿门大开,礼官拖着长腔高喊:“百官进殿”
群臣鱼贯而入,衣冠楚楚,佩玉叮当。
朱全昱混在最前列的皇亲国戚队伍里,那身灰布棉袄在一堆锦绣堆里,扎眼得就像落在绸缎上的一坨苍蝇屎。
金祥殿内,在此刻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朱温一身崭新的赤黄龙袍,头戴通天冠,端坐在高高的御座之上。
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流寇草贼,那股常年杀伐积淀出的威压,让下方的臣子们膝盖发软。
礼部尚书战战兢兢地出列,正要宣读早就写好的、歌颂尧舜禅让的骈文。
一声极其突兀、带着浓重砀山乡下口音的喊声,硬生生打断了尚书的起势。
那声音没有丝毫的敬畏,反而透着一股子隔着地垄沟喊人吃饭的随意。
满朝文武瞬间吓得魂飞魄散,齐刷刷地跪了一地,不少人甚至已经在心里替这个不知死活的狂徒默哀。
朱全昱没跪。
他不仅没跪,还往前溜达了两步,眯着那双似乎有些老花眼的眼睛,仰头打量着高高在上的朱温,又指了指那金光闪闪的龙椅。
“朱三啊,”朱全昱双手揣在棉袄袖子里,吸了吸鼻子,声音响亮地回荡在大殿里,“这椅子看着硬邦邦的,还是凉的吧?你这老寒腿受得了吗?坐那上面不硌屁股?”
比刚才更可怕的死寂。
跪在地上的长子朱友谅已经吓瘫了,整个人抖得像筛糠,额头死死抵在金砖上,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御座上的朱温,那张阴鸷的脸皮微微抽搐了一下。
他的目光像两把刀子,在自己这个看起来憨傻粗鄙的大哥身上刮了两遍。
片刻后,朱温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哈哈哈!朕的大哥,还是这般……淳朴!”
朱温站起身,故作大度地挥了挥手,“大哥是乡下人,不懂宫里的规矩,朕恕你无罪!赐座!给广王搬个软垫子来!”
群臣这才松了一口气,纷纷跟着赔笑,口中称颂陛下仁德,兄友弟恭。
在一片虚假的祥和中,朱全昱一屁股坐在了内侍搬来的锦墩上。
他依然揣着手,看似憨厚地咧嘴傻笑,目光却越过层层叠叠的人群,落在了角落里几个神色复杂的前朝降臣身上。
大梁皇宫的建昌殿内却是灯火通明,亮如白昼。
手臂粗的红烛燃得噼啪作响,舞姬们的水袖甩得如同天上的流云,但坐在席间的皇亲国戚们,却个个背挺得笔直,连挟菜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这不仅仅是一场家宴,更是新皇朱温的一场“服从性测试”。
酒过三巡,朱温似乎觉得歌舞乏味,挥手屏退了舞姬,命内侍端上来一只打造得极尽奢华的金盆,又让人拿来一副象牙骰子。
“干喝无趣,”朱温满面红光,解开了领口的盘扣,露出一撮花白的胸毛,那股子草莽习气在酒精的催化下暴露无遗,“来,咱们自家兄弟,博两把!”
众亲戚面面相觑,随即爆发出一阵整齐划一的叫好声。
谁敢扫皇上的兴?
与其说是赌局,不如说是献媚。
侄子朱友贞手里捏着一把好牌九,却故意打得稀烂,输了银子还要赔着笑脸夸:“父皇洪福齐天,儿臣这手气是被父皇的龙气给震住了!”
其他几个堂兄弟也是如此,哪怕掷出了豹子,也得想办法动动手指,把点数拨弄小了,生怕赢了皇帝一文钱。
朱温赢得哈哈大笑,面前的金银堆得像座小山。
他其实不在乎这点钱,他在乎的是这种“天下予取予求”的快感。
唯独坐在末席的朱全昱,像个局外人。
他面前只放了寥寥几十文铜钱,每一把下注都抠抠搜搜,还要拿手指头沾着唾沫数两遍。
输了一文钱,那脸上的肉都要疼得哆嗦一下。
朱温瞥了一眼大哥,眼中闪过一丝戏谑。
他抓起那副象牙骰子,在掌心哗啦啦地摇着,高声道:“大哥,你那点出息!几十文钱也值得你那般算计?来,这把朕押大的,你敢不敢跟?”
朱全昱抬起眼皮,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此刻布满了血丝。
他喝了不少酒,脸红得像关公。
“跟!咋不跟!”朱全昱猛地把面前仅剩的一把铜钱拍在桌案上,动作粗鲁得震翻了酒杯,“我就不信,你朱三能把把通吃!”

骰子落入金盆。
叮叮当当的一阵脆响后,骰子停住了。
六、六、六。
三个鲜红的六点,刺目惊心。
“豹子!通杀!”内侍尖细的嗓音喊道。
满座皆惊,随即是雷鸣般的马屁声:“陛下真乃天命所归!连骰子都听陛下的号令!”
朱温得意到了极点,他伸出手,准备去揽桌上所有的筹码,大笑道:“大哥,看见没?这就叫天命!这天下是朕的,这赌桌也是朕的!你想赢朕?下辈子吧!”
就在朱温的手指即将碰到那堆铜钱的一瞬间,一只枯瘦却有力的大手,突然斜刺里伸了出来,一把抓住了那两颗还在微微晃动的象牙骰子。
全场瞬间死寂。
朱全昱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他死死盯着朱温,胸膛剧烈起伏,像是风箱在拉扯。
“大哥?”朱温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眼神瞬间阴沉下来,“你醉了。”
“我没醉!”
朱全昱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猛地扬起手,将那副价值连城的象牙骰子狠狠砸向了面前那个硕大的金盆!
“当!!!”
一声巨响,震得所有人耳膜生疼。
脆弱的象牙在坚硬的金盆壁上撞得粉碎,白色的碎屑飞溅而出,有一片甚至崩到了朱温的脸上,划出一道细细的血痕。
“朱三!你个贪得无厌的杀才!”
朱全昱指着朱温的鼻子,唾沫星子喷了皇帝一脸,声音嘶哑而凄厉:
“你在外面杀人放火,篡了李家的社稷,如今关起门来,连自家人这点买棺材的铜钱都要赢光吗?!
天底下的便宜都让你占尽了,你就不怕把朱家的祖宗福分都给折腾绝了吗?!”
此言一出,满殿皆惊。
长子朱友谅两眼一翻,直接吓晕了过去。
周围的内侍和禁军“哗啦”一声拔出了横刀,只等陛下一声令下,就将这个狂徒乱刃分尸。
朱温坐在龙椅上,脸上的血痕缓缓渗出一颗血珠。
他没有擦,只是死死盯着这个平日里最窝囊的大哥。
那一刻,他眼中的杀意几乎凝成了实质。
但朱全昱毫无惧色。他披头散发,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又像个疯癫的预言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案几。
角落里,负责记录起居注的史官,手颤抖了一下,笔尖在纸上晕开一团墨迹。
他抬头看了一眼那个疯癫的老人,咬了咬牙,在史册上记下了一行字:
帝博戏不亦乐乎,全昱怒掷骰盆,斥帝贪虐。
第二天酒醒,圣旨就到了。
传旨的是朱温身边最得宠的大太监敬翔。
他捧着那卷明黄色的锦轴,身后跟着两队捧着金银冠冕的宫女,满脸堆笑地站在驿馆那破败的院子里。
“……皇兄全昱,性行纯良,特封广王,食邑三千户,赐紫金蟒袍,钦此!”
敬翔念得抑扬顿挫,念完后,笑眯眯地把圣旨往前一递:“王爷,接旨吧?
这可是陛下天大的恩典,满朝文武除了几位皇子,谁有这待遇?”
朱全昱正蹲在台阶上喝粥,手里捏着半块咸菜疙瘩。
他没接圣旨,而是斜着眼瞅了瞅那托盘里的金印,伸手掂了掂,眉头皱成了个“川”字。
“三千户?”朱全昱把咸菜塞进嘴里,嚼得嘎吱响,“那一年能给多少粮食?”
敬翔愣了一下,赔笑道:“王爷说笑了,这食邑是虚封,朝廷每年给您发俸禄,折银五千两,绢一千匹……”
“才五千两?”朱全昱“呸”地吐出一口菜渣,猛地站起身,一脸被坑了的愤懑,“我在砀山老家,那几百亩上好的水浇地,加上那片果林子,风调雨顺的时候一年也不止这个数!
还得天天在京城受那个活罪?不干!这买卖亏本!”
敬翔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捧着圣旨的手有点抖:“王爷,这可是抗旨……”
“抗个屁的旨!”朱全昱顺手抓起那卷圣旨,拿在手里跟卷大葱似的比划了两下,然后竟垫在了那条瘸腿的板凳底下,
“这玩意儿还没我家糊窗户的纸厚实。
你去告诉朱三,他那些虚头巴脑的王爷谁爱当谁当,我要回家收麦子了!”
说完,他冲着屋里早就吓瘫的一家老小吼了一嗓子:“都愣着干啥?收拾东西!哪怕是一个破碗也别给朱三留下,那都是咱家的家当!”
半个时辰后,汴梁城的百姓看见了奇景。
刚刚被封为广王的皇兄,拖家带口,赶着那辆拉粪的驴车,车上堆满了铺盖卷、锅碗瓢盆,甚至还有两只咯咯叫的老母鸡,像逃荒一样往城门口冲。
消息传回宫里。
朱温正在批阅奏折,听完敬翔的汇报,把笔狠狠摔在桌上:“他真这么说?嫌王爷俸禄低?”
“千真万确。”敬翔擦了擦头上的汗,“广王……不,朱全昱还把陛下赏的那些御酒都倒了,说是空坛子留着回去腌咸菜,酒太辣嗓子,带着压秤。”
“蠢货!烂泥扶不上墙!”朱温骂了一句,眼底的那抹杀意却悄悄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鄙夷,“让他滚!滚得越远越好,省得在京城给朕丢人现眼!”
“那……还派人护送吗?”
“送个屁!派一队禁军远远跟着,看着他出那道黄河渡口。
朕倒要看看,他是不是在装疯卖傻。”
汴梁北门外,黄河古渡。
朱全昱一家的驴车刚上船,后面尘土飞扬,一队杀气腾腾的禁军铁骑就追了上来,领头的校尉高喊:“广王留步!陛下有令,王爷身体尊贵,不可轻离京畿!”
船上的朱友谅吓得差点跳河:“爹!追兵来了!三叔反悔了!”
朱全昱回头看了一眼那队骑兵,那是朱温的试探。
“慌什么!”
朱全昱猛地从怀里掏出昨天朱温为了安抚他赏赐的一包金瓜子。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他像个疯子一样,把那把金灿灿的瓜子朝着岸边的码头人群狠狠撒了出去!
“抢啊!皇帝赏的金子!谁抢到是谁的!”
码头上原本等着过河的几百号难民和脚夫,瞬间炸了锅。
金子的诱惑让人失去了理智,人群疯了一样涌上去哄抢,瞬间把通往渡口的栈桥堵得严严实实。
那队禁军被汹涌的人潮死死挡在外面,马匹受惊嘶鸣,根本冲不过来。
“我的金子啊!我的钱啊!”朱全昱站在船尾,一边撒一边捶胸顿足,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朱三!你不想让我走,我就拿你的钱买路!这日子不过了!”
渡船离岸,缓缓驶向对岸。
透过混乱的人群,禁军校尉看见那个疯老头正趴在船舷上,心疼地看着落入水中的几颗金瓜子,那副贪婪又狼狈的模样,哪里有一点皇亲国戚的样子?
校尉收回了扣在弩机上的手指,对身边人冷笑道:“回去复命吧,就是个贪财的老疯子,杀他都嫌脏了陛下的刀。”
浑浊的黄河水面上,朱全昱依旧在嚎啕大哭。
只是当他低下头,将脸埋进那散发着霉味的旧棉被里时,那双泪眼却瞬间变得清明无比,冷冷地盯着河水中那个正在远去的、倒映着的汴梁城。
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来这座城。
好在,他活着出来了。
回到砀山的日子,沉闷得像口棺材。
曾经热闹的朱家庄如今大门紧闭,朱全昱下了死命令:全族守孝,闭门思过,谁敢迈出庄门一步,打断狗腿。
虽然朱家并没有死人,但这道命令没人敢不听。
只是那股怨气,像发霉的谷子一样在庄子里从早馊到晚。
长子朱友谅这几天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不喝。
他想不通,明明自己是当朝皇帝的亲侄子,是大梁的衡王,为什么还要窝在这穷乡僻壤里,闻这满院子的鸡屎味。
直到第三天深夜,一个黑影悄悄翻进了后院。
那是朱温留在砀山的暗桩,送来了一封密信。
信里只有一句话:“若有一人心向大梁,即可回京享福。”
朱友谅看着那封信,眼里的贪婪像鬼火一样烧了起来。
他当即召集了几个平日里最不安分的族弟,打点了行装,准备趁着夜色偷偷溜出庄子,奔向那个金碧辉煌的汴梁。
“大哥是不是疯了?”族弟朱全能一边系马肚带,一边小声嘀咕,“放着王爷不当,非要回来种地。”
“他是老糊涂了!”朱友谅咬牙切齿,把那封密信揣进怀里,“他不肯去,咱们去!等见到了三叔……见到了陛下,我定要参他一本,说他老迈昏聩,不识天恩!”
几人正准备拉开后门的门栓。

“咣当”一声。
一把生锈的大铁锁,重重地砸在了门前的青石板上,溅起一片火星。
朱友谅吓得一哆嗦,猛地回头。
只见火把骤然亮起,将后院照得通明。
朱全昱站在院子中央,手里提着一根早已备好的、手腕粗的枣木棍。
他身后站着几十个庄子里的老长工,个个手持扁担锄头,面无表情地堵住了所有的去路。
“爹……你……你怎么还没睡?”朱友谅心虚地往后退了一步,手下意识地捂住了胸口的密信。
朱全昱没说话,那张平日里总是挂着憨笑的脸,此刻阴沉得像要滴出水来。
他一步步走近,目光死死盯着儿子的胸口。
“拿来。”朱全昱伸出手。
“拿……拿什么?”
信被搜了出来。
朱全昱看都没看,直接扔进火把里。
火苗舔过信纸,瞬间化为灰烬。
“把他拖到宗祠去!”
朱家宗祠,列祖列宗的牌位在摇曳的烛光中显得格外森严。
全族老少都被叫醒了,黑压压地跪了一地。
朱友谅被五花大绑按在祖宗牌位前的长条凳上,嘴里塞着破布,拼命挣扎,眼珠子瞪得都要裂开了。
朱全昱拖着那根枣木棍,走到列祖列宗面前,上了三炷香,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起身时,他转过身,看着那个还要挣扎的儿子,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只有一种令人胆寒的疲惫。
“友谅,别怪爹。”
朱全昱的声音很轻,轻得只有离得最近的几个人能听见,“腿断了,养半年就能下地,头断了,神仙也接不上。”
朱友谅似乎听懂了什么,剧烈地摇头,喉咙里发出“呜呜”的求饶声。
朱全昱闭上了眼睛,深吸一口气,手中的枣木棍高高扬起,
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在这个寂静的深夜里清晰得如同惊雷。
“唔!!!”
朱友谅的左腿呈现出一个诡异的弯曲角度,剧痛让他瞬间翻白了眼,身子猛地挺直,然后像条死鱼一样软了下去,昏死在长凳上。
跪在地上的妇孺们尖叫起来,族人们吓得瑟瑟发抖,看着那个平日里老实巴交的族长,仿佛看着一个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
“都看清楚了!”
朱全昱扔掉沾血的棍子,指着昏死的儿子,对着全族人厉声咆哮:“这就是想当王爷的下场!从今往后,谁再敢提‘去汴梁’三个字,下场比他还惨!”
就在这血腥味弥漫、全族惊恐未定的时刻。
“啪、啪、啪。”
宗祠的大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不紧不慢的鼓掌声。
“好一出大义灭亲啊。”
大门被粗暴地推开,寒风裹挟着雪花卷了进来。
一队身披重甲、手按横刀的禁军,像黑色的潮水一样涌入宗祠,瞬间包围了所有人。
领头的,正是负责监视朱全昱的禁军统领。
他跨过门槛,皮靴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统领看了一眼昏死过去的朱友谅,又看了一眼满手是血、气喘吁吁的朱全昱,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意。
“广王殿下,陛下派末将来看看您过得安不安生。
没想到刚到门口,就看了一出好戏。”
统领的手缓缓按在刀柄上,眼神像毒蛇一样在朱全昱身上游走,语气咄咄逼人:
“只是末将不懂,陛下刚刚下旨招揽人才,您就把大公子的腿打断了。
您这是在清理门户呢,还是在……演一出苦肉计,给陛下的圣旨还要添上一笔‘抗旨不遵’的罪名呢?”
这一问,诛心。
如果是清理门户,那就是不给皇帝面子;如果是苦肉计,那就是欺君之罪。
横竖都是死路。
全族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朱全昱缓缓抬起头,用那双布满血丝、看似癫狂实则清醒得可怕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统领。
他突然咧开嘴,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发出了“嘿嘿”的两声怪笑,那笑声在阴森的宗祠里回荡,让人毛骨悚然。
“演戏?大人说笑了。”
朱全昱从怀里摸出一块擦汗的破布,慢条斯理地擦着手上的血,一步步逼近那个统领,声音低沉:
“我这是在救全族人的命,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把这小子的另一条腿也打断,给你助助兴?”
说完,他猛地弯腰去捡那根带血的枣木棍!
统领瞳孔一缩,手里的刀“锵”的一声出鞘半寸。
枣木棍带着风声,狠狠地砸了下去。
没有丝毫的犹豫,更没有所谓的“点到为止”。
“咔嚓”一声脆响。
那不是打在腿上的声音,而是打在了青石板上。
就在棍子即将落下的瞬间,那名禁军统领拔刀出鞘,用刀背硬生生架住了这雷霆万钧的一击。
朱全昱虎口崩裂,鲜血顺着指缝往下淌,但他像是感觉不到疼一样,依旧瞪着那双猩红的眼睛,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拦我干什么?让我打死这个不孝子!
打死了干净!省得给陛下添堵!”
统领的手臂被震得发麻,他看着眼前这个状若疯魔的老头,眼中的怀疑终于慢慢消散,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和轻蔑。
虎毒尚不食子。这老头为了表忠心,竟然真下得去死手。
“够了!”统领收刀入鞘,冷冷地看了一眼已经痛晕过去、裤管渗血的朱友谅,“广王殿下的忠心,末将见识了。
既然腿已经断了,这‘清理门户’的事就算了吧。
真要打死了,陛下那边面上也不好看。”
说完,他嫌恶地用手帕擦了擦溅在盔甲上的血点,转身挥手:“撤!回去复命,就说广王一家安分守己,正在闭门思过。”
禁军像退潮一样离开了宗祠。
大门重新关上。朱全昱手里的棍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身子晃了晃,一屁股坐在了冰凉的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整个人像是瞬间苍老了十岁。
周围的族人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疏离。没人敢上前扶他一把。
从此以后,砀山朱家庄多了一个瘸腿的少爷,也多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疯族长。
转眼便是三年。
这三年里,外面的世道越来越乱。
朱温在汴梁杀人如麻,今天杀大臣,明天杀兄弟,后梁的江山在血泊里摇摇欲坠。
而砀山朱家庄,却因为那个“疯老头”的恶名,成了一座被世人遗忘的孤岛。
这年冬天,雪下得格外大,连着下了半个月,积雪没过了膝盖。
深夜,朱全昱提着一盏昏暗的风灯,裹着那件破旧的羊皮袄,习惯性地去巡视庄外的地窖。那是全族人过冬的口粮,也是他的命根子。
走到地窖口,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看见雪窝子里趴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走近一看,是个冻僵的人。
那人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的单衣,怀里死死护着一个公文包,脸上全是冻疮,只有鼻翼还在微微扇动。
朱全昱眯起眼睛,蹲下身子。
他并没有急着救人,而是先翻开了那人冻得青紫的手掌,虎口有老茧,那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手指修长却有墨痕,这是个读书人。
再看那公文包的一角,隐约露出一枚暗红色的印泥痕迹。
那种印泥的颜色,朱全昱在朱温的案头见过,那是只有前朝(唐朝)枢密院才用的“紫泥”。
朱温正在全天下搜捕唐朝旧臣,抓到一个就是剥皮实草。
这人是个烫手山芋,也是个天大的麻烦。
朱全昱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沉睡的庄子,又看了一眼这个快死的人。
一声长叹消散在风雪里,他本心的善良还是没忍心。
殊不知,这个善举将改变他一家的命运。
他没有喊人,而是把自己那件还带着体温的羊皮袄脱下来,裹在那人身上,然后像扛一袋米一样,费力地将那人扛进了地窖。
地窖里暖和,堆满了过冬的大白菜和红薯。
那人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干草堆上,旁边生着一盆炭火,上面架着个瓦罐,正咕嘟咕嘟煮着小米粥。
朱全昱坐在对面,手里正编着一个草鞋底子,头都没抬,“醒了就喝粥。
喝完了赶紧走,别死在我这儿,晦气。”
那人惊恐地缩成一团,警惕地看着朱全昱:“你是谁?这是哪?”
“我是个种地的,这是菜窖。”朱全昱咬断了一根草绳,“你是谁我不问,你也别说。
吃饱了有力气了,就往北走。
过了黄河就是晋王的地界,那边不杀读书人。”
那人浑身一震,死死盯着朱全昱。
他认出了这张脸,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疯疯癫癫、打断儿子腿的广王朱全昱!
“王爷……为何救我?”那人声音颤抖,“我是朝廷钦犯,若是交出去,您可以换万两赏银。”
“万两赏银?”
朱全昱嗤笑一声,拿起一个红薯扔进火盆里,“那是买命钱,烫手,我家虽然穷,但还没穷到拿人命换钱的地步。”
那人沉默了许久,突然跪在干草上,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恩公高义!在下乃前唐枢密院……”
朱全昱猛地打断他,用手里的草鞋底子指了指地窖口,“我说了,别告诉我你是谁。
出了这个门,你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你。
我就是个怕死的老农,没那个胆子通敌。”

那人愣住了,随即眼眶通红,深深地看了朱全昱一眼,不再多言。他端起瓦罐,将那滚烫的小米粥一饮而尽。
临行前,风雪依旧。
朱全昱递给他一袋沉甸甸的东西。
“这是啥?”那人问。
朱全昱拍了拍那布袋子,眼神里透着一股深邃的光,“这是大唐年间留下来的老种。现
在的种子不行,长得快,但是根子浅,不抗冻,一场雪就冻死了。
这老种虽然长得慢,但是根扎得深,命硬。”
那人接过布袋,手猛地颤抖了一下。
他是聪明人,听懂了这话里的弦外之音。
现在的种子根浅不抗冻;老种根深命硬。
“恩公的话,在下记住了。”那人将布袋死死系在腰间,那是比他的命还重要的东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若有来日,必报此恩!”
“走吧。别回头。”
朱全昱摆了摆手,重新提起那盏昏暗的风灯,转身走向黑暗的庄子,“麦子熟了的时候,记得给个信儿就行。”
风雪掩盖了脚印。
乾化二年的夏天,汴梁城热得像个蒸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药渣味。
消息传到砀山的时候,朱全昱正在地里给瓜苗打顶。
“陛下……不好了。”报信的族人跪在田埂上,浑身哆嗦,“太医说,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朱全昱的手抖了一下,指甲掐断了一根嫩绿的瓜藤。
汁液流在手上,黏糊糊的。
他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收起锄头,转身回屋收拾那个用了几十年的旧包袱。
“爹,别去!”
瘸了一条腿的长子朱友谅,拄着拐杖拦在门口,眼睛赤红,“那就是个狼窝!现在二皇子(朱友珪)和三皇子(朱友贞)为了那个位置杀红了眼,您现在去,不是往刀口上撞吗?”
朱全昱看着儿子那条残废的腿,眼神复杂。
“他是皇帝,也是你三叔。”
朱全昱推开儿子,声音沙哑,“他这辈子朋友死绝了,仇人满天下。
临了,总得有个家里人送送他。”
再一次踏入大梁皇宫,这里已经没了当年登基时的金碧辉煌。
寝殿内挂满了厚重的帷幔,挡住了所有的光,阴森得像是一座活死人墓。
角落里的冰鉴散发着丝丝寒气,却压不住那股浓烈的腐朽气息。
朱温躺在宽大的龙床上,曾经那个能拉开三石强弓、杀人如麻的壮汉,如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他的脸颊深陷,眼窝发黑,只有那双眼睛还透着一股子临死前的凶光和惶恐。
听到脚步声,朱温费力地转过头。
“大……大哥?”
朱温的声音像是在风箱里拉扯,破败不堪,“你……你来了。”
朱全昱没行礼,也没说话。他搬了个锦墩,像在自家炕头一样,坐在了龙床边上。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个皱巴巴的橘子。
“砀山老家的橘子,刚熟。”朱全昱低着头,用那双粗糙的大手,一点点剥着橘子皮,“还是那棵老树结的,酸,但是解渴。”
朱温看着那橘子,眼角突然湿润了。
“大哥……朕……我是不是做错了?”
朱温喘息着,一只枯瘦的手死死抓着朱全昱的衣袖,指甲几乎陷进肉里,“他们都怕我,都恨我……连我的儿子……都在外面等着我咽气……我是不是……不该走这条路?”
这个问题,太重了。
重到无法回答。
说是,是诛心;说不是,是欺心。
朱全昱的手顿了顿。他没有回答,只是掰下一瓣橘子,塞进了朱温干裂的嘴里。
“吃吧。”朱全昱淡淡地说,“堵上嘴,就没那么多话了。”
酸涩的汁水在口腔里炸开,朱温被酸得五官扭曲,却又像是尝到了这世间最珍贵的美味,拼命地吮吸着。
“大哥……带我回家……我想回砀山……种地……”
朱温含糊不清地呢喃着,眼泪顺着眼角滑落,流进了明黄色的枕头里。
朱全昱看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弟弟,如今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哭泣。
他伸出手,想要像小时候那样摸摸弟弟的头,但手伸到半空,又停住了。
那上面戴着通天冠,那是皇权的象征,也是吃人的怪物。
“睡吧。”朱全昱收回手,替他掖了掖被角,“睡着了,就到家了。”
朱温渐渐安静下来,呼吸变得微弱。
朱全昱坐了一会儿,起身离开。
走到寝殿门口时,他看到了阴影里站着一个人。
那是二皇子朱友珪、他穿着一身戎装,手里提着一把还在滴血的横刀,身后跟着几个面目狰狞的家奴。
叔侄二人,在阴暗的廊下对视。
朱友珪的眼神里全是杀意和疯狂,他握紧了刀柄,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连这个大伯一起解决。
朱全昱却连看都没看他手里的刀一眼。
他只是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像个刚串完门的老农,侧身给这群急着进去送葬的凶神让开了路。
“大伯慢走,恕不远送。”朱友珪阴测测地说了一句。
“不用送。”
朱全昱头也没回,迈过高高的门槛,走进了刺眼的阳光里,“你们忙你们的。”
就在他刚刚走出大殿没多远。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那是濒死野兽最后的哀鸣,紧接着是重物倒地的闷响,还有刀刃砍入骨头的声音。
那声音,和当年他在宗祠打断儿子腿的声音,何其相似。
朱全昱的脚步猛地顿了一下。
那一瞬间,他的背影佝偻得像一张断了弦的弓。
但他终究没有回头。
他只是从怀里掏出剩下的那半个没剥完的橘子,狠狠地塞进嘴里,连皮带肉地嚼着。
橘皮苦涩,橘肉酸楚。
他一边嚼,一边流泪,一边大步向宫门外走去。
身后,巍峨的大梁皇宫乱成了一锅粥,喊杀声震天动地。
那个不可一世的王朝,随着那半个橘子,被他彻底咽进了肚子里。
后梁的天下,崩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快。
乾化三年的风全是腥的。先是二皇子朱友珪在皇宫里杀了亲爹,没过多久,三皇子朱友贞又带兵杀进宫,把二哥的脑袋砍下来挂在了城墙上。
紧接着就是大清洗。
曾经那些不可一世的朱家王爷们,郴王、贺王、建王……像是被收割的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地倒在刑场上。
消息传回砀山朱家庄时,正值深夜。
跛脚的长子朱友谅坐在昏暗的油灯下,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皱巴巴的邸报。
那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死人的名字,每一个名字他都认识,那是曾经和他一起喝酒、一起骑马夸耀富贵的堂兄弟们。
“郴王朱友裕,赐死。”
“皇子朱友硅,在那把龙椅上还没坐热乎,就被乱兵剁成了肉泥……”
朱友谅看着看着,牙齿开始剧烈地打颤,手里的邸报抖得哗哗作响。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那条残废的左腿。
如果不残,他现在就是衡王。
按照这份死亡名单,衡王的府邸此刻应该已经被禁军踏平,他的脑袋,应该正挂在汴梁城的某个旗杆上风干。
冷汗瞬间浸透了脊背。
那条曾经让他恨入骨髓、让他无数次在深夜里诅咒父亲狠毒的断腿,此刻竟然隐隐发烫,仿佛成了他身上最坚硬的护身符。
房门被推开。
朱全昱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更老了,背驼得像一张犁,手里提着一把铁锤,身上沾满了炭灰。
父子俩在昏暗的灯光下对视。
这是三年来,父子俩第一次正眼看对方。
朱友谅看着父亲那张满是沟壑的脸,突然觉得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想站起来,但那条断腿让他踉跄了一下,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没有爬起来,而是顺势跪在了地上,用膝盖当脚,一步步挪到了父亲面前。
朱友谅从怀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金灿灿的物件。
那是当年朝廷册封他为衡王时,赐下的金印。

这三年来,他一直像宝贝一样藏在贴身处,那是他对富贵最后的念想。
但此刻,他把金印放在了地上,像是扔掉了一块烧红的烙铁。
“这东西……烫手。”朱友谅哽咽着,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金印上,“差点把儿子的命都烫没了。”
朱全昱低头看着那个刻着盘龙的金印,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儿子。
他那双浑浊的老眼动了动,没有说话,只是弯腰捡起了金印。
“跟我来。”
朱全昱转身走向后院的打铁房。
炉火烧得正旺,红彤彤的火光照亮了父子俩的脸。
朱全昱用铁钳夹住那方象征着无上权力的金印,毫不犹豫地扔进了红热的坩埚里。
金印在烈火中迅速软化,那些精美的盘龙、那些原本可以号令一方的文字,在高温下渐渐融化成了一摊毫无形状的金水。
朱友谅跪在一旁,死死盯着那摊金水,仿佛看着自己那虚妄的野心被一点点炼化。
朱全昱熟练地操纵着风箱,又往坩埚里加了几块熟铁,最后将混合了黄金的铁水倒入了一个早已备好的模具里。
冷却,淬火,锻打。
当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的时候,一把崭新的、泛着淡淡金光的锄头,摆在了铁砧上。
这恐怕是全天下最贵的一把锄头。
朱全昱拿起锄头,掂了掂分量,递到了儿子手里。
朱全昱的声音依旧干巴巴的,没有半点温情,“腿断了,手还在,只要肯弯腰刨食,这地里就长不出死人。”
朱友谅双手接过那把沉甸甸的锄头,额头重重地磕在满是煤渣的地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爹,儿子……懂了。”
这一声爹,叫得撕心裂肺,却又透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朱全昱受了这一拜。
他转过身,看着窗外初升的太阳,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懂了就下地干活。庄子里的墙还要加固,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在这个诸侯混战、人命如草芥的清晨,砀山朱家庄的那个跛脚少爷,终于死了那条当王爷的心。他扛着那把混着金印的锄头,一瘸一拐地走向了麦田。
而在庄子外面,后唐李存勖的大军,正踏着遍地的尸骨,一步步向汴梁逼近。
龙德三年的秋天来得格外萧杀。
这一年,李存勖的晋军攻破了汴梁。末帝朱友贞在绝望中让亲信皇甫麟杀死了自己,那颗曾经高贵无比的头颅,被当作礼物送到了李存勖的马前。
后梁,亡了。
随着大梁旗帜倒下的,是针对朱氏皇族的“灭绝令”。
李存勖下令:凡朱温血脉,无论老幼,除恶务尽。
屠杀的浪潮像黑色的瘟疫一样,顺着官道一路向东蔓延,终于在那个黄昏,逼近了砀山。
“咚、咚、咚。”
大地震颤的声音传到朱家庄时,地里的乌鸦被惊得满天乱飞,呱呱乱叫。
那不是雷声,是几千匹战马同时叩击地面的死亡丧钟。
“来了……他们来了!”
在庄口放哨的族人连滚带爬地跑回来,裤子都尿湿了,“全是铁骑!黑压压的一片,把庄子围死了!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庄子里瞬间炸了锅。妇人抱着孩子哭嚎,男人拿着锄头的手在发抖。
那把刚铸好的“金锄头”,此刻在朱友谅手里沉得像座山。
“都闭嘴!”
一声苍老的断喝压住了所有的慌乱。
朱全昱从屋里走出来。
他穿了一身最干净的粗布衣裳,腰间别着那杆跟了他几十年的老旱烟袋,脚上穿着一双新编的草鞋。
他看起来不像是去赴死,倒像是去赶集。
“友谅,带着妇孺下地窖。
把盖板盖严实了,我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声。”
朱全昱的声音很平,平得听不出一丝波澜,“男人们把手里的家伙事都扔了。
人家那是杀人的军队,你们拿这烧火棍去送死吗?”
“爹!我们跟他们拼了!”朱友谅红着眼,举起锄头。
“拼个屁。”朱全昱夺过锄头,随手扔在墙角,“那是晋王的大军,连你三叔的几十万禁军都挡不住,就凭你们?”
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那只粗糙的大手第一次带着一丝温热:“躲好了,咱们朱家能不能留个种,看天意,也看你爹这张老脸还没被撕破。”
说完,朱全昱推开想要拉他的族人,独自一人拄着拐杖,向庄口走去。
庄口有一盘用来磨面的大石碾子。
朱全昱走过去,用袖子扫了扫上面的浮土,然后盘腿坐了上去。
他从腰间解下烟袋,慢条斯理地装上一锅烟丝,掏出火折子,“呼”地吹亮,点燃。
“吧嗒,吧嗒。”
青烟在黄昏的余晖里袅袅升起。
就在这第一口烟刚刚吐出来的时候,黑色的铁骑洪流到了。
那是刚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百战精锐。
黑色的铁甲上满是暗红的血垢,长矛的锋刃在夕阳下闪着令人胆寒的寒光。
马蹄声在距离碾盘十步远的地方戛然而止。
几千双充满杀气的眼睛,死死盯着这个坐在碾盘上抽烟的老头。那种无形的煞气,让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温度骤降。
为首的一员大将策马而出。
此人身材魁梧,满脸横肉,手里的马槊还在往下滴血。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朱全昱,像看着一只待宰的蝼蚁。
“你就是朱全昱?”
大将的声音像炸雷一样,震得朱全昱耳朵嗡嗡响。
朱全昱没抬头,只是又吸了一口烟,在鞋底上磕了磕烟锅:“是,我是朱大。”
“好胆色。”
大将冷笑一声,手中的马槊猛地一指,锋利的槊尖几乎戳到了朱全昱的鼻尖上,“晋王有令,朱温余孽,鸡犬不留!老东西,你是自己抹脖子,还是让爷爷把你这庄子踏平了?”
身后的骑兵们齐齐拔刀出鞘,“锵”的一声,那是金属摩擦出的死亡音符。
面对这扑面而来的刀山剑海,朱全昱的手很稳。他甚至还伸出手指,轻轻弹了弹面前那根冰冷的马槊杆。
“这位将军,赶路辛苦。”
朱全昱抬起眼皮,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看透生死的淡漠,“要杀要剐,冲我这把老骨头来就行。
庄子里剩下的都是些种地的庄稼汉,这辈子连汴梁城都没去过。
将军手里的刀是用来杀敌的,杀一群种地的,怕是脏了将军的名声。”
大将怒极反笑,“朱温杀我李家人的时候,可没嫌脏了手!父债子偿,兄终弟及!今天你们全族都得死!”
说完,大将眼中凶光毕露,手中的马槊高高举起,就要向朱全昱的头顶砸下
朱全昱没有躲。
他只是闭上了眼睛,重新把烟嘴塞进嘴里,狠狠地吸了最后一口。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破空声,紧接着是一声嘶力竭的大吼:
“刀下留人!!!”
马槊的锋刃,停在了朱全昱眉心前半寸的地方。
几缕花白的头发被锐气激断,飘飘荡荡地落在满是尘土的碾盘上。
“住手!刀下留人!”
一匹快马冲破了烟尘,马上一人身着紫袍玉带,滚鞍下马,动作急切得差点摔个跟头。
他手里高举着一面金灿灿的令牌,那是只有晋王李存勖亲赐的“免死金牌”。
“晋王有令!砀山朱全昱,乃大唐义士,不得惊扰!”
举刀的大将愣住了,硬生生收回了力道,转头看向来人:“枢密使大人?这老东西可是朱温的亲大哥,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啊!”
紫袍人没有理会大将,而是快步走到碾盘前,看着那个依旧闭着眼、嘴里甚至还叼着烟袋的老人。
他的眼眶瞬间红了。
“恩公,”紫袍人声音颤抖,“还记得那个雪夜吗?”
朱全昱缓缓睁开眼。在那一瞬间,并没有劫后余生的狂喜,只有一种仿佛早就料到的疲惫。
他看了看眼前这个位高权重的紫袍大官,又看了看他腰间那个虽然破旧、却被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布袋子。
“记得。”朱全昱磕了磕烟灰,声音嘶哑,“那袋谷子,种下去了吗?”
“种下去了!”
紫袍人解下腰间的布袋,双手捧到朱全昱面前,眼泪夺眶而出,“恩公当年说得对,大唐的老种命硬,根扎得深。如今……这谷子长出来了,满天下都是。”
随后,紫袍人转身,面对那几千名杀气腾腾的铁骑,高举手中的文书,大声宣读:
“奉晋王令:查,朱全昱虽为梁亲,然心存大唐。开平元年,曾于金殿怒斥朱温篡逆;乾化二年,曾于雪夜救助唐臣。
其断子腿以明志,守田园以拒禄。此乃乱世之清流,非朱温之余孽也!特赦朱全昱全族,永不加赋,永不问罪!”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敲在在场所有人的心上。
那名大将听完,脸色变了数变。他深深看了一眼这个坐在碾盘上的老头,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大智若愚”。

大将收起马槊,抱拳行了一礼,调转马头。黑色的铁骑洪流如潮水般退去,只留下一地杂乱的马蹄印和尚未散尽的尘埃。
庄子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
朱友谅带着族人们冲了出来。他们看着那远去的军队,又看着坐在碾盘上完好无损的老父亲,一个个腿一软,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哭声震天,那是把这三年的恐惧、委屈、绝望统统哭了出来。
唯独朱全昱没哭。
他费力地从碾盘上爬下来,拒绝了紫袍人的搀扶,也拒绝了儿子朱友谅的拥抱。
他只是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捡起墙角那把泛着金光的锄头。
“哭什么哭?丧气。”
朱全昱背着手,像往常一样训斥了一句,“天还没黑透,地里的活还没干完呢。”
说完,他拄着锄头,一瘸一拐地向着庄外的麦田走去。
夕阳如血,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那一年的秋天,砀山的麦子长得格外好。
当李存勖在洛阳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后唐,在那张龙椅上开启新一轮的杀伐与轮回时;在几百里外的砀山,一个叫朱全昱的老农,正蹲在地头,用那双粗糙的大手,爱怜地抚摸着一株沉甸甸的麦穗。
王朝像走马灯一样换,只有这地里的麦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生生不息。
史书载:朱全昱,太祖长兄也,戆朴无能,然独以一言之善,保全其族,寿终正寝。
只是没人知道,那个“戆朴”的老人,在每一个起风的夜晚,都会看着汴梁的方向,沉默良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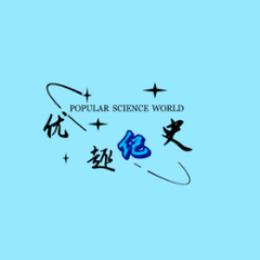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