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你要到山西去暂住一阵。”电话那端的工作人员语气平静,却不容商量。李运昌停顿两秒,只简单回答了一声“明白”。
1955年秋,薪金制正式落地,全国干部第一次被严格划入行政等级。行政5级,在当时仅次于最高层的1—4级,对应军队正兵团级,月薪折算下来大约四百三十多元。这是个什么概念?那一年北京普通科员月拿三十多元,资深工程师也不过一百出头,5级干部的收入几乎是他们的十倍。政策设计者原以为这样的差距足够体面,然而对李运昌来说,账面富裕并不等于口袋殷实。

他在河北农村长大,老家亲族多,解放后陆续有亲戚进京求职、看病、上学,谁也不好意思空手而回。再加上子女一个接一个,学费、食堂钱、衣服票都得掏。熟人来借钱,他从不推辞,“多则百元,少则十几”,月薪只剩零头。有意思的是,工资在账面上看涨,实际却在缩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后,中央几次缩减高干薪金,李运昌到1965年只剩三百多元。数字还算漂亮,可每月到头,兜里照例见底。
职务与级别的错位让外人疑惑。李运昌一辈子没当过正部长,大多是“第一副”字样。原因之一是革命年代定级主要看资历和贡献,而不是眼前座位。级别确定后极难变动,后来干部提拔再高,工资条也不一定跟着跳档。对于老干部来说,这既是荣耀,也是沉甸甸的束缚。
转折点出现在“文革”后期。1975年,为“审查问题”,他被通知离京,地点选在山西长治。按照规定,发给每月生活费二百元,比地级市书记标配还高一点,可比他原来的薪资少了一截。没人料到,这笔钱第一次让他有了积蓄。

原因很简单。一离开北京,亲戚朋友音讯全无,求助的、登门的统统消失;儿女已各自成家,也不在身边吃饭。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两口人开支有限。长治当年市场价格低,白面六分钱一斤,羊肉七角,蔬菜大多几分钱。李运昌每日两顿粗细搭配,加上偶尔买些书报,一月还花不到一百五。“剩下的,帮衬一下隔壁街坊。”他后来回忆,“远亲不如近邻是真理。”
邻居们并不知道面前这位白发老人当过交通部第一副部长,只知道他愿意替孩子看门,替老大娘跑腿,拉起家常毫无架子。李运昌也在这种半隐半显的状态里度过了三年。
1978年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传到长治。“形势变了,该回去了。”长子来信催促。是否需要等正式文件?有人劝稳妥,但家里达成共识——主动出击。于是2月初,他带着全部行李,一张三等车票,坐了十几个小时硬座回到北京西站。到家没几天,组织部门来人谈话,批评一句“擅自回京”后补上手续,事情算揭过去。
恢复工作意外顺畅。1979年,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兼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长,行政5级待遇依旧。月薪回到四百元区间,生活节奏却彻底变了。那时亲戚们已各自找到出路,孩子自食其力,李运昌终于可以把收入用在读书、看戏、偶尔旅行。朋友打趣:“你退休才真正过上工资水平相符的日子。”

有人问他,年轻时如果少管一点闲事,能不能早早攒下一大笔?他淡淡一笑:“那是命,不后悔。”从慷慨借钱到偏居长治,从两百块结余到重返北京,李运昌的际遇映照了一条清晰的历史纵线:干部待遇从高到低再到平稳,社会关系从血亲、同乡网络转向制度化保障。
不得不说,1950年代的薪金制试图用量化手段弥补战时功劳,而1970年代的外放又提醒世人,等级再高也不代表安全。对普通人而言,那一串冰冷的数字是榜样也是镜子——钱多未必花得开,位置高也可能朝不保夕。李运昌的故事说明,制度在变,环境在变,人情却难以脱身;唯有心里留几分余地,才能在风向突变时稳住脚跟。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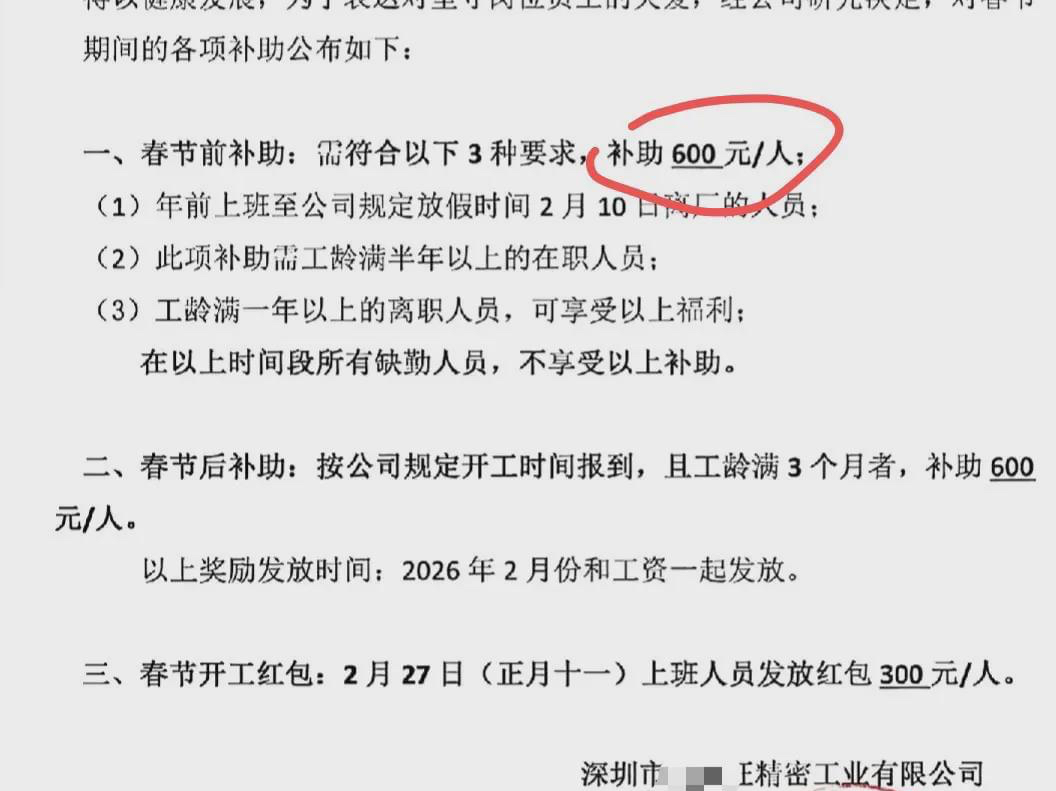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