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指南作者:吕一含
二本学生意味着什么?
二流的学校,似乎也预示着二流的人生。
二本学生这一标签,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下,通常自带低人一等的意味。他们面目模糊,也看不清自己的未来。
在成为二本院校的老师前,黄灯对于二本学生的想象也是这般刻板而匮乏——
这些学生之所以在二本上大学,是因为学习不努力,或是其他原因被分流至此。他们构成了高等教育中庞大而面目模糊的数字,是普通而平庸的沉默群体。
但当她真正站上讲台,耐下心来深入了解她的学生们,她的刻板印象彻底改观了——
每一个考入二本的大学生,不但需要自己本身很努力,也同样需要家庭的全力托举。

黄灯在中山大学
她的学生为了来到大学,他们的父母需要在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劳作,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撑孩子的求学路。
二本学生的来时路,远比她想象的更为艰辛。
在课堂上,黄灯开始更多倾听学生们的声音,也逐渐走进学生家中家访,走访过二十多个学生家里,这些成为她观察和书写的起点——她决定真正地看见他们。

1992年,高中毕业的黄灯以4分之差与本科失之交臂。她曾想过复读,但父母觉得当时本科与专科的差距不大——毕业后都是国家干部。
在中学做老师的父亲更担心的是,万一第二年还是考不上呢?
她只好顺着父母的心意进入岳阳大学读书。

早期的黄灯
在那个考上大专已属不易的年代,本科和大专之间的界限的确没有现如今区隔如此大。
黄灯并不羞于告诉别人自己在岳大读书,她和北大的同学见面聊天,大家会谈起各自感兴趣的作家、关心的社会事件,“我们岳大的学生同样也关心着北京的事”。话语间是年轻学子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期待。
毕业后,黄灯被分配至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成为一名办公室的行政人员。
然而不过两年,黄灯最初的顺遂生活被逐一打破。时值工厂响应国家政策减员增效,她从厂部团委被下调到车间当挡车工。
即使是28年后,她依然能清晰记得被调岗的日子,1997年4月17日。

职工在车间工作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一年后,工厂效益逐年递减,没有订单,工资最低时、最困难的时候,黄灯每月只能领到80元补贴——她成了实际上的下岗女工。
改革的阵痛,成了黄灯的切肤之痛。
她靠着四处向朋友、同学借钱度日,但也是在这样艰难的一年,她硬是完成了自考拿到本科文凭。
为了谋求出路,黄灯决定考研。
备考的条件不算好,她在朋友的公司做一份临时工作,下班后就在公司洗手间旁支起小床,独自看书复习。没人知道这个纺织厂的下岗女工,心里暗暗憋着怎样一口气。

黄灯
几个月后,她如愿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是那家纺织厂第一位成功考上研究生的工人,之后,她又考上中山大学的博士。
2005年,博士毕业的黄灯来到广东一所二本院校担任老师。第一次上课,她兴奋得忘带了钥匙。
在此之前,她做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干过一线女工,又经过六年漫长求学,才终于站上如今的讲台。
高等教育结结实实地改变了一个农村女孩的命运。
作为二本院校的老师,黄灯常常思考:二十年过去,和她相同起点的二本学生,如今究竟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受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压力?

黄灯(前排左一)与学生们
黄灯无疑是幸运的。
学生时代,尽管就读于地方院校,在大学生包分配的年代她不用担心找工作,每月的生活补助让她无需为生计发愁。她爱看书,读书也给了她相应的回报。
而今天,经历过无数严苛应试考验才来到大学校园的年轻人,他们还能否和自己一样,依赖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难以跨过的暗礁?
她能感觉到,微妙的改变正在教育行业中发生着。

十几年的教学,在与四千五百多名学生的日常交流中,她逐渐意识到,国内二本院校的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
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只有少数幸运者能进入重点大学,更多人只能走进普通二本院校。
想把二本学生写下来的冲动,源于一次课堂教学。
黄灯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天——2006年5月17日,一堂大学语文课上,她给学生布置了一篇题为《风》的作文。

黄灯收藏的学生作文
当黄灯读到一个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后,她久久难以平静。
女孩笔下,是一个多子女、月收入不足一千的家庭,她半年没拿到生活费,又因父母年龄未到四十五难以申请助学贷款,她焦虑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甚至怀疑自己不该来上大学。
在作文里,她自己根本“没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而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
黄灯才意识到,即便是在她认为相对发达的广东地区,这些学生背后的家庭,远没有她以为的光鲜,还有人在经受着与她童年时一样的困境。

黄灯《十三邀》
她曾以为现在的学生考上二本院校,这背后的读书之路不用很辛苦,但实际上,“从乡村到二本大学,我的学生的家庭也已为此倾尽所能。”
读完作文,黄灯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老师发起募捐,邓桦真的现实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也有了勤工俭学的机会,后来,女孩给黄灯的邮箱发去《感恩的心》的歌词。
就这样,一堂公共课上一篇临时布置的作文题《风》,逐渐坚定了黄灯走进一个年轻群体,去看见更多人青春的想法。
这篇作文也悄然改变了她任教的态度,在上课、评职称之外,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更认真地去看看那些具体的年轻生命。

黄灯在欧亚学院演讲时台下的场景
她通过学生手写的作文和他们交流,并开设了一堂不讲专业而自由讨论的课,她让学生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慢慢地便有学生会主动找到她倾诉。
让她有些意外的是,还有很多和桦真有类似遭遇的学生,相似的焦虑、困顿普遍出现在学生群体,只是他们缺少倾诉和被发现的切口。
在黄灯看来,作为二本学生,“他们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
黄灯的人生轨迹,放在现在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黄灯
对于如今来自农村的孩子,“应试教育在用极端损耗的方式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公平。”
让她记忆犹新的一次期末考,学生们在作文考题里写下——
“以高考为划分线,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被简单粗暴划分成了两部分,高考前,高考后......人生就像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我必须不能出一点差错照着这个轨迹预演下去。”
“我们几乎把十八岁以前的人生都献给了高考,十几年的努力和奋斗都押在了一场考试上。这或许是人生中赌得最大的一次赌博。”
“不明不白地进入教室,不明不白地接受着对于我们而言,无论是将来,还是现在的生活中,都可能完全用不到的知识。”

王顺然送给黄灯的摄像册里的照片
这些文字让她痛心,学生们拼命付出多年,被应试教育磨完了天性,成了工厂的标准化构件,好不容易来到大学,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
这些普遍的困顿,不只是压在个人身上的大山,也是教育系统需要面对的问题。

2006年,学校决定成立财经传媒系,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中文博士毕业的黄灯在给全校学生上公共课之外,终于有了上专业课的机会,并成了062111班新生的班主任。
班主任的身份让她自然而然地和学生有了更多联结。
她不只是陪伴学生度过大学四年,在学校后山和学生们共度毕业聚餐,黄灯也通过微信和QQ默默关注着学生们毕业后的动向,观察一代年轻人离开校园的真实境遇。

黄灯(三排左三)与学生们
作为经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黄灯很明显能察觉出大学教育多年来的目标变化:
在她上大学的年纪,教育的目的是给集体培养人才,而到了06级学生,教育成了培养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
黄灯读书时,中专生、专科生也曾被视为天之骄子,考上大学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是跳龙门般改变命运的大事。
但对她的第一届学生来说,进入二本院校,还没能来得及好好享受大学时光,就已被告知就业的压力,成为学校锻造专业流水线上的规整产品。

黄灯在演讲中分享对教育的观察
年轻人身上所呈现的丰富性,改变着她内心的刻板印象。尽管就业市场局限、房价高涨、生活压力陡增,年轻个体在困境前爆发的向上生命力依然让她为之动容。
黄灯依然能感觉到,读书、上大学对于农村孩子的重大意义。
他们也许错过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
她意识到,哪怕是处于高校生态链末端的二本院校,也有着重要的使命,并与无数普通青年的命运紧密相关。
2016年,黄灯接手1516045班,时隔九年再次做起班主任。

黄灯在教室授课
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更深的代沟和距离——学生只需要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动作,就足以消解班主任角色所带来的权威,面对更年轻一代的学生,黄灯开始觉得忐忑与困惑。
和06级学生相比,15级学生也更多了一份不确定的迷茫。
尤其到了毕业季,学生们一个个敲响她的办公室门,试图从老师口中寻得一个关于未来的确定答案:他们迫切想知道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创业的成功概率。
而这些追问都会回归到一个问题:读大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黄灯想问的:教育产业化之后,教育和年轻人的命运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黄灯
黄灯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于是将这些一线教学中的观察、学生鲜活个体的故事一一写下,在2020年集结成书出版《我的二本学生》。
这之后,她让二本学生这个长期沉默的群体,第一次大规模走进公众的关注视野,不被看见的二本学生,这一次走到了台前。
在无数采访、讲座中,她一遍遍提到二本学生给她带来的思考。

随着关注一同到来的,则是更多疑问。有读者发问,如果二本学生都这么难了,那职校大专的学生又该如何是好?
这个沉重的问题一直萦绕在黄灯内心,机缘巧合下,黄灯在2019年夏天辞去院长职务,来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任教,在职校开设非虚构写作工坊。
这一次,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教育图景。

在职校,她所要面对的是一群更早被应试教育“放弃”的学生,他们的故事往往被淹没在升学率的统计数据之后,但他们的声音同样值得被记录和理解。
在职校的一次写作课中,她读到学生将自己比作“工业废水”——
一位叫梁萍的学生回忆起自己的初三,写道:在度过无数教育机构拼命渲染的各个分水岭之下,时间终于来到了初三。“源头活水”的老师们一直很放心,倒是我们这群“工业废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黄灯在非虚构课堂上提及“工业废水”的感受
戏谑的自嘲口吻下,是连自己都瞧不上自己的颓丧感。这样直白贬低自我的笔触让黄灯感到心痛,“当人为地按照成绩把他们分类的时候,他们就马上给自己归类了。”
在后来的多次媒体采访中,黄灯都会提到“工业废水”这个令她感到触目惊心的比喻。
她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生的自我调侃,也折射了教育生态中的残酷真相。
这些在考试竞争中落后的学生,内化了外界赋予的标签,并把这些负面标签转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带着这份心痛和责任感,观察越多,黄灯和学生的接触也更加深入。

黄灯在《十三邀》中谈及教育的问题
从2017年起,黄灯开始走进学生家中做家访。
“它只是一个视角,借由这个机会,走进中国农村,在大地上做家访。”
书写《我的二本学生》时,她关注学校教育的有限性。
而随着对学生的了解深入,她更想知道,在学校教育之外,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几年里,黄灯利用假期的时间,从云南腾冲到粤西农村,她坐火车、摩托车,路不通的地方,只有手扶拖拉机才能勉强开进。

家访途中,晓静妈妈骑摩托带黄灯行驶在路上
她切身了解了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上学路之艰辛,也看到中国乡村教育的真实图景。
这些家访经历让黄灯的教育观察变得更为丰富立体,她更清楚地意识到,理解一个学生,不仅要看学校社会给予TA的,更要看TA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承担着怎样的期待和压力。
教育问题,始终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紧密相关。
2024年,她将一路上家访的所思所想写进新书《去家访》。

黄灯《去家访》|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二本学生》的热销已将她推向公众视野,她再度频繁接受采访,出席各类教育讲座、论坛,在四处奔走时她总不忘了为学生发声。
在今年最近的一次教育论坛,她坦言,“当下大众低估了这代孩子的难处,年轻人缺少出路,不是因为不努力,而需要社会提供更多包容和接纳。”
2024年底,黄灯调任至中山大学,从广东金融学院到深职院,兜兜转转,黄灯再次回到了自己读博的校园。

黄灯在新东方家庭教育上演讲
从关注二本学生到在职校开设写作工坊,黄灯的追问始终如一:
在剧变的时代下,那些普通的年轻人如何安放他们的生命。
在优绩主义盛行的时代,她的视线始终落在普通人的具体命运之上。
她所做的事的确无法立刻改变结构性的问题,但至少,让曾经被忽视的角落照进光亮,为迷路偏航的学生指清方向。
“教育是一件特别实在的事情,要靠我们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靠所有人推动。”
参考资料:
1.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2.人物《黄灯,我的职校学生》
3.三联生活周刊《我和我的二本学生》
4.学人scholar《专访黄灯:我始终关注现实中的“人”》
5.看天下实验室《不被看见的二本学生,这一次走到了台前》
内容策划: 翟晨旭 夏夜飞行
排版设计: 蕾蕾 洛溪


文学杂志小传
转载、商务、作者招募合作丨请后台联系,凡本平台显示“原创”标识的文章均可联系编辑转载,未经授权转载视为抄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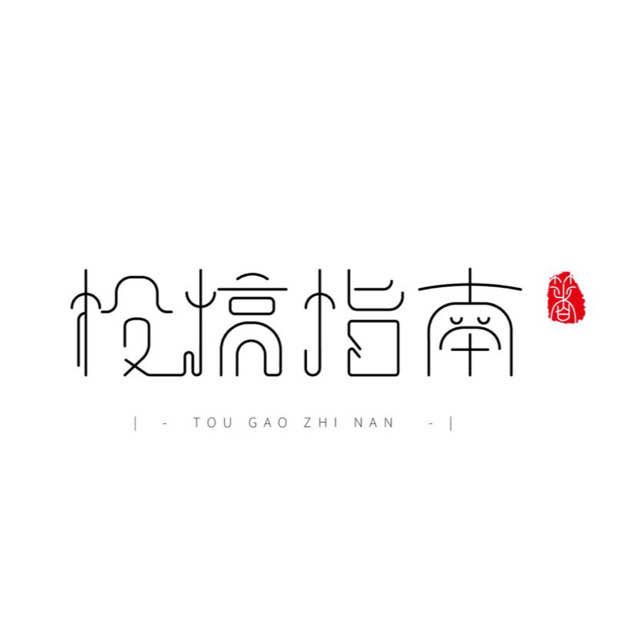


























热门跟贴